蝴蝶的念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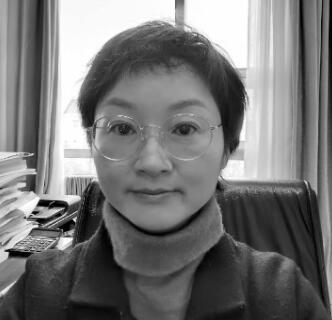
白小云,生于蘇州,現居南京。在《鐘山》《作家》《十月》《上海文學》《詩刊》《星星》《詩歌月刊》《詩選刊》《中國詩歌》《草堂》《芳草》《飛天》等發表作品若干,現北京師范大學創意寫作研究生在讀。
他又夢見了那只蝴蝶,柔軟的翅膀像兩片對折的大海,掀起風浪,藍色波濤撲面而來,把他澆透。這是“蝴蝶效應”。在夢里,他渾身濕漉漉滴著水,顫抖著,冷靜地對突然遭受的襲擊做出準確判斷。
他從夢里坐起,渾身顫抖,摸摸胸口,睡衣濕了一大片。他是冷靜的人,這次也難免噩夢聯翩。不是蝴蝶掀起大海,就是蝴蝶墜入深淵。
在接受上級嚴厲批評、媒體即將啟動連篇攻擊之前,在不可預測的處分還沒下來之前,安德榮立刻下令給教學樓安上了不銹鋼防護欄。他們喊它鴿子籠,他以前也這么喊,帶著幾分睥睨不屑。但事實到底是可怕的,容不得想象,這次他不能站在理想主義一邊,不能站在看應試教育好戲的觀眾一邊,不能站在疲勞又固執得和現實硬杠的教師們一邊,不能站在相信在高考教育的漩渦里可以撐開歡樂天地的自己一邊。他悔不當初的同時,立刻找李泊客商量。是,找李泊客,沒什么低不了頭的,當初是他拒絕了這位資深教導主任的建議,即便現在他打心底里還是小看這種謹慎過頭的建議。但沒什么低不了頭的。現實容不得等待,意外來得太突然,他還沒有從信誓旦旦的美夢里出來,就被兜頭澆了一盆冷水,在放聲大哭前,他必須憋住一口氣,像所有穩重的男人一樣,不解釋不慌亂,把該處理的事情處理好。
只是過了周末兩天,人們發現學校所有樓房的陽臺密閉了銀光閃閃的不銹鋼防護欄,打了橫豎格子,遠遠看去像一頁頁方格稿紙。如果不是突發事件,這座園林式校園會繼續在亭臺樓閣間閃現它古老沉靜的光芒,園子里百年老桂按時序飄香,肥碩錦鯉在深水池里悠閑沉浮,紫藤花老藤虬勁、等待春日,蘋果樹初秋便掛果成片……作為年輕有為的領導人才,他主政這座校園才幾個月。如果不是突發事件,周末校園里也是書聲朗朗的。一年之計在于春,一日之計在于晨,這座城市的教育信仰抓緊所有時間,特別是年少時光。而現在,最近的周末將暫停上課,學生們可以享用正常周末,在家自主學習。
周末兩天里,他被第一時間召到領導處匯報情況,匯報問題直到深夜,雖然關于補課他只是參照這座城市諸多友校的榜樣,不補課反而要被積極的家長投訴,但學校是不是強迫補課,有沒有因此給學生帶來過大壓力,這值得說明,當然這次的事情和補課沒有直接關系,和什么有關系?自然是高考壓力本身,但這也是校長需要說明交代的內容;同時他的辦公室主任、班主任同時出馬,持續不斷地與家長聯系,穩定情緒,防止事態擴大,也借以對孩子進行深入了解,當然在這種情況下要警惕家長提供篩選后的片面信息;又同時學校緊急事務會議組在學校里徹夜等待他,討論解決策略。
他第一次認識這個男孩,在這種被動的情況下。男孩窄肩膀、圓臉盤,嘴角咧開露出大門牙,銅鈴一樣的大眼睛笑得天真。如果不是出事,他不會如此反復細看一個男學生的照片,一雙眼睛長時間盯著另一雙眼睛,仿佛在和他說話。他想知道男孩經歷了什么?又想如果早點發現端倪,他一定能把他從獨自站立的五樓陽臺上勸下來。他心里重復著幾個疑問,也重復著幾句話。
生命,我們活著是為什么,努力是為什么呢?想到這,他心頭一驚,身上汗水如泉,難道學生們少了這一堂人生課?他迅速安排教務主任,下周一升旗儀式上以“生命的意義”為主題,安排一個三好學生演講。三好學生就放心嗎?不、不,這個出事的男孩不也是學霸嗎?演講稿班主任一定要事先把關,他又打電話給教務主任補充交代。周三下午的班會課,每個班進行主題討論,并讓教務主任做一個標準講稿下發到全校老師手里,把生命意義、青春奮斗的關鍵點寫全。“寫得全一點,不能遺漏!”他強調,作為教育工作者此刻他依賴言辭的力量,希望那些“關鍵點”能像種子一樣,說出去就能種進孩子們的心里。
李泊客說,“現在的孩子越來越乖,越來越沒有創造力,倔強變成了腦子里的骨頭。”
“那還不是你們這些老師管出來的?”當初,安德榮笑著反問李泊客。“你們老師”,仿佛他置身世外。
李泊客板著他教導主任的臉,不說話,像沒聽見。他在教導主任位置上穩坐這么多年,他冷臉鐵腕、怒目金剛,再皮的孩子到他手里都被順得服服帖帖。
大家都不說話。當時的場景,安德榮以為自己勝券在握,能兼容現實與理想,像牢騷看客一樣調侃“古板的衛道士”。從個人的教育理想而言,他欣賞形式上更加柔軟的根植,春風化雨,舉重若輕,游刃有余。
當然安德榮也知道,并且從來知道,菩薩心腸、菩薩面孔的老師們未必能收獲高效益,孩子們在慈善的老師那里會釋放無法無天的能量,別看他們已經是十七八歲了,孩子頑劣的天性還在,人類好逸惡勞、欺軟怕硬的天性促使他們萌生無數懶惰調皮的“智慧”。而學校教學的效益無非就是指成績吧,是所有人的緊箍咒,簡單,粗暴,統領一切。
“那還不是你們這些老師管出來的?”這句反問現在想來,像是問自己。
安德榮初到云上中學,做了充分的摸底工作,對全校中層、主要課程的任課老師的教育教學質量、習慣特點口碑進行了解,他喜歡李泊客的面孔,冷硬、真實,鐵面父親一般嚴肅,更喜歡李泊客的效益,那些善于狡辯爭論推脫、討價還價的孩子們,到他這里就知道該守規矩,知道自律和吃得苦中苦的道理。
安校長心知這次事故錯在自己一心二用,要么再理想主義一點,要么像李泊客一樣絕對的現實主義,兩者取其一都能成就佳話,兩者雜糅、拖泥帶水終不可靠。
班主任莫伯紳戰戰兢兢,意外情況下,他那被專業優秀覆蓋住的老實人本性一下暴露了。他今年暑假剛從鄉下調到市區,完成教師生涯的一次出色升級,初到云上中學就被委以班主任重任,可謂一帆風順。誰知道竟然出了這事。
事情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就莫老師這邊情況而言。期初摸底考、兩次月考,期初考試童僮分數在年級名列前茅,最近兩次月考接連往下掉,上周一次考試成績剛出來,他從年級前五十名掉到一百幾十名。按照學校提優補差的要求,他找孩子談話,“我沒有罵他,他是認真努力的孩子,犯不著罵,我只是客觀分析了他試卷的失分點,都是他會的題目,不該錯,我為他惋惜。”莫老師說,事到臨頭他勉力頂住,仍不免顯出有氣無力的失落,怕說錯話又不得不說。不是沒見過生死,曾有學生得惡疾、出交通事故去世的,但眼下這種極端的自我了斷死亡,新聞里聽說過,現實里他第一次碰到。
“有學生說,童僮是哭著回到班級的。”安德榮問,一時間關于這個孩子的信息真真假假灌滿腦袋,“他在辦公室哭了嗎?”這是關鍵細節,有時可見的場景會轉移事情的本質,他必須排除外在的嫌疑。
“哭了”,莫伯紳承認,“但我從頭到尾沒有罵他一句,反倒安慰他不要難過,只要知道自己問題錯在哪里,下階段有針對性地改進就行了”。
“你為什么不把他的情緒穩定下來,等他不哭了再讓他回教室?為什么不能再多一點耐心?哪怕再多問一句!”安德榮敲著桌子,嚴厲深長地質問,“孩子情緒有問題,老師要細心發現情緒點出在哪里,是因為成績嗎,還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你如果當時再追問一下,也許就挽救了他!也挽救了我們大家!”
“我問了,他不說,只是流眼淚,這么大的男孩子在老師辦公室里哭鼻子肯定是難為情的,我恐怕多問了反而讓他尷尬,想著這次讓他先回去,下次找適合機會再談……”莫老師解釋,“再說我還有約了好幾個孩子談話,每人談十分鐘都還是湊課間,當時實在沒時間了,下一節我有課。”莫老師說的是實情,每個孩子都只哭不說話,他恐怕課都沒法上了,他做一個班的班主任,教三個班的物理課,要備課要批作業,工作量不小。
“與其匆匆忙忙談一排孩子,不如扎實做好眼前一個孩子的思想工作,貪多求快的結果常常適得其反。”安德榮阻止莫老師的辯解。
“出了事往前找原因,當然都能找出說辭。”莫老師反對安校長“貪多求快”的判斷,“我的談話如果‘常常是適得其反的,我怎么能連續這么多年班級成績遙遙領先,說得不好聽些,我們做老師是靠學生成績吃飯的,效果決定方式。”他鼓起勇氣再說一句,對教好學生成績、和學生談心他有信心。
“你這種心態害了你呀,以為自己的經驗適合所有孩子?”安校長憤怒起來,眼下發生的事情多么可怕,為什么還要辯論?昨天他在領導們的群聲質疑中邊匯報邊檢討,難道就沒有維護自己的話要說?可是說不得啊,人命大于一切,一定是錯的因才會有錯的果,即便是事后諸葛,往前倒推,也要找出個原因來。
“我說過多少遍啦?老師吃的是良心飯,你有沒有從根本上把每個孩子當成自己孩子對待,能不能再多一點責任感、再多吃一點辛苦?想想看,如果是你自己孩子,你怎么辦?”此時此刻,安校長不能站在莫老師立場上說話,就如昨晚領導們對他除了批評還是批評,他從前取得的顯赫成績在這次意外面前不值一提,他也完全理解。“問題出在哪個班級、哪個學生身上固然有偶然性,但是為什么出在你的學校,一定有必然性,這是你要深刻反思的地方!”昨夜,領導就是這樣截然斷定他那未知的漏洞。
安校長同樣把這句話送給莫老師。事到如今,被多說幾句又怎樣,如果能換回童僮站在面前微笑,他愿意接受更嚴厲的批評打擊。
“如果是我的孩子,我連找他談話的時間都沒有,我一天十七八個小時在學校里。”莫老師低著頭,滿臉通紅,“你看我早上六點鐘就到學校了,吃完午飯在教室里看午休,晚上自習課結束,寄宿生休息關燈檢查結束,十一點半我才能到家,周末又要上班,我跟我兒子見不上面,他今年讀初三,開學到現在我和他沒同桌吃過一頓飯。”人命當前,莫老師忍不住辯解,他的工作,付出的哪只是時間?原本只是家長把孩子的成績交給他,他盡心負責;現在把一條人命也要交由他負責,他承受不起。
安校長拍桌子道,“到這個時候了,你就不能說說自己的問題?如果你的工作做周全了,會出這樣的事?”這句話像在自我批評。早該聽李泊客的話,把防護欄裝上,安德榮你太自以為事,既然欣賞李泊客,為什么要否定他的提議,既然做校長,為什么不務實一點,你的學校難道不唯分數論?不參加全市排名?不會因為考不好而挨上級批評遭家長批斗?他聽到心底質問的聲音。
“出了這種事,你就是教出一百個高考狀元,都是你的責任,人死不能復生,你看清現實啊!”安校長痛心疾首,對眼前這名“學科帶頭人”高聲起來,“他考試不好,你找他談話,他哭著出辦公室,周末回家一趟,下周來學校就跳樓了……他家人說手里有他的日記,說你罵了他……你說,你說,你準備怎么說清楚啊?”
“我,我盡力了,我對學生算得上體貼照顧,一句狠話都沒說。”莫老師繼續爭論,做不負責任的逃兵,“特別是童僮,學習成績不算差,人也乖巧,安安靜靜不惹事不鬧事,任課老師都喜歡他,還指望著他拉高班級平均分呢,怎么舍得罵他呀!不罵,他都積極得很呀!”
安校長怒氣沖沖,一雙通紅的眼睛瞪著他不說話,心疼那個銅鈴大眼的男孩,讀了這么多年書,怎么把腦子讀呆了?就不能和同學老師聊聊、說說心里話嗎?成績再重要,哪比得上生命啊!心里又著急眼下大家怎么過這一關,不管是不是莫老師的事,事發在他班級,班主任肯定要撤,職稱評級要暫停,可惜了一個教學人才的前途,但如果結果能這樣處理就算阿彌陀佛,盡力保住莫老師還能在教學崗位上發揮特長吧。自己呢?上面說,會第一時間協助他首先處理問題,其余的事暫時不談。
現在當務之急把這件事情處理好,一是溝通家長,穩定對方情緒;二是查明事情來龍去脈。千萬不能在問題沒弄清楚之前就鬧得滿城風雨,現在各類媒體參與的力量可怕得驚人,傳播發酵,能掀起滔天巨浪。
蝴蝶兩片巨大而柔軟的雙翅上綴滿了彩色斑點,像宇宙星辰,像幽暗黑夜,像鉆石珍珠,像明亮燈盞,像沉默的嘴唇,像無數雙眼睛。它們奮力向上扇起,向下彎曲,推開隱形的堤岸,抽象繪制的無數種“可能”一起跟著搖晃變幻——大鵬展翅,欲飛九天。巨大的欲望向上,天空的俯視便如颶風、海水,灌滿它們,使它們奮力掙扎又搖搖欲墜于每一個剎那。翅膀一次次將欲折斷——柔軟亦有彎折的極限。
課間休息十分鐘,安德榮竟然在座椅上睡著了,夢到蝴蝶從空中墜落大海,他急得喘不過氣,一個憋勁,撲騰一下醒了過來。校長室窗外校門口場地上遠遠聽著鬧哄哄的,空中有兩葉黑白巨翅隨風起舞,他站到窗邊定睛一看,心中一慌,該來的還是來了。
幾十號人,扯著兩面白底黑字旗,一面寫著“殺人償命”,一面寫著“還我孩子”。保安正攔著不讓他們進學校。安德榮連忙通知局里,局里準備的談判小組組織得怎么樣了?又通知莫老師先回避,不要在對方情緒沖動的時候談論任何事情,避免激化矛盾,耐心等待對方把悲傷憤怒發泄掉再說。
迅速趕到的學校臨時加強保安小組,穿著定制的耀眼橙色馬甲,帶著頭盔,舉著叉棒站成一排,離沖動哭喊的人群保持一米距離、圍成一圈。他們像水做的圍欄,流動著,前進著,哭鬧的人群擠向哪里,他們就跟到哪里,不碰觸不出聲不讓他們進校門。校長有令,他們可以哭可以鬧,不可以進學校,如果他們進了校門,“保安小組”全體處罰!如果和家長發生沖突,“保安小組”全體處罰!學校里還有數千名學生,都是家里的獨寶寶,“學霸”也罷,“學渣”也罷,都是珍貴的生命,一定要保護他們的安全,切不能發生新的意外。
花圈帶來了五六只,一字排開,靠在不銹鋼自動伸縮大門上,一個中年婦女躺在門口地上嚎哭,幾個粗壯的男人開始推搡保安,嚷著要校長和班主任出來償命。保安們回避著、瑟縮著、抵抗著,他們是臨時組成的保安隊,除了個別本就是保安,能鐵石心腸、目不斜視外,其余大部分是學校的保潔員、駕駛員、炊事員,四五十歲,家家都有上學的孩子。個別心腸軟一些的,聽那婦女嗚哩哇啦的哭聲,已經紅了眼睛。老師罵孩子,罵成怎樣才能讓一個活潑潑的孩子不想活了?像新聞視頻里流傳的老師扇學生耳光嗎?那樣的老師著實可恨,家里都舍不得冷、舍不得暖的,哪能叫你這么狠揍?但,前一陣子新聞里,有個孩子被媽媽罵了一頓,在車水馬龍的路上就鉆出自家騎車跳了天橋,留下媽媽一個人在路邊捶胸頓足。哎呀,現在這些孩子呀!罵得重了還是輕了,到底誰能說得清?保安們各自猜想著,眼睛盯著眼前的人群,腳步緊緊跟著。
安德榮只站在窗前看了一下,就縮回了脖子,不能讓下面叫嚷的人看見校長室窗口的人影。關機前,他打了一系列電話,打了110,打了上級電話,匯報現在的事態,打了學校辦公室主任的電話,讓他立刻出馬,去人群里觀察事態,做安撫準備。剛才樓下返回的消息說,有人從現場嗚哩哇啦聽不懂的哭腔、怒吼中翻譯出,對方孩子的父親還在監獄里服刑,但監獄外的兄弟們剛才已經接到現場小兄弟的電話,給哭暈幾次的嫂子打了電話,說就要聚集人馬趕過來。
安德榮吸了一口冷氣,這樣看來,對方的母親倒是溫和的,來之前沒有通知那些“兄弟們”,那幾個粗壯漢子的親人拼命的架勢恐怕是想爭取談判的先機。人死不能復生,什么樣的言語能釋放一個獨立養兒的母親的悲傷,怎樣的賠償能安慰到一個哭得死去活來的喪子中年的絕望?怎樣的談判能夠不劍拔弩張?安德榮替這個母親難過,把孩子培養成學霸一定是下了苦功夫,在他身上寄托了重要期望,他也是家長,家里也有一個在學海中奮力的孩子。也替孩子難過,把眼光放遠至一生,眼前遇到的困難都微不足道,可惜他看不到了。他希望孩子母親盡情地哭,在短時間內盡可能哭掉最多的哀傷,這樣他們談判的時候才更有可能心平氣和、風平浪靜,才能互相不被可怕的情緒牽著鼻子走。
安德榮又給莫伯紳打電話,“你去詳細了解一下童僮的個人情況!”
其實莫老師也一直沒閑著,他“躲”在一個僻靜的教室里,把與童僮可能有交往的同學一個一個喊來問話。這間教室原是學校的心理咨詢室,設在學校“百年桂園”深處一間閑置的老圖書館里。剛才校長打電話,氣急敗壞地問他童僮的家庭情況和他匯報的怎么有不同,童僮的入學信息上寫的是母親自由職業,父親自由職業,莫老師并不知道他的父親在監獄中。犯什么事,什么時候入獄,多少年?到底什么自由職業,莫老師沒有追問過,從前覺得沒必要,現在也還是覺得沒有大必要,三百六十行,都是合理的謀生,誰會在資料里瞎寫?他也不是火眼金睛,他只負責盡力教書,給孩子好成績去爭取時代下的好前程,負責不了幾百號學生的家庭。但轉念想想一旦上面問起來,回答“不知道”,怕要責問他對孩子家庭不夠了解。
童僮乖巧,看不出半點他所身處的環境與別人不同!心疼,這孩子平日謹慎安靜,心里竟藏著這樣大的秘密,實在不能只怪他承受能力弱啊。莫不是家庭遇到了什么變故?莫老師好像摸到了一點“破案”的蹤跡。
莫老師把提供信息有交叉的幾個同學聚在一起談,從斷斷續續的信息里拼接出一個模模糊糊的大概:
童僮哭著回到教室,晚自修結束后他在被窩里打手電筒,上鋪的于明問他怎么還不睡,他說“寫日記”,“他愛寫日記,有一次聊天說過他寫好幾本日記呢,難怪作文寫得那么好。”
第二天輪到兩周一次的周日假,寄宿生們按例在周六下午課程結束后回家,童僮和同鎮的郭小君乘一路班車回家,郭小君說“我考了班級倒數,心想回家肯定要挨一頓罵,誰知童僮考得那么好,竟然也憂心忡忡,‘他說這次又考砸了,上次已經挨過罵,我還以為他故意在我面前這么說呢。”
譚星晨說“聽說童僮母親會罰他下跪,自罰耳光,退步十名一個耳光,也不知這次罰了沒有。”
孩子們七嘴八舌說著,互相提供驚人的信息,又彼此驚訝于另一個同學的所知,“我爸爸兇,我媽媽巨嘮叨,打是有的,但下跪倒還沒有。”“童僮可認真的,晚上在被窩里看書要看到很晚,他估計受不了努力還退步吧。”“總會有人進步有人退步的呀,下次努力唄。”“誰家爸爸媽媽不罵孩子呀,我爸爸媽媽從來沒有表揚過我,總是說我這不好那不好,我還是要努力活得快樂。”
同學們互相討論、積極附議,補充自己所聞、體會,彼時彼刻他們比往日老師反復強調的更獨立體會出活著是好事是希望。“老師是細心善良的人,平時能顧及我們的尊嚴、秘密、面子。”孩子們順便這樣認可哀愁濃重的莫老師。
莫老師給安德榮打電話,簡要說了一下目前收集到的信息,學校里所得信息,自然都指向成績和與此相關的事務。
“為了確保這些信息的可參考性,經過孩子們同意,我錄了音。”他覺得事情有可談余地,悲劇發生在學校,根源也許在其他地方,在更久日子的積累里。“學生們說可以為我作證,我平時待他們雖然嚴格但友好。”停頓了一下,莫老師說,“他們說,他們說我像他們的爸爸!”
“爸爸,你要真是他爸爸就好了,我們也不需要在這里討論這些!”安德榮苦笑,莫老師的迂腐在這種時刻完全體現出來了,指望學生的幾句贊揚能解決問題。
“人家白紙黑字寫著你罵他呢,莫老師!”安德榮語重心長,“你還要先想辦法弄清楚他到底怎么寫的吧,再說爸爸的事”。
“日記本你能弄到嗎?”說日記寫了好幾本,安德榮忽然想到了線索,日記里肯定寫到不只一個老師,也不只寫了同學、家長。日記里藏著學生真正的內心世界,能曝光更多也能說明更多,在這個事件中這把雙刃劍到底有多鋒利,他們竟然忽略了。
“日記本被他家長拿走了!”莫老師懊喪極了,事發第一時間忙著接待家長,沒有保護童僮的東西,當時家長們還沒有失控,一些遠親幫童僮收拾東西,莫老師還不知道日記本的事。“他們一定要把談心說成罵,我也沒辦法,我好奇‘罵是日記里的原詞嗎?是童僮瞎寫,還是家長瞎說?如果是童僮情緒化的用詞呢?”
關于日記本,很快有了新的跟進,安校長的律師鐵友非常肯定地告訴他,如果家長認為日記記載的莫老師“罵”孩子致使孩子陷入絕境,那么日記本一定需要交出取證,不可能放在他們手里,聽憑他們隨便說。但問題是,如果的確用詞是“罵”,莫老師怎么自證?談心時有其他同學、老師在場嗎?有錄音、視頻嗎?
童僮上鋪同學出于內疚自責,主動向老師匯報自己因為好奇曾多次偷看童僮的日記,這位同學覺得童僮悲觀絕望的人生態度不是源自某一次考試,而可能源自無數千奇百怪的小事,譬如:宿舍十點鐘關燈的規定、頭皮屑紛紛而“海飛絲”無法治愈、永遠來不及完成的作業、傳遞本子時被前面同學扔飛了作業本、媽媽洗衣店里十幾萬元的機器壞了、皮衣皮鞋皮手套來自活生生的動物皮膚、公交車上老大爺和孕婦爭搶座位、全球變暖北極熊將在五十年內消失、同學們都以為他是學霸而他學得艱難、抖音上令人心動的美麗小姐姐其實是一個中年大媽、特朗普說美國利益優先、每一個同學都是競爭對手是隱藏的敵人、心里的話還沒說完日記本快寫完了……
李泊客查學生檔案,整理出一份童僮初中同班同學本校名單,召集他們私下聊天。很快他向安德榮提供了驚心的消息,也是令人欣喜的救他們命的消息,童僮的初中同學們說童僮有抑郁癥,初三就吃藥了,高一開學初不久家人還帶他去過醫院。市區只有兩所醫院治療精神問題,安德榮腦海里迅速搜尋可以聯系的熟人,馬上去查。十六歲的孩子,經歷了什么?
李泊客又補充,童僮的父親是經濟犯罪,從前是公司會計,性格相對比較內向,沒有復雜社交,他的“兄弟”們怕是唬人的說法。如果情況確如預料,那么學校門口的哭喪就是最難看的場面了,后期沖突升級的可能性比較小。盡管不能放松警惕,安德榮還是稍微松了口氣。
語文老師提供了童僮的隨筆本,有好幾篇無主題隨想記敘了生活細節,童僮的文字帶著強烈的青春期情緒,有些言語“事后諸葛”地理解頗能對應某些可能的現實,他自認為活在“深淵”中。
十六歲的孩子,“深淵”是幾歲開始的?什么樣的“深淵”?
好了,已有信息里的蛛絲馬跡倒過來往死者生前推去,似乎都能貫穿起來,通往一個已知的必然的結局,這結局在某些種子埋下時,就預見了未來某日五樓陽臺上那展翅一躍。在孩子五歲時、十歲時、十五歲時……的夢里,蠕動的小蟲子啃食哀愁的葉子,逐漸長大、作繭自縛、生出美麗的翅膀和決絕勇氣……
云上中學由校長、班主任、教導主任、辦公室主任臨時組成的“破案小組”經過了起初的慌亂后,慢慢鎮定了下來,通過細節排查,隱隱摸到了線索。他們像一群尋找真相的警察,也像一臺無情的透視器,睜著機械冰冷的雙眼,在生死大事面前,要掀開一個孩子的短促人生,露出內部不堪的秘密,以自證自救、自尋希望。
110打過后,警車來了,停在對面馬路邊。校門口躺在地上的母親已經哭到喉嚨沙啞,被幾個親屬婦女扶著,她們接替她哭喊;親族大漢們還在叫罵,和保安繼續糾纏;他們對孩子可能從未表達過的愛、從未聊過的事,變成了眼下洶涌的眼淚和肉體的搏擊、喉舌的叫罵。他們開始燒紙,一沓沓黃色紙錢被扔進火堆中,迅速燃成一團紅光,燃燒后的灰燼被火焰的熱氣推向空中,在校門口上空飛舞。十一月的深秋伴著撕心裂肺的哭聲和盤旋向上的灰煙,顯得特別寒冷。
安德榮望向后窗外的校園,這幾天匆忙裝好防護欄的教學樓,從一樓到五樓的陽臺,畫滿了銀色小方格,頭伸不出去了,這光芒景象配著園林式景致的校園鐘樓、亭臺,現在看來竟然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刺眼。在教學樓陽臺上安裝防護欄和在學生心里安裝防護欄兩件事之間,他選擇了簡單的事做。他愧疚地知道,這就是務實,也是高效,是眼前就能看到的安全,是他早該做的事,也是亡羊補牢的正確。但是,如果,如果誰能及時看見童僮的天空里曾經有憂傷的小蟲噬咬、那些斑斑洞跡,也許就阻止了一只斑斕憂傷的蝴蝶誕生,阻止了后來的凌空一躍,那么眼前校門口簇擁的也許是歡呼的人群——學校在各科教學方面成績優異、屢屢獲獎,每當那時校門口會對外懸掛紅色宣傳標語,吸引家長駐足。
可是誰又看見了呢?
遠處,忽然有一只蝴蝶從風景里飛出,穿越綠色草地,迎著微風向上,飛到四樓高處,顫抖著停棲在安德榮眼前嶄新的不銹鋼防護欄格子上。夢幻的美景、斑斕的野心、有限的時間、狹窄的空間和毀滅性的上升在這剎那間安靜地聚集在一起,暫停在令人憂傷的銀光中。一時間他感到有許多話要說,卻找不到用來講述的嘴唇。只盯著它,沉默的蝴蝶,翅膀上繁密的花紋,左右對稱,左右對抗,燃著鉆石般的星火——它想說些什么嗎?
再定睛一看,是一片紙錢的灰燼,落在防護欄格子上。
責任編輯 郭曉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