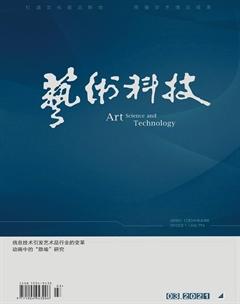淺析醫療類紀錄片的真實性與影像的力量
摘要:“上蒼給了我們生命,我們用奉獻去擁抱。”醫療類紀錄片的出現,打開了紀錄片類型的另一扇大門。導演使用鏡頭語言再現當下中國的醫療環境,真實地反映當下中國的醫療狀況。充滿社會意義的紀錄片本身就自帶話題,其影像的力量也不可小覷,這也是我們熱愛紀錄片的原因。
關鍵詞:紀錄片;真實性;影像
中圖分類號:J9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1)03-00-02
自20世紀90年代新紀錄運動以來,我國出現了許多關注社會發展的紀錄片,這些紀錄片背后的導演渴望發出自己的聲音,希望擺脫當時紀錄片普遍宏大敘事和帶著政治意識形態語言的創作境況。他們與官方話語對立,將目光由上而下地聚集,對普通百姓生活與社會發展問題進行采樣與轉述。目光多對準群眾生活、普羅大眾,以表現社會快速發展中的問題,同時也為受眾通過紀錄片更加獨立和全面地了解和思考現實社會提供了視角。醫療類紀錄片在我國出現得越來越多,其記錄的內容也一直受到受眾的歡迎,如捕捉生死時速的《急診室故事》、彰顯悲歡離合的《生命源》、關注婦產故事的《生門》等等。
1 紀錄片的真實理念
紀錄片標榜真實。紀錄片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直接電影”的影響。許多紀錄片導演都力圖做“墻上的蒼蠅”,做到純粹客觀地記錄。但有些導演仍不認同純粹的旁觀,他們認為攝像機和導演對記錄的影響是不可避免的,應做到對“真實”的不斷靠近。《生門》的導演陳為軍于1969年出生在山東日照的一個農村地區。他出生的那個時期,生兒育女是一件艱難而自然的事情,黃土地上覆蓋著厚厚的麥草灰,孩子就像成熟的果實一樣生在地上。一個深秋的下午,他掉進了一堆灰燼,父親拿起剪刀,在煤油燈上進進出出,輕輕一聲,他就斷了臍帶。40多年后,陳為軍和兩位攝影師一起,想拍一部關于當代中國孩子出生的紀錄片。這部紀錄片持續了500多個小時,記錄了80多個家庭。在那之后,紀錄片《生門》進入了電影院,這部紀錄片想讓每一個人都試圖重新理解婦女生產的不易。
紀錄片內容的真實性是文體技巧與受眾勾連的結果。有人說,紀錄片的“逼真效果”取決于受眾對電影內容的認可和接受程度。從這個意義上說,紀錄片文本與客觀存在之間的巧合在于受眾的“真實判斷”。事實上,受眾判斷紀錄片文本是否真實,反映了生活的基礎。而從客觀和現實的角度來看,紀錄片的內容永遠不會接近客觀生活本身,并且與其反映的客觀事物不一致。因為日常生活中的事物被剝奪了,所以它們是主觀的。在紀錄片的世界里,我們只對一個人、事件和事物感興趣,并成為敘事主體的對象。如醫療類紀錄片以醫院為觀察點,并跟隨醫生的腳步記錄眾生相。醫院的各部門是突發性醫療事件、直面生命脆弱與生死別離的地方,在片中,我們可以看到無法判斷真實情況的病人、醫生的認真和面對突發狀況的應急反應、護士的八卦和考核狀況……這些出現在醫院這一公共機構的一系列事件無不映射了同一個語境:社會發展變革下,人們對自我生命生存尊嚴的維系、對自我生命的珍視,醫院面對利益與道德的矛盾困境等等。
紀實的內容具有主觀和虛構兩個方面,這意味著紀錄片的敘述是修辭的。紀錄片是真實事件的見證人。“讓人想起”的行為確保了紀錄片的文字內容反映了客觀和真實的可靠性。故事聚焦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婦產科的醫療類紀錄片《生門》,通過孕婦的生產、真實的鏡頭語言,展現出生死一線的場面,當然還有人們迎接生命降臨的喜悅。受眾通過紀錄片更好地了解社會和生活以及生命的意義,這也是紀錄影像的力量。《生門》聚焦婦產科這一特殊的科室,婦產科是一個窗口。與娛樂性表演的綜藝、肥皂劇不同,紀錄片秉持的“真實性”讓人們更容易被觸動,因此人們傾向于去相信在這些紀錄片中出現的內容。無論在農村還是在城市,生命的誕生都會對個人、家庭和社會產生不小的影響。作品中反映的社會生活是否具有真實性,只能有一個客觀的衡量標準。
紀錄片的真實性與藝術性有相輔相成的辯證關系。真實性是紀錄片的核心,是其與其他影片的本質區別,但在創作過程中也需要借助故事片的敘事策略來呈現內容。這種藝術加工仍以真實為前提,只是采用一些虛構策略以呈現更加真實、生動、有趣的內容。新媒體時代,紀錄片的故事化水平日漸提升。紀錄片如《生門》也會運用鏡頭內容去講故事,這些發生在孕婦身上的故事通過鏡頭紀錄了下來,盡管使用了故事化方式,其達到的傳播效果卻因人而異;《人間世》的敘事基礎來自醫院真實發生的故事,醫生是紀錄片的主體,患者每天都在更新,體現人情冷暖的戲碼每天都在上演。所以在選題上,新媒體紀錄片應該更傾向于選擇故事素材豐富、方向性更加明確的主題。
人情味和回歸生活才是吸引受眾的要領。對于創作者來說,影片的受眾是人,能帶去影響的也是人。滿足人的自我表達的需要,體現影片的人文關懷,在題材和主題的選擇上突出生活本味,講好老百姓的故事,不僅能節省不必要的成本支出,方便之后的視頻剪輯,更能把紀錄片推向千千萬萬的年輕人,讓紀錄片被更多人接受和喜愛,發揮紀錄片在新媒體時代的別樣價值。
2 紀錄影像的魅力
記錄歷史是紀錄片的主要任務。通過紀錄片記錄的內容是真實的,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更好地保持了原有的生態。紀錄片的魅力也在于過程記錄。由于“解說加畫面”中的畫面只是一個象征符號,因此受眾在欣賞它時,必須非常依賴分析和想象來理解和接受,這勢必會減弱受眾對其接受的效果。此外,它的解說過程強調語言解釋系統,使解說內容充滿了講解的意味。使用記錄方法的完整記錄過程使觀看者能夠輸入特定時間和空間感知體驗記錄的內容。受眾繼續在觀看中積累,逐漸聚集并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感染。在紀錄片《生門》中,李雙雙的故事引起了很大的爭議,面對一個很有可能發育不健全的小生命,面對不知定數的下一胎,家人可能要承受更多風險和痛苦,讓人們意外的是,父子倆糾結的重點在于最后是否會人財兩空。相對于救孩子時的糾結,李雙雙家人手上的金戒指才是許多受眾關注的重點。在如此發達的社會,人與人之間還是缺乏互相的理解,對于他們來說引產可能不是他們的本意,只是面對未來不為所知的黑洞,不是誰都有勇氣面對的。除了這些讓人感觸特別深的紀錄片記錄的過程以外,人們對生育這個問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對生活和生命本身的意義也或多或少有了感悟。
我們必須在拍攝前做好長時間的準備,必須非常清楚拍攝什么以及如何拍攝,明確在這種環境下會發生什么、誰將出現在鏡頭中以及開發過程,怎么構建影片,不能違反它的真實性。在早期的工作中,與攝影師建立良好的關系非常重要,你應該用心去體驗敘事對象,把自己置于其中,并“跟隨”上帝。在創作紀錄片的過程中,敘述者總是將自己的藝術追求或生活觀念投射到主題上。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創作者與主題之間的共鳴和相互作用決定了紀錄片過程記錄的質量。紀錄片主要人物的選擇十分重要,應把一些典型案例呈現給受眾,若只是普通的故事,是吸引不了受眾的,所以,人物、題材、主題等的選擇都是必須慎重考慮的。在《人間世》第二季中,9歲的王松茗做了一場手術,醫生鋸開他的腿,拿出骨頭,切除上面的腫瘤,然后把沒有癌細胞的骨頭再放回他的體內。手術后,他哭著說:“我的腿好酸。”但這是他唯一保命的方法。這些感人的細節和情感的挖掘給受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用紀錄片方法記錄過程需要我們小心謹慎地拍攝,用紀錄片的方法記錄過程,不是攝像機拍攝,我們需要進行深入的采訪和情感的挖掘。2019年年初,曾感動全國人民的紀錄片《人間世》迎來了第二季。這一次,其播放的內容依然讓數百萬受眾哭成了淚人。猶記得,第一集的鏡頭對準的是一群孩子,他們并不是普通的孩子,而是一群得了癌癥,正在跟癌癥對抗的孩子。他們當中,有的人坐上了輪椅,有的人失去了胳膊,有的人正在經歷漫長的手術,有的人在要命還是要腿之間抉擇……但沒有人說放棄。
在以紀錄片方式記錄過程時,永遠不關閉機器并且不改變攝影師的生活環境是很重要的。“永不關機”意味著它會立即打開,一切都將被拍攝,而不是等待它處于危險之中。當按下相機背面的紅色小按鈕,準備召回、追蹤、反映和總結時,不能改變主體熟悉的生活環境來記錄自己的生活狀態,否則會帶來虛假人物,在人為的氣氛里,人們是不可能保持自然的。要善于捕捉細節,細節揭示了角色的性格,揭示了角色的思想。
恩格斯說:“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1]恩格斯呼吁在環境統一中塑造典型人物,這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典型現實主義理論的重要方面。紀錄片《生門》中,“李家福”是這個醫療故事中至關重要的人物,這個名字甚至成了婦產科的代名詞,甚至有許多受眾想要到武漢中南醫院找李家福咨詢。做產科醫生25年的他一年操刀的手術有近千臺,其工作量之大是普通人難以想象的,這對當下我國醫生的正面形象作了闡述。《生門》中,還有許多產婦個人的例子,中南醫院作為武漢市五家急危孕產婦搶救和轉診中心之一的三甲醫院,這里大多數的住院產婦都是各地轉來的疑難危重產婦。大家對夏錦菊這一人物可能留有深刻印象,她在術中相當于全身換血四遍的場景仍然在腦海中揮之不去,她算是真正走過一趟鬼門關的“戰士”。此外,許多導演還將捕獲的細節融入紀錄片的敘述中,用它來創造懸念,營造氛圍,創造一種意境,使紀錄片充滿魅力。
3 新媒體時代紀錄片的發展
紀錄片若充斥著明顯的導演主觀話語,成則感染受眾,但違背真實客觀原則;反則會引起受眾不滿,表現為對導演視角與話語的反抗和拒絕。不同于文藝片和紀實類的電視節目,紀錄片要隱去拍攝者的主觀意識和情感流露,創作者不能如散文般隨意抒情。以醫療為呈現視點的影片,《人間世》的語義更為明確,有較強的抒情性,相較于對醫患關系的冷靜思考,受眾更多接收到的是一種感性。而《急診室》則是以醫院急診部為觀察據點,排列展示看似散亂的片段化人物事件,將它們整合在一個公共空間里。這些簡單的事件人物羅列,看似不帶情感的冷靜觀察,構建出全景觀式的社會圖譜,其話語既在這個公共空間內,又包含更大的空間——個體所生存的社會和社會關系,引導受眾去思考畫面真實下更深層次的意義,避免明顯而狹窄的話語引起歧義而引發大眾的反抗。
紀錄片是一種以真實為核心、以真人真事為表現對象的影像記錄形式。新時期,隨著新媒體技術的廣泛應用,市場細分愈加明顯,現代人的生活和需求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傳統模式下紀錄片的生產方式和傳播模式都有所革新。新媒體時代,數字化影像存儲技術成熟、信息量爆炸式呈現、視頻創作門檻變低、受眾范圍擴大、交互式體驗和信息內容娛樂性日漸增強……手持移動設備,人們可以隨時隨地傳播和接收信息,交互式體驗使得大部分人都掌握著信息選擇權和話語權。低成本、碎片化、跨平臺和快速傳達等傳播特征都預示著新媒體的影響力正在逐漸提升。
傳統的傳播渠道主要有報刊、廣播、電視等,其中報刊只能呈現文字和圖片,廣播只能呈現聲音。新媒體時代的大眾傳播媒介進一步發展,有手機、電腦、平板等,呈現的信息形態更加豐富,任何設備幾乎都能展現包括聲音、文字、圖片、影像、動畫等在內的所有符號形式,并且實現這些符號在同一文本中的融合,如騰訊旗下的微信公眾平臺,能實現和特定群體的圖片、語音和視頻的全方位溝通和互動,這對紀錄片的宣發創造了更多靈感。在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當下,媒體融合對受眾來說不再是晦澀難懂的專業詞匯,而是成為一個大的信息時代背景,時刻影響著受眾日常的信息傳播與接收。媒體融合是傳播學中一個不會過時的話題,在未來的信息傳播中,媒體融合的趨勢只會向前發展而不會后退。隨著不同媒介功能的逐漸融合,紀錄片的傳播渠道更加多樣化、傳播速度更加快捷、傳播的成本更低,紀錄片的影響力也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從傳統意義來說,過去的紀錄片都可理解為電視紀錄片,它以欄目化的定時單向線性傳播模式為特征。紀錄片的格調偏高,面向的受眾往往是具有較高文化層次和較強理解能力的少部分人,受眾面比較狹窄。隨著新媒體技術的廣泛應用,受眾需求和市場需求都發生了劇烈變化,傳播手段和方式的變革更是改變了以往紀錄片的生產方式、傳播模式和影響力,傳統媒體下紀錄片的敘事策略不再適應需要,急需轉變以迎接新的挑戰[2]。
4 結語
醫學紀錄片除了真實客觀地記錄醫生的工作生活和醫院的運行狀況外,還介紹了醫院作為服務病人所采取的方便措施,傳播了相關的健康教育知識,尤其是醫護人員更有親和力的一面,對緩解我國醫患矛盾具有現實意義。
這個世界從來不會因為醫院的存在就讓我們更加珍愛生命,在生活中,人們不得不從事危害身體健康的工作,也有人在生命面前作出相應的舍棄選擇,只是為了活下去。醫療類紀錄片正是把一個個真實的故事記錄下來,向人們“展現一個真實的人間世態”。
參考文獻:
[1] 朱娜.試論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及其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影響[D].貴州大學,2008.
[2] 劉淑卿.新媒體時代紀錄片的“微”特征探究[D].上海師范大學,2016.
作者簡介:鄭丘成(1995—),男,江蘇徐州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影視編導與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