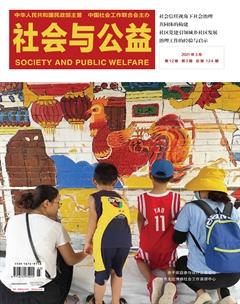家庭抗逆力視角下社會工作介入精神障礙患者家庭的服務研究
張明月
摘 要:精神障礙是指大腦的機能活動發生紊亂,導致認知、情感、行為和意志等精神活動不同程度障礙的總稱。當今社會,競爭不斷加強,社會壓力劇增,不同類型的精神疾病總量呈不斷上升趨勢,精神障礙患者已經成為社會工作者服務的重要人群之一。本文從家庭抗逆力視角出發,梳理精神障礙患者家庭所面臨的困境,以及與家庭抗逆力相關的理論研究,改變傳統的以缺陷為本的觀點,重視家庭本身所擁有的力量,從家庭內部及外部探討如何增強精神障礙患者家庭的抗逆力以應對各種挑戰。
關鍵詞:家庭抗逆力;精神障礙;社會工作
2019年,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黃悅勤教授等在《柳葉刀·精神病學》發表研究文章,對中國精神衛生調查(CMHS)的患病率數據作出了報告。在中國,抑郁癥的終身患病率為6.9%,12個月患病率為3.6%[1]。根據這個數據估算,到目前為止,中國有超過9500萬的抑郁癥患者。2020年10月9日,世衛組織舉行新冠肺炎例行發布會,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指出,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衛生日,有近10億人患有精神障礙,每40秒就有1人死于自殺,然而全球范圍內只有少數人可以獲得優質的精神衛生服務;在中低收入國家,患有精神、神經和藥物濫用障礙的人中,超過75%的患者沒有得到任何治療,應大規模增加對精神衛生服務的投資。可見,精神疾病已經成為人類的第二大殺手,針對精神疾病開展的探討與服務研究越發得到廣泛關注。
目前,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出發探索如何促進和提升精神障礙患者的社會融入、再社會化、社會支持、社會地位等。葉倩怡從系統視角出發,主張應建立多系統聯動的支持網絡來為精神障礙患者提供更周全的照顧,多系統包括社區、法律、政策以及思想觀念的轉變[2]。相對外部力量對于精神障礙患者的支持作用,增能視角更強調服務對象自身的能力。胡思遠、楊锃認為,賦權過程包括對無權狀態的省察、獲得賦權的動力、從他人處獲得支持、獲得有效資源的途徑以及社區參與[3]。同樣是基于賦權視角,張木明、豐行也倡導發揮個體的作用,推行“個體主動”與“外力推動”的模式[4]。與賦權視角相似,優勢視角也同樣注重個人的力量,強調人是有能量和資源的。蔣美華等人就提出不要再將精神障礙患者置于無能地位,要發現他們的優勢和資源[5]。除多視角外,楊曉東在針對精神障礙患者的再社會化研究中提出了一種多學科合作治療方法[6]。針對精神障礙患者這一特殊群體,已經有很多學者進行了理論與實務研究,包括針對患者個人能力的提升以及周圍環境的改善,卻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微觀系統——家庭。患者最終是要回歸家庭的,家人也是陪伴患者最多的他人。因而,想要很好地幫助患者不僅要關注個人、社會,更要充分發揮家庭的作用,提升家庭應對危機的能力,增強家庭抗逆力。
一、精神障礙患者家庭困境
(一)微觀支持系統方面
精神障礙患者的家庭支持普遍單一且不穩定,由于精神障礙患者有時會出現狂躁或情緒失常的問題,親屬的陪伴不可或缺,但長期的消耗不僅會給家庭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而且會給照顧者帶來嚴峻的挑戰,很多照顧者在這個過程中身心俱疲,不堪重負。
(二)中觀支持系統方面
社區支持缺乏,社區中對精神障礙相關疾病的宣傳不到位,社區居民缺乏對精神障礙的認識,將精神障礙認作是“晦氣”事,唯恐避之不及。同時,社區支持網絡未能及時建立,精神障礙患者家庭得不到社區支持,無法從社區中獲得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幫助。
(三)宏觀支持系統方面
首先,社會保障制度以及相關政策不夠完善。精神障礙患者的權益保障、經濟支持依舊存在很多漏洞。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自2012年才開始為精神障礙患者提供醫療保障,這種保障覆蓋面窄、水平低,實際收效有限。其次,缺乏相關社會組織的支持。醫院對于精神障礙患者只能提供病理上的治療,而在心理、生活方面則需要社會工作者、心理咨詢師等專業人士的協助。但目前還沒有具體的規章制度來明確這類社會組織應如何參與到有關精神障礙患者的服務中。我們所接觸到的服務主要還是一些政府購買服務或是公益性活動。
二、家庭抗逆力研究
關于抗逆力的研究最先興起于美國,當時關于抗逆力的研究焦點在于個人,主要關注個人特質,認為性格、智商等個人特質都會對抗逆力產生影響。隨著研究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發現,那些優秀的個人特質能否出現與人際關系具有很大關聯。以兒童為例,如果兒童能夠在家庭或者社會中遇到一個給予他關愛的人,那么他在面對困境時的抗逆力就會比其他未得到關愛的人更強一些。
對于家庭抗逆力的研究始于針對兒童抗逆力的家庭影響因素的分析。家庭抗逆力相對于抗逆力而言更強調家庭,是一種以家庭為單位的應對與適應的過程[7]。家庭抗逆力理論改變了一貫的以問題視角去看待家庭的方法,將注意力從關注家庭缺陷轉向發現家庭存在的優勢和資源,試圖去理解家庭如何在巨大的困難與壓力中繼續生存。沃什(Walsh)的家庭抗逆力系統理論模式是經典模式之一,他將信念體系、組織模式、溝通過程總結為家庭抗逆力形成的三個關鍵過程,家庭抗逆力就是從這三個方面出發去面對困境的能力[8]。同時,他將這三個關鍵過程作為臨床評估與介入工作的參考,以指導具體實務工作,應用于幫助面臨多重壓力、創傷性事件等家庭的抗逆力恢復。國內關于抗逆力的研究起步較晚,相關的研究成果也較少。馮躍為更好地探究青少年抗逆力的生成,檢索了國外近30年有關家庭抗逆力的相關文獻,分析了在不同視角下,家庭抗逆力的內涵,并總結了主要的7種研究模式以及未來的變化趨勢[9]。同時,國內一些學者也開始關注到運用家庭抗逆力來創新服務模式。同雪莉根據長期患病家庭的應對模式和適應過程,以提升家庭抗逆力為目的,提出了一系列福利服務建議[10]。劉穎等人以聽障兒童家庭為對象,以家庭抗逆力形成的三個關鍵過程為依據,展現其家庭抗逆力的生成和發展[11]。
然而,專門針對精神障礙患者家庭抗逆力提升的研究剛剛起步,相關理論與實務經驗還比較匱乏。同時,由于精神障礙患者自身的不足,社會上的“污名化”以及相應社會保障的缺乏,精神障礙患者一直處于社會邊緣位置。一些精神障礙患者家庭由于長期陷入物質與精神上的壓力而分崩離析,也有一些家庭因缺乏必要的抗逆力來應對不斷出現的挑戰而導致患者病情反復。基于這一現狀,針對精神障礙患者所提供的服務不能再僅僅局限于醫學和心理學,更應創新性地轉變思路,從社會工作的角度出發,以助人自助為目的,提升患者及其家庭的抗逆力,從而提高家庭面對危機的能力,降低家庭成員面對挑戰的無力感。除此之外,還要充分考慮環境因素對于人類行為的影響,基于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理論構建支持性社會環境,以促進精神障礙患者行為的改變。
三、家庭抗逆力的應用探討
與個人抗逆力關注個人特質不同,家庭抗逆力是將家庭看作一個整體來共同應對挑戰,家庭是家庭抗逆力形成的關鍵要素,但同時外界因素也會對家庭抗逆力的形成造成影響。本文主要借鑒沃什家庭抗逆力形成的三個關鍵過程,來探索如何提升精神障礙患者的家庭抗逆力,同時兼顧外界因素對家庭抗逆力形成的影響,內外結合提升精神障礙患者的家庭抗逆力。
(一)家庭內在力量的提升
1.家庭信念系統的構建
對于精神障礙患者家庭,要特別重視家庭關系的構建,家庭成員之間要放下對彼此的芥蒂,相信彼此,形成合力,共同應對挑戰。在服務過程中,首先要幫助家庭成員認識到構建家庭抗逆力的意義,使他們正確看待困境,不再將困境單純歸為個人原因或他人原因,而是綜合考量多方面因素,將困境作為整個家庭共同面對的挑戰。其次,正面的展望也不可或缺,社會工作者要幫助家庭成員對困境保持樂觀積極的態度,關注家庭自身所具備的優勢和潛力,不斷給予家庭成員鼓勵,使其能夠運用自身能力積極主動地去解決問題,并對自身所具備的能力充滿信心。
2.家庭組織模式的調適
抗逆力通常被認為像是彈簧,在面對壓力的時候會被壓彎,但也能夠憑借自己的彈性反彈壓力,恢復到最初狀態。社會工作者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應該幫助患者家庭保持像彈簧一樣的彈性,在面對困難或者重大危機時能夠通過及時改變家庭的角色、關系、規則和生活方式以應對突發的挑戰。但在改變的同時,也需要保持家庭的穩定性。這種穩定性可以是每天正常的家庭用餐時間、飯后的閑聊,或者是其他某種固定的生活方式,以此幫助一個家庭在混亂中依舊保持一定的秩序,讓家庭成員通過這一不曾改變的生活方式在已經發生變化的家庭中找到原本的歸屬感,在此基礎上再次發展形成新的家庭合力。
在一個家庭中,家庭成員的關系、凝聚力是應對危機的重要力量,只有將大家團結在一起才能更有效地應對挑戰。針對精神障礙患者的家庭而言,患者與家屬之間以及家屬與家屬之間或多或少都會存在一些嫌隙,可能是由于長期照顧導致的抱怨或是生活方式的沖突。為此,社會工作者要幫助家庭成員及時化解沖突,明確整個家庭的共同目標,增強家庭的凝聚力、向心力。除內部支持外,家庭外部人際關系的鏈接也同樣重要,社工可以通過幫助患者及其家屬發展鄰里或者親友關系,增強家庭的外部支持,降低家庭面對風險的壓力。
3.家庭溝通過程的促進
溝通可以用來傳遞信息,表達內心情感,構建人際網絡,等等。良好的溝通對于增強家庭抵御風險的能力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為精神障礙患者提供服務的過程中,社會工作者要幫助患者家庭營造一種和諧、安全的家庭氛圍,讓家庭成員在這樣的氛圍中放下內心的警戒,坦誠地分享自己的情感以及內心最真實的想法,合理地宣泄壓制在心中的不滿和訴求,從而真正實現彼此之間相互理解。在此基礎上,通過良好的溝通讓家庭成員對問題形成清楚且一致的理解,避免因理解的差異而產生分歧。
(二)家庭外部支持力的構建
1.加強社區宣傳
無知往往是恐懼的源頭,當前,大部分社區往往忽視了對精神障礙疾病相關知識的普及與宣傳,導致社區居民對精神障礙缺乏正確認識,對待精神障礙患者往往避之唯恐不及。鑒于這一現實情況,社區應該充分發揮宣傳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在社區內張貼海報普及精神障礙疾病的相關知識,揭開精神疾病的神秘面紗,使社區居民減少對精神障礙患者的恐懼,縮短與精神障礙患者的距離,增強社區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邀請醫院的相關專家來社區作報告,講授精神疾病的發病原因、發病癥狀以及相應的治療措施,增進居民對于精神疾病的了解,更好地關注家庭成員的身心健康,做好精神疾病的預防工作,降低精神類疾病的發病率。
2.構建社會支持網絡
沃什認為,我們要拓寬視角,抗逆力的增強并不是僅僅局限于一對一的兩個人的組合關系,不能指望僅靠一個導師或者專家就能解決問題。只有當家庭與其他各方面的關愛關系聯結成緊密的網絡,才能形成有效的支持。大多數情況下,我國精神障礙患者家庭主要是通過家庭這個非正式網絡的支持來緩解精神障礙患者所面臨的困境和壓力。這種方法雖然最為人性化也最為有效和及時,但效果也是有限的。
有些精神障礙疾病的治療周期長,患者家庭在長期的輸出過程中往往會心有余而力不足。家庭中的照顧者可能長期面臨精神上的高度緊張,體力上的持續支出,以及“污名化”之下的心理壓力。除此之外,精神障礙患者高昂的治療費用也是家庭面臨困境的重要原因。社會工作要聚焦家庭的外部系統,作為資源鏈接者,幫助構建社會支持網絡,以緩解家庭獨自面對困境的壓力。一方面,可以鏈接相關基金會、社會捐贈、企業捐贈,為家庭提供經濟支持,以緩解家庭的經濟壓力;另一方面,可以鏈接醫院的資源,保障精神障礙患者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為家屬提供相關康復技巧的培訓,提升家屬的照顧技巧。為進一步緩解家屬的照顧壓力,鏈接志愿者資源也必不可少,專業志愿者服務可以為照顧者提供支持,減輕照顧者的照顧壓力,使其獲得更多的喘息時間。
3.完善相關政策
相比社區以及社會力量,社會政策的保障對于精神障礙患者而言才是最強有力的支持。為促進相關政策的進一步落實,社會工作者應扮演好政策倡導者角色,充分了解精神障礙患者家庭真實的生活狀況,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未能滿足的需求。將收集到的真實信息反映給政策制定者,并提出相關建議,讓國家能夠及時關注精神障礙患者這一弱勢群體,從而幫助國家層面更好地、有針對性地完善相關醫療救助與醫療保障政策。
除醫療方面的社會政策外,政府層面可以通過挖掘、整合社會資源,從制度層面為精神障礙患者構建正式的社會支持體系。正式的社會支持體系可以包括專業的社會工作機構、心理咨詢中心、醫院等,相對家庭這類的非正式支持而言,這些正式的社會支持將更加有效且穩定。
四、結論
本文主要在分析精神障礙患者家庭當前所面臨的困境與需求的基礎上,從家庭抗逆力的視角出發,借鑒沃什家庭抗逆力形成的三個關鍵過程,綜合考慮家庭內在能力的提升以及外部力量的支持,從社會工作者角度提出了更有效地將家庭抗逆力應用于精神障礙患者服務中的策略,包括家庭系統內部,家庭信念系統的構建,家庭組織模式的調適以及家庭溝通過程的促進;家庭系統外部,社區宣傳的加強,支持網絡的構建以及相關政策的進一步落實。
隨著家庭抗逆力理論在實務工作中的進一步運用,相關實務經驗也在不斷累積,在本土化背景下,家庭抗逆力理論將與中國實際更好地結合,形成適合中國國情的本土化抗逆力理論。與此同時,社會工作者也應不斷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不斷提高社會工作在我國的社會地位,發展本土化的社會工作理論以應對不斷出現的社會問題。社會工作者作為重要的社會力量,其發揮的作用不應僅僅局限于支持與輔助,而應該利用社會工作的專業技巧、專業價值觀、專業方法,發揮在解決問題過程中的重要主體作用。因此,如何提升社會工作介入精神障礙患者家庭服務的不可替代性與專業性依舊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參考文獻
[1]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黃悅勤教授團隊發布“中國精神障礙患病率:流行病學現況研究”成果[J].北京大學學報(醫學版),2019(2):368.
[2]葉倩怡.系統視角下對社區精神康復服務體系的分析與思考:以某精神病患者危機個案為例[J].法制與社會,2018(31):145-146.
[3]胡思遠,楊锃.賦權視角下的精神障礙患者職業康復困境研究:兼論社會工作介入精神障礙患者康復的可能性[J].都市社會工作研究,2019(1):29-59.
[4]張木明,豐行.增權視角下精神康復者的社會融入探索:以廣州M精神康復服務中心為例[J].產業與科技論壇,2017(15):129-130.
[5]蔣美華,李正芳,嚴云鶴,等.優勢視角下精神障礙患者的個案社會工作介入[J].中國社會工作,2020(27):32-36.
[6]楊曉東,吳建杰,白麗娟,等.多學科視角下社會工作介入精神障礙患者的再社會化[J].中國民康醫學,2016(12):51-52,73.
[7]WALSH F.家庭抗逆力[M].朱眉華,譯.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13:17.
[8]WALSH F.Family Resilience:A Framework for Clinical Practice[J].Family Process,2003(1):1-18.
[9]馮躍.國外家庭抗逆力的內涵及模式研究述評[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4):140-145.
[10]同雪莉.長期患病家庭抗逆適應過程研究:基于家庭生活實踐的質性分析[J].社會科學研究,2018(5):108-115.
[11]劉穎,肖非.且行且歌:聽障兒童家庭抗逆力生成過程個案研究[J].中國特殊教育,2018(4):2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