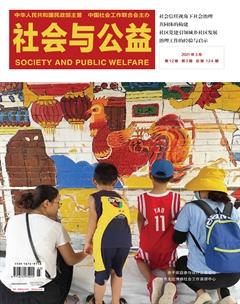從博士教育角度淺談我國社會工作研究的問題與困境
吳世友
近日,某社工微信公眾號發文指出,在知網以“社會工作”為主題詞進行搜索,結果顯示2020年發表在核心期刊的論文共293篇。相比其他社會科學專業,通過同樣的檢索方式查看2020年的發文量,如經濟學(1935篇)、社會學(714篇)及公共管理學(356篇)等,均多于社會工作專業。暫且不討論這個檢索方式的科學準確性,這些數據從某個方面倒是在直觀上引起大部分社會工作學者的共鳴。社會工作領域文章發文難是普遍現象,因此發文少,尤其是高質量的文章少就不足為奇了。
除外部因素如社會工作專門的期刊少尤其核心期刊更少導致發文難外,筆者認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工作研究的質量和文章的質量都還有較大提升空間。真正高質量的文章還是能找到地方發表的。不少好期刊,其實并不完全只發“大佬”的文章,“青椒”甚至研究生的文章要是質量過硬,也能順利發表。而研究和文章的質量上不去,一個重要原因出在教育方面,尤其是目前的社會工作博士培養沒有完全準備好畢業生獨立開展科學嚴謹的研究,特別是實證和干預研究。教育是專業人才培養的基本途徑,而博士生及博士畢業生群體,應該是一個學科研究的主要力量。本文將從社會工作博士教育的角度,來理解當下我國社會工作研究面臨的問題與困境。
一方面,由于中國社會工作教育的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較短,社會工作專業博士生的培養一直處于嚴重缺乏和滯后狀態。社會工作博士點雖從無到少(至今全國也只有20來個社工相關方向的博士點),但每年社會工作博士畢業生相對較少,專業研究人員人才儲備不足。由于社會工作人才短缺,社會工作專業從20世紀80年代末重建之初開始,專業師資就主要依靠其他相關學科(如社會學、心理學、哲學或歷史學等學科)的教師跨學科轉到社工專業,很多教師都沒有接受過社會工作專業訓練,“摸著石頭過河”教社工,帶學生實踐基本沒有問題,但是開展社會工作研究則經常遇到瓶頸。期間,雖然有如香港大學聯合復旦大學,香港理工大學聯合北京大學幫助中國社會工作界培訓了一批早期社會工作碩士人員,這些畢業生再回到各自高校,繼續培養本土的社工學生,但這些碩士教育也主要以提高社工專業實踐能力為主,并未重點開展相應的研究訓練,因此未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工作研究基礎薄弱的問題。同樣,由于社會工作博士點不足,社會工作博士畢業生少,無法滿足高校社會工作師資的需求,就會繼續從其他學科招聘教師來填補。由非社會工作背景的教師來培養社會工作學生的弊端很多,這里不一一贅述,但這是導致社會工作研究不良發展循環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節點。
另一方面,對于我國的學科和專業博士點設置,各大高校沒有完全的自主權。而且,社會工作學科一直劃歸法學學科下屬的社會學一級學科,在大部分高校內是社會學院或者社會學系的一個二級部門(系)專業,甚至是某個學科更遠的院系的一個二級部門。因此,很多教育資源、自主招生及專業設置話語權,在很大程度上還受到其他學科的影響。此外,由于國內的博導需要經過學校的評審,一般是具有高級職稱(如教授),或者是特殊人才待遇(如海歸),才有資格成為博導。同樣,由于歷史和現實原因,目前我國開設的社會工作方向博士點,還存在有部分博導是教授但是沒有博士學位的情況;或博士人才培養計劃以傳統的理論和思辨的研究范式訓練為主,而對博士生研究方法,尤其是實證研究方法的訓練重視不足。這些因素是很多本土社會工作博士畢業生的研究論文質量不高的直接原因。這些博士生畢業以后,由于訓練不足,不僅導致他們的研究文章(如思辨性的論文)在如今越來越重視實證研究的大學術背景下難以發表,而且在成為新教師后也會影響到未來的社會工作研究人才教育,又是導致社會工作專業陷入不良發展循環的因素之一。
由于國情和專業發展歷史的差異,中國的社會工作教育與很多西方國家的情況有較大不同。但國外的某些經驗,可能對改善目前我國社會工作研究發展困局有一定的借鑒和參考意義。以美國為例,首先,社會工作是一個獨立的學科,一般高校都有獨立的社工院系,再好一點的社會工作學院則有一套獨立完整的師資和本碩博人才培養體系。其次,有一個專門的監管和評估機構(即全美社會工作教育協會,英文名為 Council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簡稱CSWE)會對各個開設社工專業本科和碩士的項目進行評估,且每8年要重新評估一次,以確保社會工作學院內部的課程設置基本能滿足本專業的人才培養需求,且達到CSWE對社工學生要求具備的核心專業勝任力(Social Work Core Competencies)的要求。因此,社會工作學生在自己學院里面選課就基本能實現專業學習目標,而不用專門跑外系去選課,除非出于個人興趣。再次,博士點的設置相對比較靈活。社工博士點的設置跟各個院校的專業師資有關,只要自己院系達到博士培養的能力,就可以招收博士生。最后,博導資格不用經過評審。能否成為博導,跟職稱無關,只要具有博士學位,就自動獲得博導資格,不需要誰來評審。但是,能不能成為事實博導,通常取決于該教師是否有課題和研究經費來支持博士生的學習和研究,以及是否有學生申請成為自己的學生。因此,即使是剛畢業的助理教授或者非終身制的教師,也可以帶博士生。由于某些知識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換代,往往剛畢業的博士掌握了最新的方法,那么這種靈活的博士生培養制度和博導資格免評審情況,不僅能讓新招的博士生有機會向老教授學習經典的理論與方法,也有機會接受掌握最新或最前沿的研究方法與動向的年輕教師的指導與訓練,促進了社會工作人才尤其是博士人才的培養,進而為社會工作學科的專業發展和研究源源不斷地輸送合格的人才。
當然,美國的國情和社會工作的發展歷程跟我國不一樣,因此,在比較和借鑒的同時,不能盲目照搬,而應根據我國的具體國情酌情調整,取長補短,從而摸索出一條適合我國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道路。筆者認為,在國家層面,應適當調整學科結構,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爭取盡早把社會工作從社會學分類中獨立出來,成為具有博士自主招生資格的一級學科。在高校層面,改革博導制度,適度放寬博導資格標準,讓更多真正有能力培養博士生的教師加入到博士生培養隊伍中來。此外,開設社會工作博士點的高校應成立社會工作博士教育聯盟/協會,通過聯盟/協會的平臺,制定和完善適用于我國具體國情的社會工作博士人才培養標準和指導意見,進一步提高社會工作博士教育水平。在教師層面,博導資格是終身制,但每年招生應采用靈活制。有能力有“市場”就招學生,沒有能力就暫停招,而不是固定的博導每年招生,導致有些博導沒有精力去指導學生的研究,從而影響下一代博士生培養質量。在學生層面,盡量聚焦于自己的興趣,開展博士研究,這樣做起來才更有動力。做研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興趣很重要。此外,之前提到的國家,高校以及博導方面的改變是不可控的,有些也可能是短期內難以實現的;但是有一點是博士生當下能做的,那就是在讀博士期間盡量多學習和掌握一些研究方法。掌握不同的方法就相當于擁有可以解決不同問題的工具,擁有的工具越多,將來在做研究的過程中遇到問題時才能越有效地解決,從而達到研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