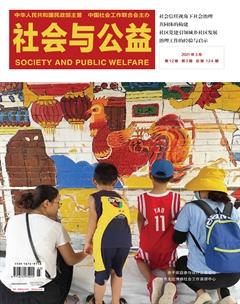貧困脆弱性群體的社會支持網(wǎng)絡建構(gòu)路徑探析
趙影 史秋霞


摘 要:依托民政部“牽手計劃”項目,對國家級貧困縣M村的實地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貧困地區(qū)脆弱性群體的社會支持網(wǎng)絡存在規(guī)模小、水平低、內(nèi)部聯(lián)動性弱等問題,這將加大其脫貧難度與返貧風險。基于社會支持網(wǎng)絡理論的介入思路,可以通過培育本土組織資源、引入跨域社會資源及構(gòu)建“社社聯(lián)動”機制等方式構(gòu)建與激活社會支持網(wǎng)絡的支持功能。
關(guān)鍵詞:社會支持網(wǎng)絡;貧困脆弱性;社會工作
基金項目:2020年江蘇省研究生科研與實踐創(chuàng)新計劃項目資助“社會工作參與精準扶貧的“社社耦合”模式研究——以‘牽手計劃為例”(項目編號:SJCX20 0826)。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qū)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要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1]相對于傳統(tǒng)的粗放式扶貧,精準扶貧思想最早由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考察湖南湘西時提出。2015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guān)于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的決定》指出:“抓好精準識別、建檔立卡這個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為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打好基礎(chǔ),為推進城鄉(xiāng)發(fā)展一體化、逐步實現(xiàn)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創(chuàng)造條件。按照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的要求,使建檔立卡貧困人口中有5000萬人左右通過產(chǎn)業(yè)扶持、轉(zhuǎn)移就業(yè)、易地搬遷、教育支持、醫(yī)療救助等措施實現(xiàn)脫貧,其余完全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實行社保政策兜底脫貧”“扶貧開發(fā)貴在精準,重在精準,必須解決好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的問題,做到扶真貧、真扶貧、真脫貧”[2]。可見,精準扶貧是一個復雜、系統(tǒng)的社會治理過程[3]。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形成多元主體參與的扶貧格局,是新時期推動精準扶貧的必然選擇。在多元參與主體中,社會工作者日益成為重要的推進力量[4]。國際經(jīng)驗已證明社會工作參與貧困治理成效顯著,專業(yè)社會工作對于緩解和消除貧困有著先天的優(yōu)勢與功能[5]。因此,有效運用社會工作的專業(yè)理念和方法推進我國精準扶貧工作的開展,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與價值。
當前,學術(shù)界對于社會工作參與扶貧工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參與的可行性、優(yōu)勢、路徑等方面。具體來看,通過比較社會工作與精準扶貧在價值觀、問題認知和對策、工作方法等方面的相似性和內(nèi)在契合性,可凸顯社會工作參與精準扶貧的可行性[6-7]。或者,從社會工作“以人為本”“助人自助”的專業(yè)理念、需求導向的實踐精神、善于資源整合及促進多元合作等方法,可以看出社會工作參與扶貧的優(yōu)勢所在[2]。參與扶貧的策略及路徑研究多集中于社會工作服務的提供、貧困群體內(nèi)生動力的挖掘及貧困者脫貧能力的提升等方面[8-10]。然而,注重貧困群體自身能力挖掘與培育的介入思路,有可能會忽視貧困地區(qū)群體內(nèi)部的差異性。與那些有就業(yè)能力、愿意改變現(xiàn)狀的群體相比,對于無勞動能力、依賴度高的脆弱性群體采取個體層面的介入路徑可能并不合適。因此,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面對貧困地區(qū)客觀上無法就業(yè)、主觀上不愿改變的脆弱性群體,如何進行扶貧介入?2017年民政部啟動“牽手計劃”項目①,搭建了社會工作東西方協(xié)作機制,將東部社會工作先發(fā)地區(qū)的社工機構(gòu)引入到中西部貧困地區(qū),為社會工作更好地介入貧困脆弱性群體扶貧服務創(chuàng)造了機會。
本文基于社會支持網(wǎng)絡的分析視角,依托民政部“牽手計劃”項目,通過對項目落地貧困縣M村貧困群體的全面分析,說明社會支持網(wǎng)絡與群體的貧困脆弱性間的關(guān)系,并嘗試搭建擴展激活脆弱群體社會支持網(wǎng)絡的可行路徑。
二、社會支持網(wǎng)絡與貧困脆弱性
社會支持的概念首先出現(xiàn)在病原學中,柯布斯(Cobbs)認為社會支持是指社會網(wǎng)絡中傳遞的能夠讓人感受到溫暖、體會到尊重的信息[11]。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將社會網(wǎng)絡定義為“聯(lián)結(jié)行動者的一系列的社會聯(lián)系和社會關(guān)系”[12]。20世紀80年代,社會支持網(wǎng)絡所蘊含的介入邏輯逐漸開始在社會工作領(lǐng)域得到應用[13]。社會支持網(wǎng)絡通常是指個人能借以獲得各種資源支持(如金錢、情感、友誼等)的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絡,通過社會支持網(wǎng)絡的幫助,人們能夠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和危機,并維持生活的正常運行[12]。絕大多數(shù)學者將社會支持網(wǎng)絡分為正式與非正式兩部分。正式社會支持網(wǎng)絡主要指來自政府、正式組織的各種制度性支持,包括提供政策、信息、資金、教育、服務等方面;非正式社會支持網(wǎng)絡主要來源于家庭、親友、鄰里及其他非正式組織的支持,更多提供的是情感和認知方面的支持[14]。
世界銀行在2000年將“貧困脆弱性”概念納入貧困研究領(lǐng)域,并將其定義為個人或家庭由于受到各種外部風險和沖擊,導致在未來陷入貧困或者更加貧困的概率[15]。其中,外在風險、家庭應對能力、應對行動及脆弱性后果一并構(gòu)成貧困脆弱性的形成機理。因此,人們受外界環(huán)境不利沖擊后,是否有可能陷入貧困常與家庭自身應對風險的能力、外界協(xié)助應對風險的能力及補救及時性有著重要關(guān)聯(lián)。對于貧困人口來說,受資產(chǎn)與資源限制,其自身應對風險的能力較弱[16],在同樣風險的沖擊下,那些抵御能力弱的家庭或個人陷入貧困的可能性要高,即其貧困脆弱性要大[17]。
我國精準扶貧的本質(zhì)要求在于脫貧后的穩(wěn)定性,其前提在于貧困群體的應對風險與沖擊能力得到提升并跳出“脆弱性—貧困—脆弱性加深”這一貧困陷阱[18]。貧困脆弱性對個體和家庭陷入貧困具有一定預警作用,對貧困脆弱性群體進行社會工作介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jié)撛谪毨丝谥仑毤耙衙撠毴后w返貧。社會支持網(wǎng)絡有助于個人和家庭增強應對風險能力,減輕貧困脆弱性[19]。社會支持網(wǎng)絡視角下的貧困脆弱性可從三個層面理解:介入依據(jù)上,個人與家庭陷入貧困的原因往往是多重疊加,對于脆弱性較高的群體來說,外界的支持可以有效降低風險的沖擊力,社會支持網(wǎng)絡的重構(gòu)與完善可以協(xié)助貧困人口抵御風險,提高抗風險能力;介入路徑上,環(huán)境的外部介入與社會網(wǎng)絡密切相關(guān),需要政府、市場、社會組織、社區(qū)等服務主體的綜合支持,以實現(xiàn)其社會支持網(wǎng)絡規(guī)模的擴大及功能恢復[19];返貧可能性上,重構(gòu)的社會支持網(wǎng)絡能有效化解日常生活中的問題和危機,有效阻斷貧困的擴大化發(fā)展與代際傳遞。
筆者通過實地調(diào)查研究,選取了M村的3戶貧困家庭開展非結(jié)構(gòu)式入戶訪談,了解這些家庭的生活現(xiàn)狀、家庭成員、獲得的扶貧支持、家庭已有的社會支持網(wǎng)絡以及對獲得支持的看法與感受等。此外,筆者還訪談了包括駐村書記、村委、社工、留守兒童學校校長、當?shù)胤鲐氜k等8位相關(guān)人員,并查看了當?shù)刎毨艚n檔案與已有扶貧項目記錄,在此基礎(chǔ)上結(jié)合文獻研究和參與式觀察,探討改善貧困地區(qū)脆弱性群體社會支持網(wǎng)絡功能發(fā)揮、結(jié)構(gòu)搭建等方面的社會工作干預的可行路徑與方法,以期發(fā)揮社會工作參與精準扶貧的最大功效。
三、M村脆弱性群體的社會支持網(wǎng)絡現(xiàn)狀
精準扶貧中“脫貧返貧”成為新的貧困治理難題,一些貧困脆弱性較高的群體出現(xiàn)“臨時脫貧”或“救助式脫貧”的現(xiàn)象,即一旦離開各種救助就會再次陷入貧困。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M村的貧困群體大部分屬于此類。M村隸屬于國家級貧困縣S縣,該村共有5930人,其中適齡勞動力3000人,常年在外務工1500人,16歲以上留守兒童60人,60歲以上老人1020人,留守婦女200人。M村脆弱性群體的基本構(gòu)成,如表1所示。
調(diào)研數(shù)據(jù)顯示,M村尚有137戶未實現(xiàn)脫貧,其中因病致貧88戶、因災致貧1戶、因?qū)W致貧7戶、因殘致貧11戶、技術(shù)缺乏致貧13戶、勞力缺乏致貧17戶。隨著精準扶貧理念的推進,M村先后獲得多種扶貧項目的支持,如通過種植農(nóng)作物或畜牧業(yè),拓展家庭收入渠道的農(nóng)業(yè)扶貧項目;通過培訓殘疾人居家代工技能,如手工布藝制作、商品標簽粘貼等,增加家庭收入的勞動技能培訓扶貧項目;通過鋪設家庭太陽能電池板,實現(xiàn)“自發(fā)自用”,改善生活狀態(tài)的光伏產(chǎn)業(yè)扶貧項目等。通過以上扶貧項目,M村大部分的貧困戶逐步實現(xiàn)了脫貧,僅有小部分“脆弱性較高的家庭”未能實現(xiàn)脫貧。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這些剩余貧困戶具有“點狀貧困”和“多因致貧”的特點。在地理分布上,貧困戶散落在村里的各個點,呈現(xiàn)出“點狀分布”的特點。如筆者實地走訪的3個貧困戶居住點距離鎮(zhèn)扶貧辦約20多千米。在致貧原因上,大部分貧困戶致貧原因復雜,呈現(xiàn)出“多重疊加”的特點。如缺乏勞動能力的低齡老人需要照顧高齡老人、輕度殘疾人需要照顧高度殘疾人等。
調(diào)研顯示,這些剩余未脫貧的貧困群體的社會支持網(wǎng)絡呈現(xiàn)出非正式網(wǎng)絡規(guī)模小、構(gòu)成單一,正式支持網(wǎng)絡功能受限,扶貧措施的系統(tǒng)性、可持續(xù)性欠佳等問題,具體表現(xiàn)如下:
(一)非正式社會支持網(wǎng)絡規(guī)模小、構(gòu)成單一
與單一因素導致的貧困不同,M村剩余貧困群體大多為多因致貧,如“貧困+老人”“貧困+殘疾”“貧困+孤兒”等。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這類群體的原生社會支持網(wǎng)絡大多規(guī)模較小,網(wǎng)絡呈現(xiàn)單一性。調(diào)研顯示,95%以上的貧困戶僅有1類及以下的非正式支持網(wǎng)絡,且以血緣親屬為主。如在調(diào)研過程中,有服務對象談到:“我都這把年紀了,家里也沒有別的人了,打工也沒人要,過一天算一天吧。”再者,因為多重疊加致貧的特點,貧困戶擁有的原生社會支持網(wǎng)絡的水平較低、支持效果不明顯,可持續(xù)性較低。如當?shù)刎毨Ч聝旱泥従臃从常骸昂⒆樱ü聝海┑陌謰尪疾辉诹耍瑺敔斍岸螘r間生病動手術(shù)住院了,奶奶去照顧爺爺了;我們鄰居也只能每天給孩子送送飯,別的也不知道能干啥;孩子還有一個姑姑在鄭州,去年把孩子接走住過一段時間,后來因為自己家庭問題,又給送回來了。”
疾病、獨居、勞動力不足等問題成為當?shù)卮迕裰仑毜闹匾颉<彝ト肆Y本和社會網(wǎng)絡相對薄弱、勞動力稀缺、創(chuàng)造財富較困難等加劇了貧困脆弱性。貧困疊加降低了個人和家庭面對風險的復原力,家庭自身應對風險的能力較弱,使得M村貧困戶長期處在脆弱性狀態(tài)中,并逐步轉(zhuǎn)化為慢性貧困脆弱狀態(tài),這導致單一的物質(zhì)支持或短期的扶貧服務難以保障脫貧成果的長效性。
(二)正式社會支持網(wǎng)絡的實際功能受限
與集中連片貧困區(qū)不同,當?shù)刎毨丝诜植汲庶c狀形態(tài),即貧困人口散落在各個自然村落。村與村之間相隔較遠且交通不便,一個貧困戶到另一貧困戶之間相距較遠,步行一般要半個小時左右。這種點狀分布的特點稀釋了正式社會支持的力量,降低了正式支持系統(tǒng)幫扶投入的精準性。走訪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無論是物質(zhì)支持還是軟性支持,M村貧困戶對正式支持網(wǎng)絡提供的幫扶使用率較低、效果差。如很多貧困戶雖然每年收到政府發(fā)放的冬衣,但卻因“不合身”或“不習慣”等原因而閑置不用。雖然政府出資修繕貧困戶居住的房屋,卻無法改變其生活習慣。M村駐村書記反映:“我們剛給他收拾好了,才兩個星期,他自己又給弄成這樣。”
此外,那些居住較為偏遠的貧困戶因為交通不便,也很難參與政府投入的各種“軟性”扶貧項目中。如社區(qū)開展的就業(yè)培訓、產(chǎn)業(yè)扶貧等活動,很多貧困戶因為路程較遠、交通不便而往往選擇放棄。政府撥付的扶貧補貼金也因取款點距離太遠,很多高齡獨居老人或殘疾人對補助資金的實際使用率較低。一位貧困獨居老人說:“政府特別好,給我們發(fā)錢,發(fā)物資,還通知一些免費的活動。但是我行動不方便,也不知道去哪里取錢,在家湊合過也挺好的。”另外,有些實際貧困的群體或脫貧后再返貧的群體,很難被政府識別到,傳統(tǒng)的行政脫貧在這種情況下很難發(fā)揮作用。
(三)現(xiàn)有扶貧措施的系統(tǒng)性、可持續(xù)性欠佳
扶貧開發(fā)是一個上下聯(lián)動的系統(tǒng)工程,自上而下的精準扶貧,是以物質(zhì)扶貧為主的幫扶政策,這種取向的扶貧最突出的特點是可量化[20],但返貧概率也高。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M村所獲得扶貧資源與支持很多,但呈現(xiàn)出形式單一、扶貧群體重復、扶貧效果難以持續(xù)等特點。M村大部分貧困群體以正式支持、物質(zhì)支持為主,而能夠獲得支持物資的群體以特殊或特別貧困的家庭為主,如孤寡高齡老人、殘疾人等。這些支持內(nèi)容常常在單次支持結(jié)束后便沒有了后續(xù)的服務跟進,待物質(zhì)消耗完之后,貧困群體很容易再次陷入貧困狀態(tài)。此外,各種資源彼此之間缺乏互動,未建立互動性的社會支持網(wǎng)絡,使得資源投入量大,資源使用效率不高,資源投入效果不好。貧困個體及家庭在面對貧困問題和外在風險時,獲得的支持單一且支持內(nèi)容持續(xù)性差,因而貧困家庭難以持續(xù)應對貧困問題,最終難以全面脫貧。
四、互構(gòu)式協(xié)作支持網(wǎng)絡的構(gòu)建
(一)培育本土志愿者與社區(qū)社會組織,彌補正式支持網(wǎng)絡的功能受限
社會工作者可通過挖掘M村鄰里志愿者團隊,提升其扶貧能力,并運用社區(qū)社會工作方法培育本土社區(qū)社會組織,擴大貧困群體的社會支持網(wǎng)絡規(guī)模。鄰里志愿者作為非正式支持網(wǎng)絡的補充,可以給予貧困者及時的幫扶,同時可以作為貧困預警網(wǎng)格中的重要一員,隨時關(guān)注貧困者的狀態(tài),彌補行政扶貧中識別不精準、服務不及時和不持續(xù)的困境。社區(qū)社會組織作為正式支持網(wǎng)絡,可以通過專業(yè)的方法和服務,為貧困者提供專業(yè)的服務,解決貧困者深層次的問題。如許多貧困家庭出現(xiàn)貧困代際傳遞的現(xiàn)象,社會組織可通過開展發(fā)展性教育、認知性教育等方式改善貧困代際傳遞問題。互構(gòu)式協(xié)作支持網(wǎng)絡的構(gòu)建,如圖1所示
(二)引入?yún)^(qū)域社會資源,提升非正式社會支持網(wǎng)絡規(guī)模與水平
通過發(fā)揮社會工作者資源鏈接作用,整合各類優(yōu)質(zhì)資源,解決M村貧困群體原生社會支持網(wǎng)絡水平低、種類單一、支持效果不明顯的問題。如通過鏈接M村所在縣級與市級社會資源,如醫(yī)務資源、救助資源等提升脆弱性群體社會支持網(wǎng)絡的規(guī)模與支持水平,使得脆弱性群體在面對外在風險時能夠從網(wǎng)絡中獲得有效的支持。除了將本土資源盤活外,還通過鏈接跨域資源,將先進地區(qū)的優(yōu)質(zhì)資源與經(jīng)驗引入M村,提升M村貧困群體社會支持網(wǎng)絡整體水平。如鏈接來自江蘇、上海等地區(qū)的政府、公益、志愿者及高校資源,為M村貧困群體提供更加專業(yè)、豐富的扶貧服務。
(三)構(gòu)建跨域“社社聯(lián)動”機制,實現(xiàn)網(wǎng)絡間的協(xié)作互動
正式網(wǎng)絡與非正式網(wǎng)絡,以及正式網(wǎng)絡與正式網(wǎng)絡之間協(xié)作聯(lián)動,能夠為貧困群體提供更好的扶貧服務。但當前M村各網(wǎng)絡之間的聯(lián)動較少,通過發(fā)揮社會工作協(xié)調(diào)者角色,構(gòu)建跨域“社社聯(lián)動”②機制,促進社會支持網(wǎng)絡的協(xié)作聯(lián)動性。即通過東部社會工作先發(fā)地區(qū)的社工機構(gòu)牽手M村本土社區(qū)社會組織,一方面東部社工機構(gòu)培育本土社會組織的發(fā)展,以推動與督促本土組織參與扶貧工作;另一方面,借助東部及社工機構(gòu)優(yōu)勢資源和平臺,保障跨域資源輸入的持續(xù)性。通過跨域“社社聯(lián)動”,實現(xiàn)社會支持網(wǎng)絡協(xié)作互動發(fā)展。
最終,在構(gòu)建本地資源網(wǎng)絡與外部資源網(wǎng)絡的基礎(chǔ)上,打造內(nèi)外協(xié)作網(wǎng)絡,并有效利用項目中所培育的本土力量,持續(xù)、有針對性地開展扶貧工作,降低返貧概率,保障扶貧成果。
注釋
①“牽手計劃”項目是民政部鼓勵社會工作先發(fā)地區(qū)牽手后發(fā)地區(qū)參與精準扶貧的社會工作項目。
②本文“社社聯(lián)動”是指社會組織與社會組織,即援助地區(qū)社會組織與授援地區(qū)社會組織聯(lián)動。
參考文獻
[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N].人民日報,2017-10-18(02).
[2]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guān)于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的決定[N].人民日報,2015-12-08(01).
[3]王春光.反貧困與社會治理專題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5(3):4.
[4]袁君剛.社會工作參與農(nóng)村精準扶貧的比較優(yōu)勢探索[J].西北農(nóng)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17-22.
[5]CUMMINS I. Book Review: Dave Backwith Social Work,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J].Critical Social Policy,2015(4):556-558.
[6]王思斌.精準扶貧的社會工作參與:兼論實踐型精準扶貧[J].社會工作,2016(3):3-9,123.
[7]高飛,向德平.專業(yè)社會工作參與精準扶貧的可能性與可及性[J].社會工作,2016(3):17-24,124.
[8]向德平,姚霞.社會工作介入我國反貧困實踐的空間與途徑[J].教學與研究,2009(6):22-26.
[9]顧東輝.精準扶貧內(nèi)涵與實務:社會工作視角的初步解讀[J].社會工作,2016(5):3-14,125.
[10]程萍.社會工作介入農(nóng)村精準扶貧:阿馬蒂亞·森的賦權(quán)增能視角[J].社會工作,2016(5):15-23,125.
[11]Cobb S. Social support as a moderator of life stress[J].Psychosomatic medicine,1976(5):300-314.
[12]賀寨平.國外社會支持網(wǎng)研究綜述[J].國外社會科學,2001(1):76-82.
[13]TRACY E M,BROWN S. Social Work Treatment: Interlocking Theoretical Approaches [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447-594.
[14]張友琴.社會支持與社會支持網(wǎng):弱勢群體社會支持的工作模式初探[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3):94-100,107.
[15]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Attacking Poverty[J].World Bank Publications,2001(6):1145-1161.
[16]Alwang J,Siegel P B,Jorgensen S L. Vulnerability: A View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EB/OL].(2001-06-30)[2019-10-16].https:// ideas.repec.org/p/wbk/hdnspu/23304.html.
[17]祝建華.城市居民家庭貧困脆弱性的測度、因素識別與消減策略[J].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3):129-138.
[18]何思妤,黃婉婷.庫區(qū)移民貧困脆弱性與精準脫貧方略重構(gòu):基于長江上游386戶庫區(qū)農(nóng)村移民的分析[J].農(nóng)村經(jīng)濟,2018(12):49-55.
[19]胡潔怡,岳經(jīng)綸.農(nóng)村貧困脆弱性及其社會支持網(wǎng)絡研究[J].行政論壇,2016(3):19-23.
[20]金昱彤.社會工作參與精準扶貧:從救助個案到改變系統(tǒng)[J].甘肅社會科學,2017(6):165-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