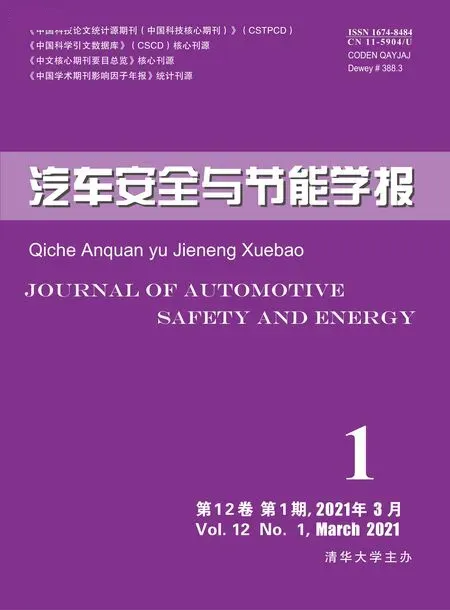系統綜合效率優化的插電式混合動力車輛的能量管理策略
童盛穩,陳 韜,謝 輝
(內燃機燃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天津大學,天津 30007,中國)
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plug-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PHEV)可通過外部電網和發動機做功2種方式獲取電能[1],實現較長的純電里程;采用混合動力的方式工作,降低了燃油消耗,避免了里程焦慮[2]。因此,在插電式混合動力系統工作過程中,必然存在能量之間的轉換和能量源自身效率變化導致的能量損失。與純電動汽車和傳統混合動力汽車不同,在運行中,PHEV車輛電池中儲存的能量來源是變化的,電池儲電的等效效率會隨著時間改變,并造成實際運行中系統綜合效率的動態變化[3]。
插電式混合動力車輛處于發動機充電模式時,電池儲電的等效效率受該時刻發動機工作效率影響,因此導致整個系統的綜合效率具有動態性和耦合性的特點。PHEV綜合能效的變化最終會影響能量管理策略的運行效果。能量管理策略是混合動力系統能量管理的基礎和核心。混合動力的能量管理策略能效評價方法主要有以下3類:
第1類,以等效系統油耗作為綜合能效評價指標。等效油耗最低策略(equivalent consumption minimization strategies,ECMS)是應用最為廣泛的能量管理策略。該方法通過等效因子將電能消耗轉換成等效油耗,并將實際燃油消耗和等效油耗之和作為能效評價指標[4-5];但等效因子沒有確切的物理意義,因此,用等效因子的方法來實現電能的轉化,在PHEV中用無法解決能效的耦合性及動態性的問題。
第2類,以等效功率作為綜合能效評價指標。Jinglai WU[6]以最小化系統等效功率為優化能效指標,進行混合動力系統能效優化,考慮了實際轉化過程的效率對電能進行轉換,有效提升了系統能效。但該方法未考慮電池儲電效率的變動,無法很好應對系統綜合能效的耦合性問題。
第3類,以系統綜合效率作為評價指標。許多研究[7-9]表明:以系統效率作為能效評價指標,對插電式混合動力系統能效提升,有顯著效果;現有的研究還未見系統的針對能效的耦合性及動態性進行效率的修正。Xin YE[7]針對并聯式HEV,采用效率模型,結合模糊控制的方法,驗證了HEV在最佳系統效率下能量分配的有效性,提高了燃油經濟性。Wei WANG[8]等人針對功率分流式HEV建立系統效率模型,并以系統效率為優化目標,提高了系統能效,但未能考慮電池效率的時變特性。連靜[9]等人針對并聯式混合動力系統,構建了不同運行模式下的系統效率評估方程,并基于最高系統效率進行扭矩分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整車油耗;但并未考慮電池電量來源效率不同引起的效率動態變化。Goekce K[10]等人針對串聯式混合動力系統,建立了系統效率成本函數,結合發動機及電機效率等高圖,構建瞬時優化算法進行扭矩尋優,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系統能效。林歆悠[11]等基于并聯PHEV,建立系統效率模型;并采用遺傳算法,進行電量保持模式下的能量分配迭代尋優,使整車性能有所提升,但未考慮PHEV電池中充電能量的轉化來源引起的效率變化。以上研究雖然采用了多種手段對PHEV系統的能效進行了優化;但是沒有很好地解決PHEV系統存在的時變和耦合問題;因而解決該問題面臨的主要困難為如何準確估計系統效率。
針對PHEV系統能效的耦合性和時變性,需要對電池儲電效率的動態變化進行評估,并根據其變化對系統綜合效率進行優化,實現最大程度地真實節能;因而,為了使系統在運行過程中實現能效的動態最優,有必要通過相應的優化算法進行運行模式的選擇及動力的優化分配。
本文通過建立發動機、電機、電池效率等關鍵耗能裝置模型。在此基礎上,根據功率分流式PHEV不同運行模式下的特點,分別建立不同運行模式下的綜合系統效率評價模型;采用基于預設規則和動態優化相結合的復合能量管理策略,以系統綜合效率動態最優為目標,在不同模式下對PHEV系統能量的優化分配,以期提高插電式混合動力車輛道路運行能效。
1 研究平臺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國內某自主品牌的插電式混合動力車輛。該車輛的動力構型為功率分流式插電式混合動力系統,電機1、2為交流永磁電機,其他基本參數如表1所示。
基于GT-SUITE平臺搭建功率分流式混合動力整車及動力系統模型,包括:電機模型、行星輪傳動模型、電池模型、車輛模型。動力構型如圖1所示。整車模型如圖2所示,其中未注符號為軟件模塊名稱。

表1 HEV基本參數

圖1 PHEV動力構型圖

圖2 混合動力系統對象模型
1.1 發動機和電機模型的建立
為了為簡化計算和縮短計算時間同時有效保證模型精度,假設發動機處于良好的預熱狀態,建立基于真實實驗數據和機理結合的穩態發動機及電機模型。
根據發動機轉速(neng)及輸出扭矩(Teng),通過查表可得發動機模型實際油耗為

若令Qf為燃油總熱量消耗,則發動機效率為

同理,電機模型也選用了基于效率等高圖的建模方式。查表可得電機1 (e1)及電機2 (e2)效率為:

發動機、電機1、電機2效率等高圖如圖3所示。

圖3 發動機、電機的效率等高圖
1.2 傳動系統及車輛模型
本動力系統為單行星排平行軸構型,行星輪系統由齒圈(ring)、太陽輪(s)、行星齒輪(r)組成。
行星輪系統各部分的轉速(n)滿足:

電機2通過中間齒輪與齒圈耦合, 3個動力源之間的轉速關系為

式中:ρ為行星輪齒數比;Ns為太陽輪齒數;Nr為齒圈齒數;i1為齒圈減速比。
行星輪系的扭矩傳遞關系:

式中:角標eng、e1、e2分別表示發動機、電機1、電機2;角標c、s、r分別表示行星齒輪、太陽輪、齒圈;角標wheel、brake分別表示驅動、制動;R為輪胎滾動半徑;c0、c1、c2為道路阻力因數;m為整車質量;v為車速;g為重力加速度;λ為道路坡度。
1.3 電池模型的建立
將電池看作一個理想電壓源和一個內阻串聯的等效電路,令t0表示初始時刻,則t時刻的充電狀態(state of charge, SOC)為

其中:I表示瞬時電流,C為電池容量。
電池的充電效率、放電效率為:,

式中:Ebat為電池電動勢,R為電池內阻,Pbat為電池輸入或輸出功率。
2 插電式混合動力系統綜合效率評價函數
建模中,基于電池中能量的組成對電池儲電效率進行修正。并考慮生產運輸過程能量損耗代價,對系統不同運行模式下的能效進行優化。
2.1 電池-電機子系統效率評價模型
通過電網向電池充電時,電網電能轉換損失的能量較小;但是當通過發動機向電池中充電時,由于發動機工作效率(η)較低,實際轉換過程中所產生的能量損失會相對較大。電機總消耗能量為:

考慮到能量生產運輸的損失,需要對燃油和電能在生產運輸中的效率進行考量,假設煉油和運輸汽油的效率ηgas為86%[3],電能的損失取決于所采用發電技術,由文獻[10]可知2019年中國發電量構成情況,考慮到這些發電技術在實際應用中的占比,可以通過以下公式獲得平均效率:

式中:ηge為電能平均生產運輸效率,ai為每種發電技術的占比,ηi為每種發電技術的發電效率[12]。
隨著實際和充電能量變化的電池修正效率為

式中:Preq為需求功率,Peng為發動機輸出功率,為通過制動能量回收的能量。分子表示t時刻的電池能量,分母為在t時刻電池所消耗或者補充的總能量,E0為初始電池能量,E1為通過發動機補充電量所消耗的能量。
2.2 不同工作模式下的系統效率評價模型
以驅動方式劃分,本系統包括:單電機驅動、雙電機驅動、混合驅動、制動能量回收等4種運行模式[13]。在不同的運行模式下,系統效率的評價模型不同。
1) 單電機驅動模式。電動機單獨驅動車輛行駛,發電機空轉。系統所消耗的總能量Ecost及系統綜合效率ηtot為:

式中:Ereq為驅動車輛所需的能量。
2) 雙電機驅動模式。當需求扭矩超出驅動電機額定扭矩且電池電量充足時,混合動力系統以雙電機模式驅動,發電機輸出扭矩,驅動車輛。該模式下,2個電機特性不同,效率也不同,有必要建立相應模式下的系統效率模型,優化能量分配,實現系統效率最優。消耗的能量及系統綜合效率為:

此時2個電機均作為電動機向外輸出功率。
3) 混合驅動模式。2個電機既可以作為發電機也可以作為電動機,發動機不僅工作驅動車輛,也可以通過多余的能量向電池充電。系統消耗的能量及綜合系統效率為:

在給定車速、SOC、需求功率的情況下,尋找最優的發動機和2個電機的功率分配關系,使得系統效率最高。
4) 制動能量回收模式。當車輛需要減速制動且電池SOC低于上限值時,可以通過電動機制動回收多余的能量,從而實現車輛的減速。電機制動也存在能量轉換的損失。該模式下系統需求功率為負,電動機發電向電池充電。系統獲得的能量及綜合效率為:

3 復合式能量管理策略的構建
3.1 復合式能量管理策略架構
針對插電式混合動力系統能效的耦合性和時變性,本研究提出基于預設規則和動態優化相結合的復合式能管理策略,通過預設規則快速確定車輛運行模式,根據動態優化算法以系統綜合效率評價函數最優為目標對能量協調分配進行優化,并將系統效率作為混合動力系統模式切換的依據。實現系統的動態能效優化。集成后的能量管理控制策略結構如圖4所示。

圖4 PSOSCALF算法與規則集成的策略框圖
圖4中系統效率模型用于計算當前車輛狀態下各個動力源的實時效率,并通過計算發動機累積充電量對電池效率動態變化進行修正。圖4中S表示車輛狀態信息。集成后的能量管理策略在原有規則的策略基礎上,對不同運行模式,分別以不同的系統效率評價函數為最優目標進行能量分配尋優,并在每一次優化過程中對電機驅動和混合驅動下系統的綜合效率進行比較。當目標需求功率下當前模式功率分配效率較低時,控制策略會發出模式切換命令指導規則進行模式的切換,使混合動力系統始終處于最優驅動模式下。
3.2 復合能量管理策略的規則構建
能量管理策略是決定整車運行的能耗經濟性和動力性的關鍵環節,基本思想是根據各個動力部件的工作特性,對動力傳動系統控制,實現發動機和電機之間合理的能量分配[14]。
基于分層架構構建的能量管理策略規則,將所有運行和控制模式分為駕駛模式層和能量管理層。根據車輛實際工作狀態,運行模式分別有:停機模式、停車充電模式、單電機驅動模式、雙電機驅動模式、混動模式1(電機為主能量源)、混動模式2(發動機主能量源)、混動模式3(電機和發動機共同驅動)、制動能量回收模式、機械制動模式。
3.3 復合式能量管理策略的優化算法構建
為了實現系統效率的優化,需要在預設規則的基礎上,對不同運行方式下系統可能存在的狀態進行對比尋優,因此,需要一種高效準確的尋優算法。
粒子群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是一種基于社會搜索和群體智能的算法,其特點是速度快,參數數量少易于實現。然而,粒子群算法易陷入局部最優,全局搜索能力弱的缺點。本文以PSO算法為基礎,加入正余弦算法(sine cosine algorithm,SCA)中的位置更新方程式和Levy Flight算法,提高算法的性能。在SCA算法中,解決方案更新的數學公式是基于正弦和余弦函數方程,保證了算法的開發和利用能力[15]。Levy Flight是一種隨機分布,可以在空間中進行更有效的搜索[16],可以在尋優過程中避免陷入局部最優。本文采用的優化算法為“基于正余弦算法和飛行算法改進的粒子群優化算法(PSO based on sine cosine algorithm and levy flight, PSOSCALF)”。
結合SCA算法和Levy Flight分布后的PSOSCALF算法的粒子速度和位置更新方程為:

式中:Vi(t+1)和Xi(t+1)分別是粒子i在迭代t+1處的速度和位置矢量;c1和c2分別是個體學習因子和社會學習因子;w為慣性因子;levywalk[Xi(t)]為加入Levy Flight的粒子位置矢量;r1、r2、r3、r4為隨機數;XgBest是迭代t次后的全局最優點;r4為正余弦之間的切換因子;r1指定解決方案的下一個位置方向;r2定義了朝向或背離終點的距離遠近;r3為終點引入隨機權重。為了平衡探索和利用,正余弦的取值范圍應該自適應調整,r1隨著優化迭代逐漸減小。
PSOSCALF優化的流程如圖5所示。

圖5 PSOSCALF優化流程圖
在不同的運行模式下,算法的優化變量不同。如在系統處于雙電機驅動模式時,選取的優化變量為驅動電機的功率,優化模型可以表示在約束條件下確定需求功率、確定車速及修正電池效率下的效率尋優問題:

當混合動力系統處于混合驅動模式下時:選取的優化變量為發動機功率,為了保證最大化提高發動機效率,將發動機的操作工況固定在最高效率線上,通過調節電機1扭矩穩定發動機目標轉速。此時優化模型及約束條件可以表示為:

4 優化結果及仿真分析
本研究通過Simulink-GT聯合仿真平臺上對控制策略進行了效果驗證。其中邊界條件來源于2個連用的全球統一輕型汽車測試循環(worldwide harmonized light vehicles test cycle, WLTC),其輸出實際車速與參考車速如圖6所示。仿真車速與參考車速基本吻合,說明整車控制策略能滿足車輛運行過程中的動力需求。

圖6 實際速度與參考速度
在連用的WLTC工況下,針對功率分流式混合動力系統,分別對基于規則及基于預設規則和動態優化相結合的能量管理策略,進行仿真對比分析。發動機工況分布密度對比及工況點在萬有特性中的分布如圖7所示,其中白色圓圈為發動機工作點。
從圖7中可以看出,基于系統綜合效率優化的策略仿真結果中發動機工況點更多的集中于發動機高效率區。同時,通過計算均方根誤差(RSME)對發動機工況分布集中度進行評價。RSME反映了數據偏離目標值的程度。通過計算,在基于規則策略的控制下,發動機工況分布的RSME值為19.2;而基于動態優化策略的控制,RSME值為14.8。可見在基于動態優化策略下的工況點相對于基于規則的策略更加集中分布在最優工作線附近。
圖8給出了仿真運行的電機1和電機2的工況分布對比。通過計算最終的平均效率得到電機1的平均效率優化前為0.64,優化后為0.647,電機2的平均效率優化前為0.759,優化后為0.764。

圖7 發動機工況點分布

圖8 電機1及電機2工況點分布對比
插電式混合動力系統的綜合能耗對比如圖9所示。其中:E為系統能耗,黑色實線為考慮生產運輸效率后系統基于規則控制下的循環能耗;紅色點線為基于預設規則和動態優化相結合的復合能量管理策略優化后的系統循環能耗。相對于優化前的結果,系統能耗降低了10.6%。
為驗證此能量管理策略的適應性及插電式混合動力系統效率的動態性和時變性。分別對兩個連用的全球統一輕型汽車測試循環(New European Drive Cycle,WLTC)和2個連用的新歐洲駕駛循環(NEDC),分別在初始電量為60%和80%的初始條件下進行仿真對比,能耗仿真結果如表2所示。
不同初始條件及工況下優化前后的能耗對比曲線如圖10所示,其中:E60為初始電量60%時的能耗,E80為初始電量80。
由仿真結果可知:在初始電量為60%時,在2個WLTC循環及2個NEDC循環下,優化后能耗分別降低了10.6%和12.5%。在初始電量條件為80%時,在2個WLTC循環及2個NEDC循環下,優化后能耗分別降低了7.8%和9.8%。在電量較高的情況下,同樣的循環系統能耗會相對較少,這是由于系統會優先消耗效率較高的電能。可見基于綜合效率最優的優化方法在不同的工況及初始條件下均可有效提升系統綜合能效。

圖9 優化前后系統綜合能耗對比

表2 不同初始條件及循環下能耗對比

圖10 不同初始電量條件及循環下能耗對比
5 結 論
本文針對插電式混合動力系統綜合效率存在時變性和耦合性所造成的能量優化管理難題。基于Simulink-GT-Suite聯合仿真平臺,開展功率分流插電式混合動力車輛(PHEV)綜合能效管理優化研究,通過建立電池能效評價模型及提出不同模式下的系統效率評價函數,并以系統效率最優為目標設計了復合能量管理策略。通過仿真得到主要結論如下:
當車輛在經過連續2個“全球統一輕型汽車測試循環(WLTC)”仿真后,采用基于預設規則及動態優化相結合的復合能量管理策略,使發動機及電機在實際運行中的工作點更加集中在高效率區;相對于未考慮系統綜合效率的策略,系統總能耗降低了10.6%。在不同初始電量條件下,該能量管理策略在WLTC及NEDC循環下均可有效降低系統能耗。相對于基于規則的策略,優化后的電機工作點總體效率也得到提升,工況點分布更為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