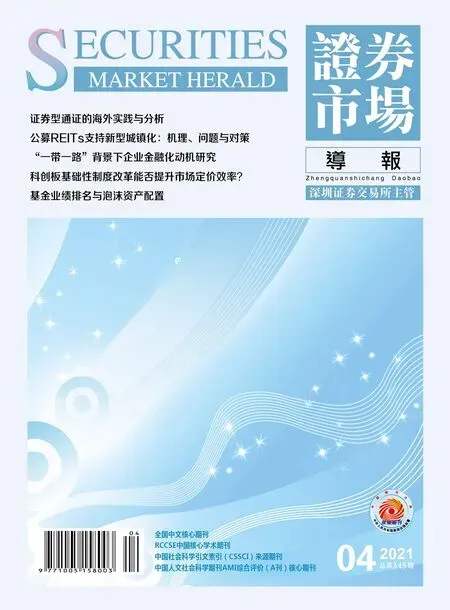科創(chuàng)板基礎(chǔ)性制度改革能否提升市場定價效率?
張宗新吳釗穎
(1.復(fù)旦大學(xué)金融研究院,上海 200433;2.復(fù)旦大學(xué)經(jīng)濟學(xué)院,上海 200433)
一、引言
正如上海證券交易所指出,“新股發(fā)行定價始終是困擾資本市場的‘老大難’問題”。1長期以來,A股市場投機炒作的局面始終存在且未能實質(zhì)性改變,出現(xiàn)了諸如估值扭曲、供需失衡等市場定價問題,極大地限制了資本市場服務(wù)實體經(jīng)濟的能力。因此,如何實現(xiàn)市場化的發(fā)行定價和交易機制安排,通過制度變革推動市場力量均衡博弈與市場化定價機制,是監(jiān)管部門一直以來面臨的重要難題。在這一背景下,資本市場注冊制改革被提上日程,完善資本市場基礎(chǔ)性制度建設(shè)成為了資本市場改革的核心內(nèi)在邏輯。
作為基礎(chǔ)性制度的重大創(chuàng)新,注冊制改革是中國資本市場制度性改革的重要里程碑。實際上,注冊制改革在中國資本市場的落地經(jīng)歷了漫長歷程。早在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已明確指出“推進股票發(fā)行注冊制改革”,然而多年來囿于種種因素卻一直未能實質(zhì)性推進,已然成為了中國資本市場改革的一塊“硬骨頭”。直至2018年,習(xí)近平總書記親自宣布設(shè)立科創(chuàng)板并試點注冊制改革,體現(xiàn)了中央對股票發(fā)行注冊制改革的堅定決心。2020年4月,創(chuàng)業(yè)板改革并試點注冊制正式啟動,標(biāo)志著中國資本市場進入改革“深水區(qū)”。隨著注冊制改革不斷實現(xiàn)歷史性突破,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資本市場基礎(chǔ)制度體系正在加快建立。
科創(chuàng)板基礎(chǔ)性制度改革是一項綜合性增量改革,融合了詢價機制改革、價格限制機制改革等多項制度改革,其初衷是實現(xiàn)市場化的發(fā)行定價和交易定價,通過優(yōu)化價格形成機制、提升市場價格發(fā)現(xiàn)效率,從而優(yōu)化金融生態(tài)環(huán)境、提高資本市場資源配置效率、更好地服務(wù)實體經(jīng)濟發(fā)展。作為資本市場改革“試驗田”,科創(chuàng)板市場的豐富試驗成果和經(jīng)驗積累已進一步輻射至創(chuàng)業(yè)板市場,推進創(chuàng)業(yè)板注冊制改革與功能系統(tǒng)性再造,并為全市場推行注冊制提供條件基礎(chǔ)。在科創(chuàng)板正式誕生兩周年之際,如何厘清基礎(chǔ)制度改革中定價機制改革的市場功能與改革效果,完善詢價機制改革及價格限制機制改革對市場價格信號功能發(fā)揮的促進作用,是當(dāng)前中國資本市場關(guān)注的重點問題,直接關(guān)系到資本市場基礎(chǔ)性制度改革能否激發(fā)市場活力和提高市場效率,這也是本文研究的出發(fā)點。
關(guān)于科創(chuàng)板注冊制改革的既有研究中,國內(nèi)外學(xué)者大多基于成熟市場經(jīng)驗以及法律制度層面,定性分析了注冊制改革的市場功能與模式適用性判別(Morrissey,2010;曹鳳岐,2014;湯欣和魏俊,2016)[16][18][24],而較少基于市場定價效率這一分析視角進行深入定量研究。此外,盡管已有諸多文獻基于A股主板市場,分別探討了一級市場詢價制度或二級市場交易制度功能(劉志遠等,2011;俞紅海等,2013;李東昕等,2014;王朝陽和王振霞,2017;宋順林和唐斯圓,2019;Chen et al.,2019)[21][29][19][26][23][4],科創(chuàng)板市場增量改革的創(chuàng)新實踐則將兩者納入同一改革效應(yīng)分析框架,并為探討二者對市場定價效率的影響及作用機理提供了全新檢驗樣本。因此,本文將圍繞以下問題展開論證:其一,相比A股主板及其他市場,科創(chuàng)板市場運行能否實現(xiàn)更高效率的市場化定價程度,即科創(chuàng)板注冊制改革是否達到中央決策層與證券監(jiān)管層的政策預(yù)期與目標(biāo)?其二,從具體改革路徑來看,發(fā)行定價市場化機制改革與交易定價市場化機制改革如何共同推動股票價格形成?是否在科創(chuàng)板市場定價效率提升的過程中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對上述問題的深入挖掘和論證剖析,正是本文的重點內(nèi)容以及研究價值所在。
針對上述研究問題,本文重點探究了科創(chuàng)板注冊制改革下的詢價機制改革與價格限制機制改革對市場化定價形成的影響效應(yīng)。本文的創(chuàng)新點在于:(1)基于科創(chuàng)板基礎(chǔ)制度改革下的市場定價效率視角,探析科創(chuàng)板詢價機制改革以及漲跌幅限制改革效應(yīng),構(gòu)建科創(chuàng)板市場價格形成改革效應(yīng)的論證框架,為中國資本市場基礎(chǔ)性制度改革提供決策依據(jù)。(2)運用規(guī)范實證方法,考察科創(chuàng)板市場的效率測度與制度評價,為科創(chuàng)板定價機制改革對市場定價效率的改善功能提供了最新的經(jīng)驗證據(jù)。(3)利用科創(chuàng)板作為“改革試驗田”的增量改革優(yōu)勢,挖掘并梳理了詢價機制改革與價格限制機制改革影響市場價格形成的作用路徑,進一步豐富和拓展了相關(guān)領(lǐng)域研究,為監(jiān)管層全面推進基礎(chǔ)制度改革提供有價值的理論依據(jù)。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shè)
(一)科創(chuàng)板基礎(chǔ)制度改革與市場定價效率
為了更好地實現(xiàn)新股發(fā)行定價權(quán)的市場化以及二級市場交易定價的合理性,科創(chuàng)板基礎(chǔ)制度改革中的定價機制改革主要包含了詢價機制改革和價格限制機制改革兩項核心舉措。
針對發(fā)行定價層面,科創(chuàng)板注冊制改革下的詢價機制改革取消了直接定價方式,全面實施以機構(gòu)投資者為參與主體的市場化詢價、定價機制,大幅提高網(wǎng)下發(fā)行比例,同時放開了原有23倍發(fā)行市盈率的新股定價管制,設(shè)置詢價有效報價區(qū)間約束,并充分披露詢價報價信息。主板市場新股發(fā)行價格往往會受到定價上限的約束而被人為壓價,導(dǎo)致新股發(fā)行價格低估的現(xiàn)象普遍(宋順林和唐斯圓,2017)[22];同時承銷商和發(fā)行人大多直接利用剔除最高報價2后的最高價格作為最終發(fā)行價,并未綜合考慮詢價結(jié)果、選擇合理的發(fā)行價格,從而抑制了新股定價效率(Cheung et al.,2009)[5]。科創(chuàng)板詢價機制的市場化改革,旨在促使新股發(fā)行定價更接近于市場預(yù)期估值,更大程度地體現(xiàn)和尊重市場自身對投資標(biāo)的價值判斷,從而抑制虛高報價操縱空間及新股炒作空間,提升市場定價效率與價格發(fā)現(xiàn)功能。
針對交易定價環(huán)節(jié),科創(chuàng)板市場也對A股市場傳統(tǒng)交易機制實行了重要增量改革創(chuàng)新。3首先是直接影響價格形成的漲跌幅限制機制,科創(chuàng)板重點突破了新股上市首日價格最大漲跌幅44%的限制,在新股上市的前5個交易日不設(shè)漲跌幅限制,同時從第6個交易日開始,漲跌幅限制由主板現(xiàn)行的10%放寬至20%。既有研究表明,漲跌幅限制政策是加劇市場波動的重要原因,而放寬甚至放開漲跌幅限制并不會引起市場過度波動,相反能較好地促進市場充分博弈、加快均衡價格實現(xiàn)(Hsieh et al.,2009)[12]。其次是配套的融資融券制度,科創(chuàng)板股票自上市首日起即可作為融資融券標(biāo)的,并優(yōu)化了轉(zhuǎn)融券制度與融券供給機制,改善了基于供給面的賣空約束,加快了市場供需關(guān)系的自發(fā)平衡(Chang et al.,2007)[2]。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shè)1:
H1:科創(chuàng)板市場基礎(chǔ)制度改革有效提升了市場定價效率、加快了市場價格發(fā)現(xiàn)。
(二)詢價機制改革的發(fā)行定價市場化效應(yīng)
若科創(chuàng)板基礎(chǔ)制度改革下的市場定價效率顯著提升,一個重要問題則是,詢價機制改革是如何作用于發(fā)行定價均衡實現(xiàn)?基于既有行為金融學(xué)研究,本文認為“詢價機構(gòu)報價行為”是其中的重要作用路徑,具體來看存在以下三種子路徑。
一是“詢價機構(gòu)報價分歧”路徑。既有研究已為論證“投資者意見分歧會影響資產(chǎn)定價”提供了理論和經(jīng)驗證據(jù)支持(Miller,1977)[14]。Gouldey(2006)[9]將意見分歧理論引入到詢價機構(gòu)報價和一級市場定價的分析框架中,投資者可能出于不同的主觀解讀而產(chǎn)生意見分歧,影響新股發(fā)行定價過程。李冬昕等(2014)[19]運用詢價機構(gòu)意見分歧理論對中國特色IPO“三高”現(xiàn)象進行相應(yīng)解釋,提出詢價機構(gòu)的報價分歧主要來自兩個維度:一是其自身對新股的主觀估值差異,二是二級市場投機炒作產(chǎn)生的再售期權(quán)價值。在科創(chuàng)板注冊制改革下,一方面,發(fā)行人信息和交易所審核信息受到充分披露和揭示,由此詢價機構(gòu)對相關(guān)信息獲取及解讀的差異性應(yīng)當(dāng)有所降低;另一方面,考慮到放開價格限制改革也削弱了投資者“炒新”動機,詢價機構(gòu)報價中所包含的新股炒作溢價程度降低。因此,科創(chuàng)板詢價機制改革通過緩解詢價機構(gòu)意見分歧而有助于提升發(fā)行定價效率。
二是“詢價機構(gòu)報價有效性”路徑。Cornelli and Goldreich(2003)[8]對詢價機制下的新股配售及定價效率進行了研究,發(fā)現(xiàn)詢價過程中機構(gòu)報價形成的訂單集具有較高的新股定價信息含量。國內(nèi)學(xué)者部分選擇基于詢價機構(gòu)報價過程中的競爭與合謀等視角,來解釋IPO定價問題(劉志遠等,2011;俞紅海等,2013)[21][29],發(fā)現(xiàn)詢價機構(gòu)之間的競爭有助于提高IPO定價效率,但機構(gòu)投資者的過度競爭同樣也會導(dǎo)致IPO定價過高。對此,科創(chuàng)板注冊制改革特別針對發(fā)行定價確定了四數(shù)區(qū)間約束4,促使發(fā)行定價綜合考慮詢價結(jié)果及剩余有效報價的平均水平,避免利用剔除最高報價10%比例后的上限直接作為發(fā)行價,以充分尊重市場詢價結(jié)果,從而遏制機構(gòu)投資者出于利益訴求和制度漏洞的虛高報價。因此,科創(chuàng)板詢價機制改革通過提升詢價機構(gòu)報價有效性而有助于提升發(fā)行定價效率。
三是“詢價機制報價定價管制”路徑。不少研究表明,發(fā)行定價管制提高了IPO抑價率,降低了IPO定價效率(Cheung et al.,2009)[5],而放開定價管制顯著降低了IPO首日回報率、提高了新股定價效率(劉志遠等,2011)[21]。王冰輝(2013)[25]基于IPO擇時視角,發(fā)現(xiàn)A股市場的發(fā)行定價管制會給公司帶來較高的融資成本,使其選擇海外上市的動機增強,也因此抑制了A股市場的成長性。科創(chuàng)板詢價機制改革打破了以往A股市場發(fā)行定價存在的“天花板效應(yīng)”,讓市場更好地發(fā)揮了價格發(fā)現(xiàn)功能和定價決定作用,同時也有助于二級市場對新股進行合理定價,降低新股的價值不確定性(宋順林和唐斯圓,2017)[22]。
綜合上述三條作用路徑的學(xué)理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設(shè)2:
H2:科創(chuàng)板基礎(chǔ)性制度改革中的詢價機制改革更好地實現(xiàn)了發(fā)行定價市場化。
(三)價格限制改革的交易定價市場化效應(yīng)
作為金融市場價格穩(wěn)定機制,價格限制機制包含新股上市初期的漲跌幅限制以及日后交易的漲跌幅限制兩個維度。事實上,關(guān)于價格限制的市場功能和作用效果在學(xué)術(shù)界引發(fā)了較大的爭議和討論。支持者認為,價格限制機制可以有效減少交易者成本,并緩解劇烈波動導(dǎo)致的恐慌交易(Chou et al.,2003)[6];在外部沖擊引起市場劇烈波動的特殊情形下,價格限制機制也為市場信息擴散和投資者吸收信息提供了時間,從而緩解市場恐慌情緒、避免市場暴漲暴跌(Greenwald and Stein,1991)[10]。然而反對者則對價格限制的上述功能表示質(zhì)疑,提出價格限制一方面會推遲市場供需平衡、延遲市場價格發(fā)現(xiàn),并導(dǎo)致價格波動外溢,另一方面會干擾市場交易連續(xù)性、限制市場流動性等(Chen et al.,2005)[3]。
從上市初期的價格限制來說,A股主板市場IPO首日限價政策雖然直接抑制了新股上市首日的炒作空間,但也可能同時使得二級市場投資者預(yù)期高度一致,甚至盲目追漲,導(dǎo)致新股發(fā)行上市后二級市場短期內(nèi)價格超漲、長期回報率低下的異象。更嚴重的是,IPO首日限價政策還可能加劇對投資者“炒新”和樂觀情緒的刺激作用,例如新股連續(xù)漲停帶來的財富增值效應(yīng)可能會吸引更多投資者關(guān)注新股和參與“打新”(宋順林和唐斯圓,2019)[23]。科創(chuàng)板放開前五日漲跌幅限制的改革舉措則有助于抑制新股價格操縱,促進新股上市初期市場投資者充分博弈,加快投資者預(yù)期和市場增量信息融入股價,促使市場均衡定價較快形成。
而從日后交易的價格限制來說,當(dāng)交易存在漲跌幅限制時,股價越接近交易上下限,越容易吸引投資者關(guān)注,此時投資者出于追求高利潤或者避免損失的考慮,反而加速了股票價格對漲跌停閾值的觸發(fā)(Hsieh et al.,2009)[12],A股市場以散戶為主的市場結(jié)構(gòu)會進一步加劇過窄的10%漲跌幅限制形成的磁吸效應(yīng)(Wong et al.,2006)[17]。由于散戶投資者掌握市場信息的渠道有限,且對短期收益損失更加敏感,所以呈現(xiàn)出追漲殺跌等非理性投資特征以及盲目跟隨的“羊群效應(yīng)”(Christie and Huang,1995)[7]。這也促成了A股市場特有的“漲停板敢死隊”現(xiàn)象,投機者在股價上漲階段只需利用相對較少的資金便可共同促使股價漲停,吸引散戶投資者關(guān)注,次日即可通過出售股票給追漲的投資者而實現(xiàn)獲利(Chen et al.,2019)[4]。科創(chuàng)板將日后漲跌幅限制由主板的10%放寬至20%,這一改革舉措更好地促進市場充分博弈,緩解過窄漲跌幅限制對市場交易連續(xù)性的干擾和對市場流動性的限制(Chen et al.,2005)[3],從而糾正股票定價扭曲問題,加快均衡價格實現(xiàn),并提高市場定價效率。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shè)3:
H3:科創(chuàng)板基礎(chǔ)性制度改革中的價格限制改革更好地實現(xiàn)了交易定價市場化。
三、研究樣本、變量選擇和描述性統(tǒng)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shù)據(jù)來源
本文以2019年7月22日至2020年4月30日上市的科創(chuàng)板公司為研究樣本。為了避免樣本自選擇偏誤帶來的內(nèi)生性問題,本文主要采用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來消除內(nèi)生影響,以獲得在滬市主板及深市創(chuàng)業(yè)板上市并具有相似特征的公司作為配對樣本,進而對市場定價效率及公司市場表現(xiàn)進行比較研究。借鑒相關(guān)文獻的處理方法(魏志華等,2019)[27],本文的處理步驟如下:首先,篩選配對樣本為同行業(yè)且于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5在滬市主板及深市創(chuàng)業(yè)板上市的公司;其次,將市場屬性虛擬變量(Treat)作為被解釋變量,以新股上市前一年末的公司營業(yè)收入、每股收益、市凈率變量對其進行Logit回歸,并據(jù)此計算傾向得分值;最后,采用最近鄰匹配方法對科創(chuàng)板公司樣本進行1∶3匹配。經(jīng)檢驗,上述處理滿足平衡性假設(shè)和共同支撐假設(shè),即匹配有效。本文所使用的IPO相關(guān)信息數(shù)據(jù)主要來自Wind數(shù)據(jù)庫,詢價報價數(shù)據(jù)來自手工收集整理,上市公司財務(wù)數(shù)據(jù)與市場行情數(shù)據(jù)來自CSMAR數(shù)據(jù)庫。
本文對樣本做如下處理:(1)剔除了首日交易數(shù)據(jù)以及公司財務(wù)特征等關(guān)鍵變量缺失的樣本;(2)剔除了以固定價格方式進行發(fā)行定價的公司樣本,旨在與規(guī)定采用累計投標(biāo)詢價方式的科創(chuàng)板公司相匹配;(3)為了降低異常值的影響,對連續(xù)變量進行上下1%分位的縮尾(winsorize)處理。經(jīng)處理,本文得到共計8021條月度公司觀測值,共包含318家IPO公司,其中科創(chuàng)板IPO公司為94家,滬市主板IPO公司為123家,創(chuàng)業(yè)板IPO公司為101家。
(二)變量定義與指標(biāo)構(gòu)建
1.市場定價效率
借鑒已有研究(李志生等,2015)[20],本文主要基于兩個方面來衡量資產(chǎn)定價效率:一是資產(chǎn)價格的信息發(fā)現(xiàn)效率,本文選擇了股價同步性、相關(guān)系數(shù)指標(biāo);二是資產(chǎn)價格的信息反映速度,本文選擇的相應(yīng)指標(biāo)是價格延遲度。
首先,關(guān)于股價同步性指標(biāo),本文參考Morck et al. (2000)[15]度量個股收益相對市場收益的同步性程度,該代理變量是對股價中公司特質(zhì)信息含量的反向測度。首先構(gòu)建模型(1):
其中ri,t為股票i在第t日的收益率,rm,t則為股票i所在市場的經(jīng)流通市值加權(quán)后的第t日市場收益率,市場因素解釋部分占全部收益率方差的比例正好等于該模型回歸得到的擬合優(yōu)度。隨后運用式(2)進行對數(shù)轉(zhuǎn)換,最終得到股價同步性指標(biāo)SYNCH。指標(biāo)數(shù)值越小,股價中的特質(zhì)信息含量越多,信息效率越高。

其次,關(guān)于相關(guān)系數(shù)指標(biāo),Bris et al.(2007)[1]提出可用當(dāng)期個股收益率與滯后一期市場收益率的相關(guān)系數(shù)來衡量定價效率水平。本文將個股日度收益率關(guān)于滯后一期的市場日度收益率進行按月回歸,所得到的回歸系數(shù)實際上即等價于上述相關(guān)系數(shù),并借鑒李志生等(2015)[20]取回歸系數(shù)的絕對值作為最終定價效率的代理變量ROU。回歸系數(shù)絕對值越小,表示股票所包含的特質(zhì)性風(fēng)險越大,定價效率越高。
再次,關(guān)于價格延遲指標(biāo),Hou and Moskowitz (2005)[11]提出可利用資產(chǎn)價格對市場信息調(diào)整速度的相對效率來衡量定價效率。本文借鑒李志生等(2015)[20]在市場模型中加入市場收益率四期滯后項(如式3所示),并運用式(4)估計價格對信息反應(yīng)的延遲程度。

其中ri,t為股票i在第t日的收益率,rm,t則為股票i所在市場的經(jīng)流通市值加權(quán)后的第t日市場收益率,rm,t-n表示滯后n期的市場收益率,εi,t為隨機誤差項。

價格延遲變量DELAY的定義是四階收益率滯后項回歸系數(shù)之和占全部回歸系數(shù)的比例,滯后項解釋力越弱,意味著價格對信息的反應(yīng)延遲程度越小,即股價的信息反映效率越高。
2.IPO定價效率
借鑒已有研究(Cheung et al.,2009)[5],本文采用IPO抑價率指標(biāo)(IROP_under)來度量新股發(fā)行定價效率。該變量的計算方法為(內(nèi)在價值-新股發(fā)行價格)/內(nèi)在價值,表示新股發(fā)行定價時相對內(nèi)在價值的抑價程度。其中,參考宋順林和唐斯圓(2019)[23]的方法,本文采用可比公司法估計公司的內(nèi)在價值,內(nèi)在價值=發(fā)行時所屬行業(yè)市盈率×新股上市后每股收益;另外對于科創(chuàng)板部分虧損企業(yè)而言,其內(nèi)在價值的計算方法則修改為:估計的內(nèi)在價值=發(fā)行時所屬行業(yè)市凈率×新股上市后每股凈資產(chǎn)。
3.上市后市場表現(xiàn)
本文分別從上市首日市場表現(xiàn)和上市后市場表現(xiàn)來刻畫科創(chuàng)板股票定價的市場化程度。
一是IPO溢價率變量IROP_over。該變量的計算方法為(新股上市收盤價-內(nèi)在價值)/內(nèi)在價值,表示新股上市后二級市場股價的高估程度。其中,為了保證指標(biāo)的可比性,本文選擇的新股上市收盤價分別對應(yīng)為:科創(chuàng)板公司上市首日收盤價、非科創(chuàng)板公司開板日(打開漲停板之日)收盤價。主要原因是,對于近三年上市的滬市主板與創(chuàng)業(yè)板公司而言,魏志華等(2019)[27]指出由于新股上市首日存在44%的漲幅限制,首日收盤價無法充分反映其市場價值而出現(xiàn)連續(xù)漲停現(xiàn)象,只有當(dāng)收盤時首次打開漲停板才意味著市場真正消化了新股的相關(guān)信息。此外,本文采用前述可比公司法估計公司的內(nèi)在價值。
二是首日實際收益率IPOret。已有文獻通常采用首日收益率來計算新股上市首日的市場表現(xiàn)和新股定價效率(Cheung et al.,2009)[5]。為了得到更為準(zhǔn)確、合理、且具有可比性的新股首日收益率,對于科創(chuàng)板公司,首日實際收益率即為(新股上市首日收盤價-新股發(fā)行價格)/新股發(fā)行價格;對于非科創(chuàng)板公司,采用新股上市后首個收盤未漲停日的收盤價來替代新股上市首日收盤價。
針對上市后市場表現(xiàn),本文與現(xiàn)有文獻一致(Kao et al.,2009)[13],采用累計超額收益率(CAR)和購買并持有超額收益率(BHAR)兩個度量指標(biāo)。同樣地,對科創(chuàng)板公司與非科創(chuàng)板公司分別選擇上市次日、首個收盤未漲停日次日為起點,分別計算公司上市后短期(30個交易日、60個交易日、90個交易日)以及中長期(120個交易日、180個交易日)的累計超額收益率(CAR)和購買并持有超額收益率(BHAR),計算公式分別如下:

表1 主要變量定義

其中,ri,t為股票i第t日收益率,rm,t為股票i所在市場經(jīng)流通市值加權(quán)后的市場收益率。其他主要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
(三)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tǒng)計
表2展示了基于A股市場整體的主要變量描述性統(tǒng)計結(jié)果。一是,近三年A股市場上市新股整體的市場表現(xiàn)(CAR和BHAR)均值為負,并且隨著時間的加長,負值水平提升,表明整體來看新股上市后的短中期市場表現(xiàn)并不理想,這也印證了既有研究發(fā)現(xiàn)的A股IPO公司長期“弱市”現(xiàn)象(魏志華等,2019)[27],新股上市初期的溢價需要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被逐漸消解,由此推動股價逐步向內(nèi)在價值回歸。二是,A股科創(chuàng)板塊新股的IPO溢價率達到116%左右。從最大值來看,新股上市打開漲停板后收盤價也高于內(nèi)在價值近40倍。這表明上市初期新股價格呈現(xiàn)較高的溢價水平,二級市場整體投機炒作氛圍較為濃厚。此外,新股也呈現(xiàn)一定程度的抑價發(fā)行特征,平均IPO抑價率達到32%左右,意味著新股發(fā)行價格大約為內(nèi)在價值的70%,體現(xiàn)了主板和創(chuàng)業(yè)板市場發(fā)行定價管制的抑制作用。

表2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tǒng)計結(jié)果
為了更直觀地考察科創(chuàng)板市場與主板市場及創(chuàng)業(yè)板市場定價效率的差異,本文采用t檢驗對關(guān)鍵變量進行均值差異檢驗,結(jié)果如表3所示。其一,科創(chuàng)板市場的股價同步性(SYNCH)、相關(guān)系數(shù)(ROU)、價格延遲度(DELAY)、非流動性比率(Amihud)均顯著更低,即表明科創(chuàng)板市場的定價效率以及流動性水平顯著優(yōu)于滬市主板市場及創(chuàng)業(yè)板市場。其二,科創(chuàng)板市場IPO抑價率(IROP_under)較低甚至均值為負,表明科創(chuàng)板股票一級市場價格管制程度顯著改善,科創(chuàng)板新股首日的IPO溢價率(IROP_over)較高,表明市場參與者對科創(chuàng)板公司上市具有較高的樂觀預(yù)期;此外,科創(chuàng)板股票的首日實際收益率(IPOret)較低,意味著科創(chuàng)板市場通過上市初期的充分博弈,較快地形成了定價均衡,由此打破了主板及創(chuàng)業(yè)板市場存在的“短期價格超漲、長期回報低下”的扭曲異象。其三,從新股上市后市場表現(xiàn)來看(CAR和BHAR),科創(chuàng)板市場股票上市后短期內(nèi)的市場表現(xiàn)均值為負,但隨著時間推移,市場表現(xiàn)均值轉(zhuǎn)負為正、逐漸增大,該變化趨勢則與滬市主板及創(chuàng)業(yè)板市場新股上市后累積收益負向加深的趨勢形成了鮮明對比。

表3 科創(chuàng)板市場定價效率及市場表現(xiàn)的均值差異檢驗結(jié)果
四、實證結(jié)果與分析
(一)科創(chuàng)板市場定價效率優(yōu)化效應(yīng)
為了解答“相比A股主板及其他市場,科創(chuàng)板市場運行能否實現(xiàn)更高效率的市場化定價程度”這一問題,一方面,借鑒李志生等(2015)[20],本文擇取了公司財務(wù)特征與交易行情特征兩個方面的控制變量,并基于面板數(shù)據(jù)構(gòu)建了如下實證模型:

其中,被解釋變量Efficiency代表市場定價效率的三個代理變量,分別是股價同步性SYNCH、相關(guān)系數(shù)ROU、價格延遲度DELAY;變量Treat是市場屬性虛擬變量;其余控制變量定義見表1。模型估計穩(wěn)健標(biāo)準(zhǔn)誤經(jīng)股票層面聚類調(diào)整。如果研究假設(shè)H1成立,則解釋變量Treat的回歸系數(shù)β1應(yīng)顯著為負,表明無論是從信息發(fā)現(xiàn)效率層面還是信息反映速度層面,科創(chuàng)板市場定價效率均顯著優(yōu)于滬市主板市場與創(chuàng)業(yè)板市場。
另一方面,本文借鑒魏志華等(2019)[27]所考慮的新股市場表現(xiàn)影響因素,選擇了公司IPO財務(wù)特征作為控制變量,并基于新股IPO首日截面數(shù)據(jù)構(gòu)建如下實證模型:

其中,被解釋變量為累積超額收益絕對值(|CAR|)或買入并持有超額收益絕對值(|BHAR|),變量數(shù)值越小表明新股上市后的股價越趨于理性。若假設(shè)H1成立,則變量Treat的回歸系數(shù)β1應(yīng)顯著為負,即相比滬市主板與創(chuàng)業(yè)板市場,科創(chuàng)板市場定價效率提升。
表4呈現(xiàn)了科創(chuàng)板市場定價效率是否相比滬市主板市場及創(chuàng)業(yè)板市場顯著提升的檢驗結(jié)果。結(jié)果表明,科創(chuàng)板市場的股價同步性(SYNCH)、相關(guān)系數(shù)指標(biāo)(ROU)顯著較低,意味著科創(chuàng)板市場價格能夠更加真實且充分地反映所有市場信息,特別是基于公司微觀層面的特質(zhì)信息能被較好地納入資產(chǎn)定價過程;此外,科創(chuàng)板市場的價格延遲度(DELAY)也顯著較低,表明科創(chuàng)板市場的信息反映速度較快,資產(chǎn)價格能夠更為及時且準(zhǔn)確地吸收最新市場信息。綜合上述結(jié)論,基礎(chǔ)制度改革顯著提升了科創(chuàng)板市場的定價效率,促進市場更好發(fā)揮價格發(fā)現(xiàn)功能,較好地達到了改革預(yù)期目標(biāo),即假設(shè)H1證明成立。

表4 科創(chuàng)板市場定價效率提升效應(yīng)的檢驗結(jié)果
此外,本文還基于新股市場表現(xiàn)的視角,進一步論證基礎(chǔ)制度改革是否有效改善了科創(chuàng)板市場的定價效率,回歸結(jié)果如表5所示。結(jié)果顯示,市場屬性虛擬變量Treat的回歸系數(shù)顯著為負,而且隨著時間推移,回歸系數(shù)呈現(xiàn)負向增長趨勢,意味著科創(chuàng)板市場的新股定價效率更高且更為理性。該結(jié)論也與現(xiàn)有研究指出A股主板新股股價存在“短期過度上漲、長期表現(xiàn)弱勢”特征形成了鮮明對比。該結(jié)論也進一步印證了基礎(chǔ)制度改革的實施效果已較好地達到了改革預(yù)期目標(biāo)。有鑒于此,從整體來看,科創(chuàng)板創(chuàng)新實踐的基礎(chǔ)性制度改革將有助于資本市場價格信號功能、配置資源和服務(wù)實體經(jīng)濟的能力的有效發(fā)揮。
(二)詢價機制改革的發(fā)行定價市場化效應(yīng)

表5 科創(chuàng)板市場表現(xiàn)優(yōu)化效應(yīng)的檢驗結(jié)果
下一步,本文需要探究的問題是,作為科創(chuàng)板基礎(chǔ)制度改革中定價機制改革的重要環(huán)節(jié),科創(chuàng)板詢價機制改革如何影響一級市場發(fā)行定價效率與新股市場表現(xiàn),及其是否存在“詢價機構(gòu)報價行為”的作用機制。
首先,為了考察科創(chuàng)板新股發(fā)行定價效率是否有所改善,本文構(gòu)建了回歸模型(9):

其中,被解釋變量|IROP_under|是IPO抑價率的絕對值,該指標(biāo)反映了新股發(fā)行定價相對內(nèi)在價值的偏離程度,數(shù)值越小則表明新股發(fā)行定價越趨近于內(nèi)在價值,意味著市場發(fā)行定價效率越高(Cheung et al.,2009)[5]。如果研究假設(shè)H2成立,則解釋變量Treat的回歸系數(shù)β1應(yīng)顯著為負,表明科創(chuàng)板新股發(fā)行定價效率顯著優(yōu)于滬市主板市場與創(chuàng)業(yè)板市場。
其次,為了論證科創(chuàng)板詢價機制改革是否存在“詢價機構(gòu)報價行為”作用機制,本文借鑒中介效應(yīng)檢驗思想,在模型(9)的基礎(chǔ)上構(gòu)建了模型(10)和模型(11)。

其中,被解釋變量Reform代表了詢價機構(gòu)報價行為的統(tǒng)一代理變量,分別指代詢價機構(gòu)報價分歧(Stdxunjia)、報價有效性(Lowprc)。關(guān)于報價分歧(Stdxunjia)指標(biāo),本文借鑒李冬昕等(2014)[19]采用詢價機構(gòu)的報價差異性進行度量,即為所有詢價機構(gòu)報價的標(biāo)準(zhǔn)差。對于部分公司存在極少數(shù)遠遠高于其他機構(gòu)報價的異常報價,本文將此類異常報價視為存在惡意操縱目的的無效報價并將其剔除。關(guān)于報價有效性(Lowprc)指標(biāo),該指標(biāo)度量了詢價機構(gòu)報價上限與新股發(fā)行定價之間的差異程度,若指標(biāo)數(shù)值越大,則意味著新股發(fā)行價格越低于網(wǎng)下投資者有效報價的上限,表明新股發(fā)行定價更理性且充分地考慮了詢價結(jié)果及剩余有效報價的平均水平。
在模型(11)中,本文將詢價機構(gòu)報價行為Reform及其與市場屬性虛擬變量(Treat)的交叉項(Treat×Reform)同時作為主要解釋變量,令I(lǐng)PO抑價率絕對值(|IROP_under|)關(guān)于該兩項解釋變量進行回歸檢驗,以此檢驗“詢價機構(gòu)報價行為”路徑是否成立。

最后,為了印證上述詢價機制改革效應(yīng)是否有助于改善科創(chuàng)板中長期定價效率,本文將模型(11)的被解釋變量替換為新股市場表現(xiàn)絕對值變量(|CAR|/|BHAR|)。其中,回歸系數(shù)β2反映了詢價機制改革下的“詢價機構(gòu)報價行為”路徑對科創(chuàng)板定價效率的中長期影響。

表6呈現(xiàn)的是科創(chuàng)板詢價機制改革效應(yīng)及其作用機制的檢驗結(jié)果。從中可以看出,科創(chuàng)板股票的IPO抑價率絕對值顯著低于主板市場股票,即科創(chuàng)板市場的新股發(fā)行定價偏離程度有所緩解、發(fā)行定價效率有所提升,充分體現(xiàn)了詢價機制改革對發(fā)行定價效率的促進作用。在注冊制詢價機制改革實施后,詢價機構(gòu)的報價分歧(Stdxunjia)顯著降低,同時報價有效性(Lowprc)顯著提升,并且通過檢驗詢價機構(gòu)報價行為對發(fā)行定價的影響,可以看到主板市場中較高的詢價機構(gòu)報價分歧容易引起IPO定價高估,這與李冬昕等(2014)[19]結(jié)論相一致;但對于科創(chuàng)板市場而言,注冊制改革下的詢價機制改革通過降低詢價機構(gòu)意見分歧,反而改善了新股發(fā)行抑價現(xiàn)象、更好地實現(xiàn)了發(fā)行定價的市場化。此外,科創(chuàng)板詢價機制改革通過改善詢價機構(gòu)的報價有效性,同樣提升了新股發(fā)行定價效率。上述結(jié)論均表明詢價機構(gòu)報價行為是科創(chuàng)板詢價機制改革提升市場發(fā)行定價效率的重要作用機理。

表6 科創(chuàng)板詢價機制改革效應(yīng)及其作用機制檢驗
一方面,在“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的注冊制改革理念下,一級市場信息透明度大幅提升,詢價機構(gòu)對相關(guān)信息獲取以及解讀的差異性也相應(yīng)降低,同時科創(chuàng)板市場交易機制改革抑制了上市初期投資者“炒新”等非理性行為,詢價機構(gòu)報價中所包含的新股炒作溢價程度也由此降低,因此詢價機構(gòu)報價之間的意見分歧程度減小;另一方面,詢價機制改革使得科創(chuàng)板新股發(fā)行價格顯著低于網(wǎng)下投資者有效報價的上限,與主板市場和創(chuàng)業(yè)板市場大多直接利用有效報價上限作為發(fā)行價格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該結(jié)果也意味著注冊制改革使得詢價報價信息充分融入發(fā)行定價之中,以保證新股的定價過程充分尊重市場詢價結(jié)果。此外,科創(chuàng)板詢價機制改革也突破了發(fā)行定價的管制約束,不同于主板市場新股發(fā)行價格往往會受到市盈率倍數(shù)限制而被人為壓價、導(dǎo)致新股發(fā)行價格低估的普遍現(xiàn)象,科創(chuàng)板市場抑價發(fā)行的異象不復(fù)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略高于內(nèi)在價值的有效發(fā)行定價。該結(jié)果也論證了,科創(chuàng)板詢價機制的市場化改革可促使新股上市的發(fā)行定價更接近于市場預(yù)期估值,更大程度地體現(xiàn)了市場自身對投資標(biāo)的價值判斷,有助于抑制潛在的新股炒作空間。由此,假設(shè)H2即可證明 成立。
進一步地,本文探究了上述詢價機制改革效應(yīng)對科創(chuàng)板市場定價效率的中長期影響,結(jié)果如表7所示。從Panel A“詢價機構(gòu)報價分歧”子路徑來看,短期內(nèi)科創(chuàng)板詢價機構(gòu)報價分歧對市場表現(xiàn)的影響與主板市場及創(chuàng)業(yè)板市場并無較大差異;但中長期來看,在科創(chuàng)板市場中,詢價機構(gòu)報價分歧越小的新股定價效率更高且更趨于理性,而對于非科創(chuàng)板市場則結(jié)論相反。由此可知,科創(chuàng)板注冊制詢價機制改革降低了詢價機構(gòu)報價的分歧程度或差異性,進而提升了發(fā)行定價效率,遏制了新股上市后中長期內(nèi)的投機行為與股價非理性上漲。
從Panel B“詢價機構(gòu)報價有效性”子路徑來看,對科創(chuàng)板市場而言,詢價機構(gòu)的報價越向下偏離網(wǎng)下投資者有效報價的上限,則股票定價越趨于理性。但對于主板市場和創(chuàng)業(yè)板市場,結(jié)論恰恰相反。本文認為原因可能是,主板市場和創(chuàng)業(yè)板市場中的承銷商和發(fā)行人大多直接利用剔除最高報價后的最高價格作為最終發(fā)行價,并未綜合考慮詢價結(jié)果、接受市場詢價過程,因此最終發(fā)行價相對有效報價上限的負向偏離會被市場反向解讀為悲觀信號,導(dǎo)致上市后股價的投機性與非理性增強。而在科創(chuàng)板注冊制改革后,由于報價結(jié)果及詢價信息含量已被充分融入發(fā)行定價之中,發(fā)行價相對有效報價上限的偏離意味著高價發(fā)行的操縱空間被壓縮,因此該類股票的定價效率更高、市場表現(xiàn)更加理性。由此可知,科創(chuàng)板注冊制改革改善了詢價機構(gòu)報價的有效性,并以此提升了科創(chuàng)板新股定價效率。
(三)價格限制改革的交易定價市場化效應(yīng)
2014年7月至今,A股市場新股發(fā)行采用一級市場價格調(diào)控(不超過23倍市盈率)疊加二級市場首日漲停限價(發(fā)行首日漲幅不超過44%)的聯(lián)合機制安排。盡管此項政策實施的初衷是為抑制投資者“炒新”行為、防止新股上市首日股價過度炒作,然而事實上IPO首日限價政策卻收效甚微,反而成為了刺激投資者“炒新”行為和投機泡沫累積的助推器(魏志華等,2019)[27]。對此,科創(chuàng)板市場對漲跌幅交易機制實施了重大改革創(chuàng)新,不僅完全放開了上市前五日的漲跌幅限制,也放寬了之后交易日的漲跌幅限制。

表7 科創(chuàng)板詢價機制改革效應(yīng)的中長期影響效應(yīng)
首先,為了論證科創(chuàng)板放開首日限價改革是否有助于抑制市場“炒新效應(yīng)”,本文基于新股截面數(shù)據(jù)構(gòu)建了實證模型(13):

其中,被解釋變量IPO_variable代表的是新股上市首日市場表現(xiàn)的兩個代理變量,分別是IPO溢價率(IROP_over)、首日實際收益率(IPOret),由此刻畫出科創(chuàng)板放開首日限價改革效應(yīng)。同時,為了剝離出價格限制改革對新股上市首日市場表現(xiàn)的凈影響效應(yīng),本文在模型控制變量中加入IPO抑價率(IROP_under)來控制新股發(fā)行定價抑價程度對首日市場表現(xiàn)的影響。基于前文的理論分析,本文認為科創(chuàng)板放開首日限價改革效應(yīng)可能存在“投資者博弈充分性”和“投資者情緒”兩條作用路徑。科創(chuàng)板放開IPO首日漲跌幅的改革舉措有助于促進新股上市初期市場投資者充分博弈,并緩解首日價格限制對投資者“炒新”和樂觀情緒的刺激作用,加快市場均衡定價形成。為了進一步檢驗科創(chuàng)板放開首日限價改革效應(yīng)是否存在上述兩條作用路徑,本文分別以首日實際換手率(Turnover)和投資者情緒(InvSent)度量上市初期的投資者博弈充分性和投資者樂觀情緒。首日實際換手率越高則意味著市場交易越活躍、投資者博弈越充分。為了保證指標(biāo)的可比性,本文以新股上市當(dāng)天至首個收盤未漲停日的區(qū)間換手率來計算非科創(chuàng)板上市公司的首日實際換手率,避免僅考慮上市首日而嚴重低估換手率水平。本文同樣遵循前文的內(nèi)在機制檢驗思想,借鑒(宋順林和唐斯圓,2019)[23]將上述兩個機制變量及其與市場屬性虛擬變量(Treat)的交叉項加入模型(13)。
在此基礎(chǔ)上,為了探究日后放寬漲跌幅限制改革能否提升科創(chuàng)板市場定價效率,本文基于面板數(shù)據(jù)構(gòu)建了實證模型(14)。考慮到科創(chuàng)板詢價機制改革引起的發(fā)行定價差異、以及融券賣空機制改革對市場價格發(fā)現(xiàn)功能的潛在提升作用,為了剝離上述兩種情形對市場定價效率的影響,本文在控制變量中加入了IPO抑價率(IROP_under)來控制新股發(fā)行定價抑價程度對日后市場定價效率的影響,同時加入融券標(biāo)的虛擬變量(Ifshort)及其與融券賣空交易比率(Shortratio)交叉項來控制融券賣空機制和賣空交易行為對日后定價效率的影響。參考已有研究(俞紅海等,2018)[28],融券賣空交易比率(日度融券賣出量/當(dāng)日交易量)可有效度量和捕捉融券賣空交易行為。為了避免上市初期制度改革對市場定價效率的影響,本文還剔除了新股上市后最初30天的觀測數(shù)據(jù)。此時主要解釋變量Treat的回歸系數(shù)β1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創(chuàng)板日后漲跌幅限制放寬至20%改革對市場定價效率的影響效應(yīng),若假設(shè)H3成立,此時回歸系數(shù)β1應(yīng)顯著為負,表明科創(chuàng)板日后放寬漲跌幅限制改革能提升科創(chuàng)板市場定價效率,推動交易定價市場化進程。

表8 科創(chuàng)板價格限制改革的首日表現(xiàn)效應(yīng)及其作用機制檢驗

表8呈現(xiàn)的是科創(chuàng)板價格限制改革的首日表現(xiàn)效應(yīng)及其作用機制檢驗結(jié)果。在控制新股發(fā)行定價效率的影響后,科創(chuàng)板股票的IPO溢價率(IROP_over)和首日實際收益率(IPOret)顯著較低。基于IPO溢價率和首日實際收益率指標(biāo)所代表的“炒新效應(yīng)”特征,結(jié)果顯示科創(chuàng)板放開首日限價的改革舉措有效抑制了A股市場以往長期存在的投資者“炒新”行為以及新股上市初期價格操縱現(xiàn)象。從作用機制來看,科創(chuàng)板股票的首日實際換手率和投資者情緒對IPO溢價和首日實際收益率的影響顯著為負,而滬市主板和創(chuàng)業(yè)板股票顯著為正,該結(jié)論印證了主板市場的換手率指標(biāo)更多地體現(xiàn)為投機性而非流動性,此時首日限價政策通過刺激投資者投機炒作和樂觀情緒而加劇了IPO溢價。相反,科創(chuàng)板新股上市首日交易越活躍則意味著投資者博弈更充分、IPO溢價更回歸理性,且不容易受到市場投資者情緒的正向影響,表明科創(chuàng)板放開首日限價改革通過促進新股上市初期市場投資者充分博弈、抑制投資者情緒溢出影響股價,加快市場均衡定價形成,因此,“投資者博弈充分性”和“投資者情緒”兩條作用路徑是科創(chuàng)板放開首日限價改革效應(yīng)的重要內(nèi)在機制。
進一步地,本文探究了科創(chuàng)板價格限制改革對市場定價效率的影響。在控制詢價機制改革引起的發(fā)行定價效率差異以及融券賣空機制改革的疊加影響后,檢驗結(jié)果(見表9)表明科創(chuàng)板交易定價市場化機制改革顯著提升了市場定價效率,加快了股票價格發(fā)現(xiàn)過程。從作用機制來看,科創(chuàng)板股票的換手率對市場定價效率的影響顯著為負,而滬市主板和創(chuàng)業(yè)板股票顯著為正,該結(jié)論同樣也印證了主板市場的換手率指標(biāo)更多地體現(xiàn)為投機性而非流動性。與主板市場相比,科創(chuàng)板漲跌幅限制的放寬給予了市場投資者更加充分的博弈空間,緩解了過窄漲跌幅限制對市場交易連續(xù)性的干擾和對市場流動性的限制(Chen et al.,2005)[3],也增大了股票流動性對市場定價效率的正向影響,加快了市場供需平衡和均衡定價的形成。因此,“投資者博弈充分性”與“股票流動性”路徑是該效應(yīng)下的重要內(nèi)在機制。上述結(jié)果均為科創(chuàng)板價格限制改革的市場效率優(yōu)化功能提供了證據(jù)支持,即假設(shè)H3證明成立。
(四)穩(wěn)健性檢驗
考慮到除了前文提及的基礎(chǔ)性制度設(shè)計差異,科創(chuàng)板市場和非科創(chuàng)板市場之間還可能存在短期的新舊板塊固有差異,如科創(chuàng)板市場作為新興板塊市場受關(guān)注度更高、投資者交易活躍度更高等,進而可能反映在新板塊流動性更好、定價效率更高等特征維度。為了避免新舊板塊潛在差異可能造成的影響偏誤,本文在剔除科創(chuàng)板成立初期三個月的觀測數(shù)據(jù)后,再次進行回歸檢驗,如表10所示,回歸結(jié)果依然穩(wěn)健成立。
五、結(jié)論及政策建議
作為基礎(chǔ)制度改革的重大創(chuàng)新,科創(chuàng)板市場改革的核心是新股發(fā)行定價權(quán)的市場化,以及二級市場交易定價的合理性。基于市場定價效率視角,本文論證了發(fā)行定價市場化機制改革和交易定價市場化機制改革的影響效應(yīng),發(fā)現(xiàn):(1)相比主板市場及試點注冊制改革之前的創(chuàng)業(yè)板市場,科創(chuàng)板市場定價效率顯著提升、價格發(fā)現(xiàn)功能顯著優(yōu)化,因此科創(chuàng)板基礎(chǔ)制度改革經(jīng)檢驗較好地達到了改革預(yù)期目標(biāo)。(2)從具體改革路徑來看,科創(chuàng)板市場在詢價機制改革下更好地實現(xiàn)了發(fā)行定價市場化。詢價機制改革基于“詢價機構(gòu)報價行為”路徑,即通過抑制詢價機構(gòu)報價的差異程度、改善詢價機構(gòu)報價的有效性,降低了科創(chuàng)板IPO定價偏誤程度、提升了發(fā)行定價效率。(3)科創(chuàng)板市場在價格限制改革下更好地實現(xiàn)了交易定價市場化。放開首日限價改革通過“投資者博弈充分性”和“投資者情緒”路徑降低了科創(chuàng)板新股IPO溢價率和首日實際收益率;另外,在控制詢價機制改革引起的發(fā)行定價效率差異以及融券賣空機制改革的影響后,日后放寬漲跌幅限制的改革舉措通過“投資者博弈充分性”和“股票流動性”路徑顯著提升了市場定價效率。基于上述多維度改革舉措,科創(chuàng)板市場的價格發(fā)現(xiàn)功能得以優(yōu)化,而較高的市場定價效率也有助于資本市場實現(xiàn)通過價格信號引導(dǎo)資源配置、服務(wù)實體經(jīng)濟的功能。

表10 科創(chuàng)板市場定價效率提升效應(yīng)的穩(wěn)健性檢驗結(jié)果
研究結(jié)果表明,中國資本市場通過引入以注冊制改革、定價機制改革等為代表的基礎(chǔ)性制度改革來提升市場定價效率的目標(biāo)已取得了實質(zhì)性進展且卓有成效。資本市場的健康運轉(zhuǎn)離不開以市場為主導(dǎo)的價格形成機制,未來應(yīng)當(dāng):一是,進一步優(yōu)化注冊制詢價機制改革,實現(xiàn)詢價對象的理性專業(yè)化和詢價過程的審慎規(guī)范化,同時監(jiān)管機構(gòu)應(yīng)對于經(jīng)常性虛高報價的機構(gòu)予以調(diào)查并加大責(zé)任追究和處罰力度,促進新股發(fā)行定價市場化,引導(dǎo)市場關(guān)注企業(yè)自身內(nèi)在價值;二是,基于科創(chuàng)板基礎(chǔ)制度改革下的定價機制改革經(jīng)驗,發(fā)揮資本市場基礎(chǔ)制度改革的“輻射效應(yīng)”,進一步推進A股主板市場基礎(chǔ)性交易制度改革,例如取消新股發(fā)行定價管制、放開上市初期漲跌幅限制等,并同步完善融券賣空交易、T+0交易等配套機制改革,提升我國資本市場定價效率,實現(xiàn)資本市場的功能系統(tǒng)性再造。 ■
注釋
1. 摘自上海證券交易所官方網(wǎng)站于2019年9月30日發(fā)布的文章“設(shè)立科創(chuàng)板并試點注冊制,引領(lǐng)資本市場全面深化改革”(http://www.sse.com.cn/home/theme/70anniversary/doc/c/c_20190924_4919728.shtml)。
2. 根據(jù)《證券發(fā)行與承銷管理辦法》的規(guī)定,采用詢價方式首次公開發(fā)行的股票,在網(wǎng)下投資者報價后,“發(fā)行人和主承銷商應(yīng)當(dāng)剔除擬申購總量中報價最高的部分,剔除部分不得低于所有網(wǎng)下投資者擬申購總量的10%,然后根據(jù)剩余報價及擬申購數(shù)量協(xié)商確定發(fā)行價格。”
3. 2019年6月13日,劉鶴副總理在“陸家嘴論壇”明確指出,“以更加市場化、便利化為導(dǎo)向推進交易機制改革”是中國資本市場持續(xù)健康發(fā)展需要重點關(guān)注的問題之一。2019年9月11日,中國證監(jiān)會易會滿主席在《人民日報》發(fā)表《努力建設(shè)規(guī)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署名文章,特別指出交易機制改革關(guān)系到資本市場的穩(wěn)定健康發(fā)展,因此對于金融風(fēng)險防控和經(jīng)濟高質(zhì)量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
4. 按照《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chuàng)板股票發(fā)行與承銷實施辦法》第九條規(guī)定,“發(fā)行人和主承銷商應(yīng)當(dāng)在申購前,披露網(wǎng)下投資者剔除最高報價部分后有效報價的中位數(shù)和加權(quán)平均數(shù),以及公開募集方式設(shè)立的證券投資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資產(chǎn)管理產(chǎn)品、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和基本養(yǎng)老保險基金的報價中位數(shù)和加權(quán)平均數(shù)等信息。”同時第十條規(guī)定,“初步詢價結(jié)束后,發(fā)行人和主承銷商確定的發(fā)行價格(或者發(fā)行價格區(qū)間中值)超過第九條規(guī)定的中位數(shù)、加權(quán)平均數(shù)的孰低值的,發(fā)行人和主承銷商應(yīng)當(dāng)在申購前至少一周發(fā)布投資風(fēng)險特別公告。”由此,上述四類數(shù)據(jù)信息共同約束了發(fā)行人和主承銷商的發(fā)行定價決策(簡稱四數(shù)區(qū)間約束)。
5. 為了保證控制組在行業(yè)屬性限定下有足夠樣本以供處理組進行匹配,本文延長了主板及創(chuàng)業(yè)板樣本期間的選擇范圍,因此與科創(chuàng)板樣本期間范圍存在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