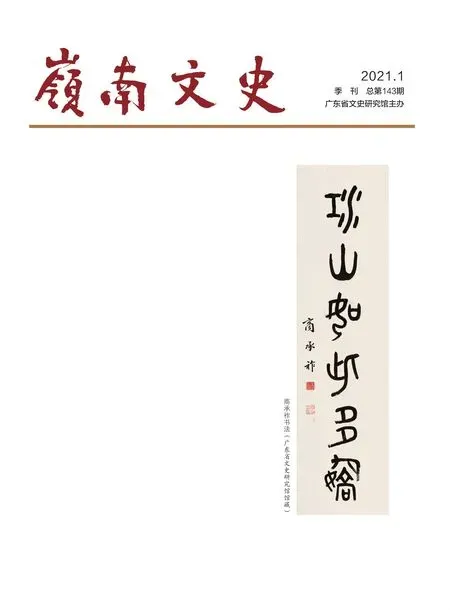陳獨秀在廣州的創黨活動
余宏檁

陳獨秀
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陳獨秀曾三次來廣州,進行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活動。陳獨秀從1920年到廣州開始進行革命活動,先后指導中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等的召開,創建廣州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1923年中共三大的召開、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實現和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都留下了陳獨秀不朽的業績。
一、陳獨秀主管廣東教育期間打下了廣州建黨的輿論基礎
(一)陳獨秀與“安馬分流”
無政府主義在廣州的傳播早于馬克思主義,其代表人物是劉師復。1915 年劉師復去世后,黃凌霜、區聲白、梁冰弦等人繼承其衣缽。他們在學生和工人中有較大影響,還控制了茶樓、理發等行業工會組織,創辦了《民聲》《民風》《勞動者》周刊等。這些刊物在揭露反動政府和資本家壓迫剝削勞動人民,號召群眾起來斗爭方面,起過積極作用;但也使一些青年受其蒙騙,誤把無政府主義當作最革命的理論,分不清無政府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的區別。無政府主義的主要錯誤是把工人受壓迫剝削的根源歸咎于政府,聲稱要打倒一切政府和權威,強調個人的絕對自由。這種小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思潮,曾在廣州泛濫一時,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一大障礙。
1920年12月底,陳獨秀到廣州。這段時間,維經斯基隨陳獨秀到廣州,一直到1921年1月12日。在沒與陳獨秀取得統一意見的情況下,他解散社會主義者同盟,所謂解決與無政府主義者的“分流”問題。陳獨秀對Anarchism安那其主義即無政府主義,是有一定保留態度的,對維經斯基親自操作“安馬分流”是不完全茍同的,“預日托故離開廣州作短程旅行,比不出席”。[1]因為“分流”無疑削弱了無產階級力量,無政府主義中的有益部分,一些有改造社會思想的進步青年,無疑被一刀切“分流”出去了,機器工人也在此時被“分流”出去,最后走到黨的對立面。而這些進步青年和機器工人如在此時加以引導和領導,無疑是有成長為革命力量的。當然,陳獨秀在《下品的無政府黨》中也貶斥那些真正的“下品”者,但同時指出了無政府主義者中有不少“純潔的青年”。曾慶榴先生提出的“數十年后‘姓社’‘姓資’的爭論”時,“鄧小平這時發明了‘不爭論’”,“當年‘姓安’、‘姓馬’的問題,是不是也可以照此辦理呢?”[2]或許是解決當年“安馬”是否“分流”的較好辦法。但是歷史不可能重來,陳獨秀當年的回避態度也應有各種復雜的歷史背景和問題使然。
(二)批判無政府主義,主張無產階級專政

陳獨秀在《廣州群報》創刊號上發表的文章《敬告廣州青年》
無政府主義在廣東傳播較早,在廣大工人中有較大的影響。實際上,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在推翻舊社會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問題在于推翻后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以及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制度,在這點上是有分歧的,或者說是還沒有達成共識。由于陳獨秀對社會主義的宣傳,強調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必然性,與無政府主義的觀點大相徑庭,所以引起無政府主義者的注意。陳獨秀到廣州之前,俄國人米諾而、別斯林與黃凌霜、梁冰弦、區聲白等無政府主義者已成立一個名為“廣東共產黨”的組織。[3]“1999年11月,日本學者石川禎浩給筆者寄來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收藏的幾份有關早期廣東共產黨組織史的資料,其中的一份是剪自1920年12月24日《廣州晨報》的剪報,內容是轉述在廣州市內各馬路散發的一張印刷品,署名為‘共產黨廣州部’”。[4]說明1920年前后,廣州曾出現署名“共產黨廣州部”的無政府主義印刷品。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宣傳要“自創一個無牧師、無皇帝、無總統、無法官、無獄吏、無警察管轄和無寄生蟲之社會”。[5]1920年12月底,陳獨秀到廣州后,首先與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通過書信的形式進行討論,這些書信公開在《廣東群報》上發表,可以說是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論戰。
1921年1月15日,陳獨秀在廣東省公立政法學校作題為《社會主義批評》的演講,剖析各種“社會主義”理論觀點,并著重批評了無政府主義。1月22日,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在《群報》發表《致陳獨秀先生書》,反對陳獨秀的觀點。在這場論戰中,區聲白三次詰難,陳獨秀三次辯駁。陳獨秀在廣州期間,通過文章、演講、書信等方式,在革命道路、生產與分配、階級斗爭、社會組織、國家政權等問題上,對無政府主義進行了系統的批判,并著重闡明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作用。他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不許有產階級得到政權的意思,這種制度乃是由完成階級戰爭消滅有產階級做到廢除一切階級所必經的道路。”[6]以陳獨秀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的論戰,宣傳馬克思主義,批判無政府主義,使社會主義者從思想上劃清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界限。
1921年8月,陳獨秀將這些書信在廣州出版發行的《新青年》上公之于眾,宣傳社會主義和批判無政府主義,但很大成分是基于學術上的討論和批判。陳獨秀還在《新青年》《勞動與婦女》等刊物上發表《中國式的無政府主義》《下品的無政府黨》等一系列文章,還通過演講、書信等形式,對無政府主義進行了全面的批判,批判無政府主義者宣揚的絕對自由的虛無主義,宣傳了馬克思主義,從而劃清了科學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界限,使一些一度受無政府主義所蒙騙的革命青年轉為信仰馬克思主義。
(三)創新教育,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

1921年元旦《廣州群報》增刊有關于陳獨秀到達廣州的報道
1920年12月,應廣東省長陳炯明之邀,陳獨秀首次到穗,出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當時,粵系軍閥陳炯明自福建漳州率粵軍回粵,趕走了原來踞守在廣東的桂系軍閥莫榮新。陳炯明主政廣東后,邀請當時在上海的陳獨秀到廣東,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職務。陳獨秀上任前向陳炯明提出教育不受行政干擾和教育要得到行政保護及經費支持等問題,得到陳炯明難得的支持。陳炯明許諾“保證決以全省歲入十分之一以上為教育經費,無論如何,絕不短發”。[7]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是非常有利的條件。利用這一條件,陳獨秀在給廣東教育帶來了改革和新做法新思路的同時,主持創辦了宣傳員養成所、機器工人夜校、注音字母教導團等。尤其是1921年初開辦的位于廣州起義路維新橫路素波巷30號,今廣州市第十中學內的“廣東省立宣傳員養成所”“注音字母教導團”,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廣東支部成立的地方,也是1922年前中國共產黨廣州早期黨組織的主要活動地和《青年周刊》的通訊處。“廣東省立宣傳員養成所”的開辦,主要是培養具有共產主義理論知識的人才,培養向廣大工農群眾進行革命宣傳、傳播馬克思主義知識的宣傳員,譚植棠任教務主任,譚平山、楊章甫、鄧瑞仁等任教員。學員來自廣東各地,學習的主要內容有國語常識、社會科學、共產主義知識、三民主義教程。此外,還創辦了“俄語學校”“機械工人夜校”。除讓學員們學習一般的文化知識外,主要是讓他們能學習到十月革命經驗和馬克思主義,以提高基層宣傳干部的政治理論水平。同時,還派梁復然、王寒燼等到佛山組織建立土木工會和理發工會,開展工人運動。
1921年4月,《新青年》(原稱《青年雜志》)因被上海法國巡捕房查封而被迫遷來廣州,更加強了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力量。《青年雜志》是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主編的,1916年第二卷第一號改名為《新青年》,提出民主和科學兩大口號,標志著中國新文化運動興起。1916年年底,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協助陳獨秀把刊物的編輯部遷到北京,李大釗、吳虞、劉半農、胡適、魯迅等成為《新青年》的撰稿人后,刊物逐漸獲得廣大知識分子和群眾的歡迎。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新青年》由民主主義的刊物逐漸轉變成社會主義的刊物,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上起了重大作用。特別是1920年8月,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組織——中共上海發起組成立后,陳獨秀任書記,《新青年》從第八卷開始就作為中共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與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各流派進行了理論上的斗爭,在思想上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新青年》遷到廣州后改成季刊,季刊第一期的發刊詞《新青年的新宣言》明白地揭示了無產階級的理論性刊物的性質,肯定過去的“《新青年》雜志是中國革命的產兒”,曾“成為革命思想的代表”;同時又指出“中國的真革命乃獨有勞動階級方能擔負此等偉大使命”,因此,“《新青年》乃不得不成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羅針”。[8]《新青年》自改成季刊后,就變成了純粹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刊物,變成了黨的最早的理論性機關刊物之一。它宣傳了黨在革命迅速開展時期中的路線和策略,貫徹了統一戰線的方針,并大力介紹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和國際工人運動經驗,對反動的實用主義思想展開了深刻的批評。
二、陳獨秀推動廣州的創黨活動順利進行
1920年8月,在中國工業和工人運動中心的上海,建立起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中共上海發起組,陳獨秀任發起組書記。從此,上海就成為創建全國無產階級政黨的活動中心。接著,北京、武漢、長沙、濟南等城市也先后建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1920年9月,俄國共產主義者蘇俄政府代表米諾爾(即斯托楊諾維奇)、佩斯林(亦稱佩爾林或別斯林,俄文為“МиpТpyдa”)從天津到廣州建立俄國通訊社。他們伙同區聲白、梁冰弦等無政府主義者于1920年底成立共產黨,并出版《勞動者》,在工人中有一定影響。據《廣州共產黨的報告》稱:“去年年底,B和佩斯林來到廣州,建立了俄國通訊社,對組織工會采取了措施,并在《勞動界》[9]周刊上發表了文章。黃凌霜同志把他們引薦給廣州革命界,這樣一來,他們就被無政府主義者包圍了。盡管組織了共產黨,但是與其稱作共產黨,不如稱作無政府主義的共產黨。黨執行委員會的九個委員當中,七個是無政府主義者,只有米諾爾和佩斯林同志是共產主義者。由于觀點不一致,譚平山、譚植棠和我拒絕加入這個小組。”[10]也有一種說法,廣東學者沙東迅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對“五四運動在廣東”的專題進行調研過程中,先后走訪了譚祖蔭、劉石心等(現均已辭世)有關人士,內容也涉及到廣東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創建等問題。據譚祖蔭、劉石心回憶,“當時無政府主義者只是與兩位蘇俄政府代表聯系,并沒有建立什么組織”。[11]這種說法無考。
在上海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不久,1920年8月,陳獨秀決定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并讓俞秀松負責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同月,俞秀松、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金家鳳、袁振英、葉天底等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在上海新漁陽里6號,建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由俞秀松擔任團書記。此后,上海團中央局繼續聯絡各地創建團組織。到第二年春,在北京、長沙、武漢、天津、濟南等地社會主義青年團先后成立時,陳獨秀也通過書信與譚平山等人相約在廣州組織團組織。1920年下半年,譚平山、楊匏安、阮嘯仙、劉爾崧等人在廣州組織了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為廣州黨組織的建立做了鋪墊。
1920年12月,陳獨秀因受邀到廣東任廣東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長,經香港,于12月26日抵穗,先入住大東酒店。陳獨秀后搬至廣州泰康路太平沙回龍里九曲巷11號二樓,并自起名“看云樓”。在這里,陳獨秀開展了一系列建立黨組織和革命宣傳活動,直至1921年9月離穗返滬。陳獨秀到廣州后,找到7 月已回到廣州開展新文化運動的譚平山,并讓其擔任廣東教育行政委員會副委員長,委托他籌組廣州黨組織。在譚平山的協助下,陳獨秀召集陳公博、譚植棠和省立甲工學生阮嘯仙、周其鑒、劉爾崧及楊匏安等人,重起爐灶,籌建廣州黨組織的活動(有別于早期無政府主義者成立之共產黨)。1921年3月,作為全國6個之一的第一批黨的早期組織廣州共產黨組織正式成立。這一時期,全國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城市有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如加上1920年秋施存統、周佛海等在日本東京的旅日支部和1921年張申府、周恩來、趙世炎、劉清揚等在法國巴黎成立的旅法支部,總共應為8個。這些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名稱不一,有的稱“共產黨”,有的稱“共產黨支部”或“共產黨小組”,但它們的性質相同,都是組成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后來長期被通稱為“共產主義小組”。新成立的廣州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黨員有陳獨秀、譚平山、譚植棠、沈玄廬、袁振英、李季等,米諾爾和佩斯林也參與創建,一共8人。陳獨秀任書記(后為譚平山),活動據點主要在素波巷。

陳獨秀在廣州的住址“看云樓”所在地——廣州太平沙九曲巷(今北京路太平沙)
1921年初“宣傳員養成所”和“注音字母教導團”等各種學校的創辦,也為培養黨的組織骨干和為發展組織做了必要的準備。《廣東群報》是1920年10月開始出版的日報,編輯有譚平山、譚植棠、鄧瑞仁等。其內容主要是反映社會現實生活,報道勞工運動狀況,宣傳馬克思主義,介紹世界新聞和蘇俄的消息等。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把《廣東群報》和上海發起組成員沈玄廬主編的《勞動與婦女》作為自己的機關刊物,加上當時由上海遷來廣州出版的《新青年》,發展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
正值廣州早期黨組織建立前后,1920年成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沒有明確的宗旨,加上經費和人事的變動等原因,思想比較混亂,主要體現在對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理解上。“那時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只不過帶有社會主義傾向,并沒確定了那一派社會主義。所以分子很復雜:馬克思主義者也有,無政府主義者也有,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也有,工團主義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12]各地成員主要都是對社會主義思想向往的青年組成,在此前受五四運動影響和啟蒙,但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認識還比較膚淺和混亂,或者說一知半解。無政府主義者的言論和宣傳,往往對這些剛剛加入團組織的進步青年造成了誤導。因此,當時團的活動和會議的舉行和商議往往發生爭執和沖突。“在廣東、北京每一次開會均有爭論,并且有時甚至動武,組織上表現的非常沖突”。[13]由于指導思想上的分歧,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大多退出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并在1921年4月前后開始分化了。無政府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逐漸分道揚鑣,也導致1921年5月前后團的工作一度出現停頓。這種現象引起了陳獨秀、蔡和森等人的注意。他們意識到“繼續同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共事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開始以共產主義組織的名義發表關于他們目標和原則的宣言,而他們的目標和原則同我們對共產主義的基本概念是背道而馳的”。[14]

1921年4月遷到廣州昌興街26~28號的《新青年》雜志社
青年團組織是黨的后備力量,如果不加整頓,勢必會影響剛剛建立的共產黨組織的發展。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把社會主義青年團作為黨的預備力量,決定加強對各地團組織的領導。隨后召開的共產國際三大和青年共產國際二大,給予中國建青年團組織作出指示。根據中國代表張太雷帶回的精神,陳獨秀在廣州對青年團中的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混淆進行整頓和統一,明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吸取1920年初宗旨不一致的經驗教訓,明確規定“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團體”,[15]以區分無政府主義思想。1921 年底,陳獨秀讓譚平山等人籌備成立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2月26日,廣東團組織創辦的《青年周刊》創刊。在創刊《宣言》中明確提出:“‘社會革命’四個大字,就是我們的先行旗幟。”[16]周刊是八開小報,每號出四版,楊匏安、阮嘯仙、郭瘦真是周刊的主要撰稿人。從3月7日第二號開始,周刊逢周日出版,通訊處則設在素波巷19 號。3月14日,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青年周刊》成為廣東團組織的機關刊物。3月22日,周刊第四號刊登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當天的《成立大會演說撮錄》,其中聲明“本團的宗旨是研究馬克思主義,并企圖實現馬克思主義”。[17]周刊的內容很廣泛,除報道青年團的活動、反映各地情況外,還傳遞世界信息,轉載共產國際指示。《青年周刊》是五四運動后發行較廣、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刊物之一,它對廣東乃至全國青年傳播馬克思主義發揮了廣泛的影響。
在廣州期間,陳獨秀還指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和早期旅法黨組織的成立。陳獨秀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起草黨綱和致與會代表的信,并就組織和工作提出幾點意見,如關于黨員的發展與教育、黨的組織原則、黨的紀律、黨的群眾工作等。雖然召開地點是在上海,但陳獨秀為這次會議的順利召開一直在做多方面的指導工作,并關注會議召開的全過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多次催促陳獨秀親自赴滬參加會議,但由于陳獨秀當時兼任廣東大學預科校長,正忙于籌建校舍,遂指派陳公博和包惠僧代為出席中共一大。早期旅法黨組織的成立也是在陳獨秀的關心下成立的。據相關資料記載:張申府1977年回憶:“周恩來和劉清揚(時在法國)都是我介紹入黨的,時間約在1921年1月或2月,先介紹劉清揚,然后由我和劉清揚介紹周恩來。當時入黨手續是和周恩來談話后,寫信向陳獨秀(時在廣州)報告。”[18]
1921年7月23日,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和《關于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確定黨成立后的中心任務是組織工人階級,領導工人運動。在陳獨秀缺席的情況下,大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中共一大后,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指出,陳獨秀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不應再兼任資產階級政府的官員,要求陳獨秀回滬主持中央工作。同年8月,陳獨秀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回上海前,陳獨秀讓譚平山等人在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基礎上適時組織成立中國共產黨廣東支部(譚平山為書記,譚植棠負責宣傳),隸屬中共中央局領導。中共廣東支部成立后,大力發展組織,特別重視在工人中發展黨員,培養了許多黨員和干部,為廣東成為大革命的策源地做了組織上的準備。中共一大后,先后吸收阮嘯仙、劉爾崧、楊匏安、馮菊坡、王寒燼、羅綺園、楊章浦、黃裕謙、郭植生、梁復然、陳適曦、張善銘、譚天度等入黨。10月,陳獨秀正式辭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職務,全力領導黨組織將重心放在工人運動和黨團組織的發展上。至1922年6月,中共廣東支部共有黨員32人,其中一半是工人。由于廣東黨組織的不斷發展擴大,1922年,黨的活動地點逐步轉移到司后街(今越華路)楊家祠,原處仍然作為廣東團組織的活動地點。
三、在陳獨秀審時度勢中,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最終形成
不可否認,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力量是薄弱的,客觀上需要更多的革命力量的合作或加入。在尋求合作力量的過程中,早在1922年陳獨秀就對孫中山和陳炯明作了分析,認為兩方都“希望很少”。同年6月30日,他在給維經斯基的函中說:“南方孫文與陳炯明分裂,孫恐不能制陳,陳為人言行不能一致,在南方也不能有所建設,他對于社會主義,我確知道他是毫無研究與信仰。我們很希望孫文派之國民黨能覺悟改造,能和我們攜手,但希望也很少。”[19]

1922年4月下旬,陳獨秀第二次來廣州后,召集準備出席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代表大會的黨團領導干部,在高第街素波巷召開工作會議。圖為修繕后的會議舊址。
在蘇俄有關檔案解密之前,關于陳獨秀與共產黨人怎樣加入國民黨或者說加入國民黨方式的歷史問題是模糊的,其實情況應從西湖會議說起:1922年4月4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開全會,馬林提出共產黨人直接加入國民黨的意見,而陳獨秀是堅決反對的。其反對的理由可在陳獨秀給維經斯基的信中了解一二:“(一)共產黨與國民革命之基礎及所據之基礎不同;(二)國民黨聯美國,聯張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三)國民黨未曾發表黨綱,在廣東以外之各省人民視之,仍是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共產黨倘若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會),永無發展之機會;(四)廣東實力派陳炯明,名為國民黨,實則反對孫逸仙派甚然,我們倘若加入國民黨,立即受陳派之敵視,即在廣東亦不能活動;(五)孫逸仙派向來對于新加入之分子,絕對不能容納其意見及假以權柄;(六)廣東、北京、上海、長沙、武昌各區同志對于加入國民黨一事,均已開會議決絕對不贊成,在事實上亦已無加入之可能。”[20]這可以證明那些認為是陳獨秀決定共產黨人直接加入國民黨甚至與陳獨秀后期一些問題聯系起來的觀點是有待商榷的。
對于怎樣加入國民黨的問題和國共聯合的問題,陳獨秀非常重視。他為此事與張國燾一起回到廣州連續召開了三次會議,直到1922年5月中旬才回滬。1922年4月底,陳獨秀主持在廣州召開中共黨團領導干部會議,會議除傳達1月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關于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問題的精神外,就是著重討論了怎樣與國民黨聯合的問題。按出席會議的蘇俄全權代表達林回憶:“4月底5月初在廣州舉行的共產黨的會議上,關于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問題引起了熱烈的爭論。”“關于這個問題的爭論持續了好幾天。陳獨秀動搖不定,但長時間的討論以后他認識到了統一戰線的策略,但沒有通過一定的決議,會議決定繼續討論。”[21]從這些資料中不難看出,當時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對于共產黨人以什么樣的方式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的重大問題上是比較慎重的,認識是不斷深化的。同年5月初,陳獨秀出席在廣州召開的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和青年團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指導兩個大會提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口號。6月,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提議邀請國民黨及社會主義各團體召開聯席會議,采取“黨外合作”的形式建立民主主義的革命聯合戰線。“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就中國民主革命的重大問題,向社會各界公開自己的政治主張,也是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分析中國社會狀況,解決中國革命的新起點。它為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完成制定黨的民主革命綱領的歷史任務,奠定了基礎。”[22]7月,中共二大召開。于8月下旬,中共中央特別會議(第二次西湖會議)召開,蘇俄代表馬林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要求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但受到陳獨秀的反對,同時也表示:如果這是共產國際的不可改變的決定,也只能服從。最后,陳獨秀妥協,但條件是必須改組國民黨,得到李大釗的贊成。為了黨組織的生存和發展,在這段時間,陳獨秀高度重視廣東勢力分析,曾赴惠州勸說陳炯明與孫中山處理好關系,甚至勸其加入共產黨,未果。從這些情況分析,陳獨秀告誡黨內同志注意:“廣東恐怕不久必有變故。我們應有所適從。”[23]不久,“孫陳事變”爆發,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立即斷絕與陳炯明一切關系,支持孫中山,不因孫中山暫時受挫而改變黨的政策,有力促進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國共合作的實現。
第二次西湖會議后,陳獨秀在馬林和李大釗的協助下,拜訪孫中山,與國民黨建立聯系,并根據共產國際的精神和二次西湖會議的決定,帶頭加入國民黨,第一批同時加入的還有李大釗、蔡和森、張太雷。在此期間,陳獨秀受黨中央委派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并根據大會《關于國共合作的決議》中關于國共合作的精神,籌備召開中共三大。

中共三大舊址

1923年9月1日,在廣州出版發行的《陳獨秀先生講演錄》
1923年6月12 —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順利召開。在中共三大召開前,中共廣東區委受大會委托,租賃了房子作為會址和代表宿舍。同時,各個委員會接到中央通知,都要求選派代表參加中共三大。中央對參加中共三大的代表作出具體要求:以產業工人為主體,從事工農革命運動的主要負責人和省、區的書記。北方區共選出12名代表,是全國各區代表中人數最多的,他們是:李大釗(時任北方區委書記)、羅章龍、王荷波、王一仲、王俊、張德惠、何孟雄、孫云鵬、陳濤、劉天章等。兩湖區有:毛澤東、陳潭秋、項英等。江浙區有:徐梅坤、王振一、于樹德、金佛莊等。廣東區有:譚平山、馮菊坡、阮嘯仙、劉爾崧等。中央代表為:陳獨秀、張國燾、張太雷。此外,從法國回來的蔡和森、向警予和從蘇聯回來的瞿秋白也參加了會議,劉仁靜以中共出席共產國際四大代表的身份列席會議。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參加了中共三大。出席中共三大的代表共約40人(有一說是30多人,但陳獨秀得票最高是“40票”。[24]故代表最少應是40名),代表著全國黨員 420 人。

中共三大情景復原圖之一。站立者為陳獨秀。
中共三大的召開沒有舉行開幕儀式,由陳獨秀主持。一個多星期的會議日程安排得十分緊湊。12日上午,陳獨秀代表中央作關于第二次代表大會以來的工作報告,下午由馬林在會上報告國際形勢和國際工運問題。第二天,代表們就陳獨秀報告進行討論。第三、第四天,由各地代表匯報一年來的工作情況。瞿秋白在會上簡要介紹共產國際“四大”的情況,陳潭秋報告“二七”慘案的經過,孫云鵬講述京漢鐵路大罷工被捕工人的救濟工作,毛澤東等還就農運工作發言。會議經過討論,決定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的方針。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宣言》《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以及黨綱草案、勞動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等項議案。選出由陳獨秀、蔡和森、羅章龍、譚平山、毛澤東等人組成的中央局。中共三大主要歷史功績是確定了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以推動國民革命運動的發展。
陳獨秀在廣州的創黨活動和相關歷史活動,一定程度上說明陳獨秀在這段歷史期間的思想、工作、活動和作出的貢獻。陳獨秀在廣州的創黨活動,使廣州成為黨創建時期重要的誕生地;成為繼上海、北京之后的黨的創建地;成為黨早期組織成立的國內六個城市之一。陳獨秀對黨的創建、國共合作的實現、推動建立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等,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注釋:
[1] 海隅孤客(梁冰弦):《解放別錄》。(臺灣)文海出版社印行,第35頁。
[2][4] 曾慶榴:《陳獨秀在廣州若干歷史斷片的檢視》。中共廣州市委黨史研究室、廣州市中共黨史學會編《廣州黨史》,季刊,2009年12月第15期,第26-30頁。
[3] 1920年10月10日出版的《勞動者》第二號,發表《共產黨的粵人治粵主張》文章。轉錄“廣東共產黨”的一份傳單《苦的平民!怎樣才是快樂的呢?》。這是至今“廣東共產黨”名稱最早出處。
[5][8][16][17] 中共廣州市委黨史文獻研究室編:《廣州紅色史跡》。嶺南美術出版社,2020年5月,第1版,第4-6、11頁。
[6] 陳獨秀:《社會主義批評》。1921年1月15日,《獨秀文存》第一卷第547頁。
[7]《民國日報》1920年12月12日、18日。
[9] 俄文為“МиpТpyдa”,應為《勞動者》周刊。
[10]《廣州共產黨的報告》,沒有署名。根據內容判斷,作者可能為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廣州代表陳公博,無考。
[11]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紅廣角》。2011年4月,沙東迅:《九訪中共廣東黨的創建見證人——訪譚祖蔭(一)》第28—30頁。《紅廣角》2011年6月,沙東迅:《九訪中共廣東黨的創建見證人——訪劉石心(一)》第31—32頁。
[12][15]《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大會》(1922年5月),見《“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26-27頁。
[13] 蔡和森:《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見《“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78頁。
[14] 張太雷:《致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書面報告》(1921年6月10日)。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出版社,1997年1月,第175頁。
[18]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共產主義小組》,下冊,第915頁。
[19][20]《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二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303-304、222-223頁。
[21] [蘇]C.A.達林:《中國回憶錄1921-1927》,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1981年3月,第1版,第79—138頁。
[22]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黨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9月,第99頁。[蘇]C.A.達林:《中國回憶錄1921-1927》,第79—138頁。
[23] 陳公博:《我與共產黨》《“二大”和“三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103頁。
[24]選票原件在俄羅斯,復制件保存于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