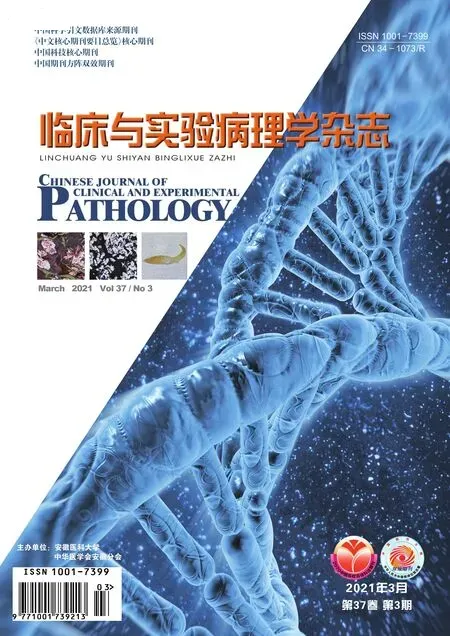肺原發性囊性滑膜肉瘤(單向型)1例
鄭 潔,張立東,孫雅靜,劉 敏,劉可欣,姜忠敏
患者男性,24歲。主因“胸悶氣短5 h”于2019年7月13日入院,診斷為左側自發性氣胸,經保守治療,患者肺復張良好,拔除胸管后出院。2019年10月17日患者再次無明顯誘因出現胸悶憋氣癥狀,活動時加重,休息后未見明顯緩解,無發熱、咯血、胸痛及呼吸困難等癥狀。胸部CT示:左側胸腔前部見氣體密度影,左肺組織壓縮60%,左肺見斑片影,邊緣模糊,提示左側氣胸,左側肺大泡,左肺壓縮>50%(圖1),為求進一步診治入院。患者既往體健,無吸煙史,無遺傳性疾病家族史,否認藥物過敏史。查體:體溫36.4 ℃,脈搏80次每分鐘,呼吸18次每分鐘,血壓110/70 mmHg。右肺呼吸音清晰,左側呼吸音消失,無胸膜摩擦音。入院診斷:(1)左側自發性氣胸;(2)肺大泡。入院后吸氧,完善相關檢查明確無手術禁忌,于2019年10月21日在全麻下行胸腔鏡左側肺大泡切除+胸膜腔粘連封閉術。

圖1 胸CT示:左側氣胸,左側肺大泡
病理診斷眼觀:灰褐色楔形肺組織1塊,大小3.4 cm×0.7 cm×0.2 cm,吻合口長3.4 cm,肺膜表面可見一灰白色囊泡,大小1.5 cm×0.9 cm×0.2 cm。鏡檢:少許肺組織與不規則囊壁結構相連(圖2),囊壁由單一密集短梭形細胞構成(圖3),核形態較規則,核分裂象少見,表面被覆間皮細胞。免疫表型:vimentin、BCL-2(圖4)、EMA(圖5)、Calretinin、β-catinin陽性,CD99(圖6)、HBME、SMA部分陽性,Ki-67增殖指數熱點區為15%,desmin、CK陰性。FISH檢測融合基因SYT/SSXT陽性(圖7)。

②③④⑤⑥⑦
病理診斷:(左肺)囊性滑膜肉瘤(synovial sarcoma, SS)。
討論SS是一種間葉性梭形細胞惡性腫瘤,一般中青年較多見。該病通常發生于四肢大關節周圍軟組織,也有發生在關節外部位的報道,如肝、腎、心臟等[1-2]。原發于肺者罕見,特別是肺囊性SS尚未見相關報道。肺SS最常見臨床癥狀為咳嗽、咯血、胸痛以及胸悶氣短,也可表現為自發性氣胸,低熱和體重減輕少見。該病胸部CT通常表現為肺內實性腫塊,邊緣較光滑,偶見切跡樣改變[3]。本例為囊性病變,發生在年輕人,以胸悶氣短反復氣胸為首發癥狀,發生于肺膜表面,組織學表現為囊性,同時胸部CT提示氣胸,所以與肺大泡難以鑒別。如再次遇到此類肺大泡患者可行MRI協助診斷避免出現誤、漏診。
肺SS的診斷及鑒別診斷主要依靠病理組織學及免疫組化標記,對于疑難病例檢測特異性細胞遺傳學/分子異常協助診斷。組織學上SS分為單向型和雙相型兩種,以單相型最為常見,完全由梭形細胞成分組成,胞質少,胞核深染,呈圓形、卵圓形或短梭形,分裂象不明顯,細胞密集呈束狀或編織狀排列,界限不清,間質黏液變性、囊性變、骨化和血管外皮瘤樣等一系列形態學特征在SS中較多見[4-5]。雙相型由梭形細胞和上皮樣細胞混合排列而成,即在梭形細胞背景中可見灶性上皮樣區域,呈裂隙樣、腺管狀、乳頭狀結構,核圓形,染色質顆粒狀,偶見核仁,常空亮伴黏液分泌。本例鏡下主要表現為囊性結構,緊貼肺膜表面,表被間皮,囊壁主要由單一密集短梭形細胞構成,局部可見玻璃樣變及血管外皮瘤樣結構。部分間質疏松水腫呈黏液樣改變。大多數SS中vimentin、CK、CK7、CK19、EMA、BCL-2、CD99陽性,SMA和Calretinin在部分SS中呈局灶陽性,30%以上的SS有S-100細胞核內和細胞質內陽性,CD34和desmin通常為陰性。SS細胞遺傳學標志為t(X;18)、t(p11;q11)易位,形成STY-SSX融合基因。不管哪種組織學類型,90%以上的SS都發現有此易位,并且應用FISH或RT-PCR法檢測SS染色體易位具有特異性,適用于SS的診斷和鑒別診斷[6]。本例免疫組化及FISH結果支持為肺囊性單相型SS。鑒別診斷首先排除肺轉移性SS和肺大泡,需要進行詳細的臨床和影像檢查才能確診;其它包括胸膜肺母細胞瘤、梭形細胞癌、惡性間皮瘤、纖維肉瘤和平滑肌肉瘤等,需要結合免疫組化及FISH檢測結果協助鑒別診斷。
肺SS治療主要以手術切除為主,根據分期行放、化療輔助治療。該患者預后較差,平均生存期23個月,也有生存期超過5年的病例報道[7]。本例為肺原發性囊性SS,手術病變完整切除后未行任何輔助治療,術后2個月行PET-CT檢查未發現可疑病變,隨訪4個月未出現任何陽性體征。由于肺囊性SS發病少,其生物學行為及預后尚需進一步隨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