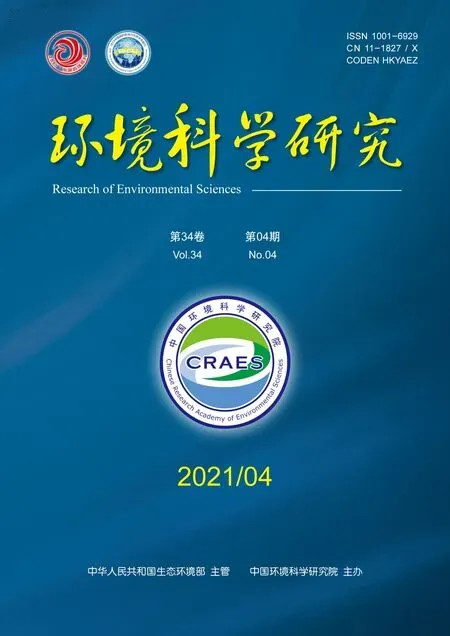呼倫湖砷的時空分布特征及成因分析
車霏霏, 君 珊, 陳俊伊, 郭云艷, 王書航*, 包文旗
1.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 湖泊水污染治理與生態修復技術國家工程實驗室, 北京 100012 2.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 國家環境保護湖泊污染控制重點實驗室, 北京 100012 3.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生態環境監測站, 內蒙古 呼倫貝爾 021008
As(砷)是一種廣泛存在于自然界中的生物非必需元素,因其部分化合物的生物毒性和高致癌風險引起全球范圍內的廣泛關注. 環境中的As能夠在自然過程或人為活動作用下進入水體,地表水ρ(As)范圍跨度較大,可從0.5 μg/L到 5 000 μg/L[1]. 通常,As在天然水體中多以As(Ⅴ)(砷酸鹽)和As(Ⅲ)(亞砷酸鹽)等無機As形態存在,其中As(Ⅴ)在富氧水體中占主要優勢,As(Ⅲ)則多在還原條件下存在,后者的生物毒性約為前者的25~60倍[2-3]. 此外,水體中的無機砷還可能通過浮游藻類的生物代謝轉化為微量的有機As化合物,其中以毒性較低的MMA(一甲基砷)和DMA(二甲基砷)為主[4-5]. 除上述生物作用外,水體中的As能夠以吸附或共沉淀等形式累積在沉積物中[6],因此沉積物通常是水環境中As的一個重要“儲庫”;同時,沉積物中部分不穩定As也可在一定環境條件影響下向水體遷移[7-8],從而引起As的二次釋放風險.
呼倫湖是亞洲中部草原區最大的湖泊,也是我國第五大湖泊,于1992年被批準為國家級濕地自然保護區,在呼倫貝爾草原的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9]. 近年來,受持續暖干氣候和人類活動等因素影響,呼倫湖水情發生劇烈變化,進而導致湖濱濕地大面積銳減,湖泊水生生態系統退化,草場退化、土地沙化等生態環境問題,水質持續下降. 據相關報道[10],近五年來呼倫湖湖水的As超標問題突顯,基于高As暴露帶來的環境風險,深入調查研究呼倫湖的As污染問題刻不容緩. 目前,已有一些研究[11-13]對呼倫湖沉積物中包括As在內的重金屬開展調查,指出沉積物中As的潛在風險相對較高,且As的生物有效性呈自湖泊西北部向東南部遞減的趨勢. 然而,目前關于呼倫湖水體As的相關調查研究較少. 因此,該研究對呼倫湖水體及沉積物中As的時空分布進行詳細調查,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了相關環境因素對As分布特征的影響,以期為深入了解呼倫湖水As分布及高As成因提供數據及理論支撐.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域
呼倫湖流域(包括海拉爾河流域及哈拉哈河流域)位于中國和蒙古國境內,流域面積2.92×105km2,其中我國境內流域面積占總面積的37%. 湖區位于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西端,屬半干旱大陸性氣候,降水量少,蒸發強烈,全年盛行西北風. 呼倫湖水量補給主要來源于地表徑流、降水及地下水,其中入湖河流主要包括克魯倫河、烏爾遜河以及海拉爾河(通過引河濟湖工程入湖),排水通道為新開河;河流沿岸地勢開闊,畜牧業較為發達. 歷史上呼倫湖最大水域面積超過 2 300 km2,平均水深約6 m,但近幾十年來受氣候變化等影響,湖泊水量補給減小,湖泊面積呈萎縮趨勢[14].
1.2 樣品采集與預處理
采用6 km×6 km網格布點法布設呼倫湖采樣點,并分別于2018年10月(秋季)、2019年3月(冬季)、2019年5月(春季)和2019年7月(夏季)對呼倫湖水面下約20 cm的表層水及0~10 cm的表層沉積物進行采集,共采集水和沉積物樣品各215個,其中3月為冰封期,同步采集冰層樣品;同時,于2019年5月和2019年7月在入湖河流采集表層水,并在5月同步采集表層沉積物,共采集河流水樣28個,沉積物樣品14個. 采樣點布設見圖1.
水樣置于保溫箱中低溫保存,其中用于測定As形態的水樣經0.45 μm水系濾膜過濾后添加0.25 mol/L EDTA-Na2以固定形態[15],1周內完成As總量及其形態的分析測定;沉積物封裝在干凈的自封袋中低溫保存,并在實驗室內完成冷凍干燥、研磨過篩等預處理步驟.

圖1 呼倫湖及入湖河流采樣點位布設Fig.1 Sampling sites and location of Lake Hulun and inflowing rivers
1.3 指標測定
水樣ρ(TAs)(TAs為總As)的測定方法參照HJ 678—2013《水質 金屬總量的消解 微波消解法》,即在水樣中加入濃HNO3并進行微波消解,消解后使用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譜儀(ICP-MS,Agilent7700,安捷倫公司,美國)測定消解液中ρ(TAs);冰層樣品待冰樣融化后同樣加入濃HNO3進行微波消解,并使用ICP-MS測定消解液中ρ(TAs);水樣ρ(DTAs)(DTAs為溶解態TAs)通過對原水樣過濾并直接使用ICP-MS測定獲得. 水樣As形態測定參照文獻[16]中高效液相色譜(HPLC,Agilent1200,安捷倫公司,美國)與ICP-MS聯用法,使用流動相通過PRP (苯乙烯-二乙烯基苯共聚物)-X100(250 mm×4.1 mm)型陰離子交換柱完成As形態分離.
沉積物TAs通過微波消解法提取,并由ICP-MS測定w(TAs)[17];同時,采用BCR連續提取法[18]對2019年5月的沉積物As賦存形態進行分析,具體形態包括F1 (可交換態及碳酸鹽結合態As)、F2 (Fe/Mn 氧化物結合態As)、F3 (有機物及硫化物結合態As)及F4 (殘渣態As),各形態含量均通過ICP-MS測定得到.
此外,為分析呼倫湖As的來源及分布影響因素,對表層水ρ(TFe)(TFe為鐵總量)、pH、沉積物w(TFe)、以及沉積物黏粒(<4 μm)、粉粒(4~63 μm)、砂粒(63~2 000 μm)占比等物理化學指標進行測定,測定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呼倫湖水體及沉積物物理化學指標Table 1 Physical and chemical parameters in water and sediments of Lake Hulun
2 結果與討論
2.1 呼倫湖水體中As的時空分布及組成特征
2.1.1ρ(TAs)的時空變化
根據各季節調查結果,呼倫湖全湖水體ρ(TAs)在6.6~87.3 μg/L之間,平均值為47.0 μg/L;其中春季、夏季、秋季、冬季的ρ(TAs)平均值分別為(53.1±5.7)(45.4±7.2)(40.3±6.6)(48.0±20.5)μg/L,春、冬兩季ρ(TAs)平均值較夏、秋兩季高.

圖2 呼倫湖水體ρ(TAs)的空間分布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ρ(TAs) in water of Lake Hulun
圖2顯示了各季節呼倫湖水體中ρ(TAs)的空間分布. 由圖2可見,ρ(TAs)高值區在冬季、春季、夏季、秋季經歷了自呼倫湖沿岸(特別是西北沿岸)逐漸向全湖擴散,之后又逐漸集中在湖心的變化過程,入湖河口處的ρ(TAs)相對湖體較低. 值得注意的是,與其他3個季節不同,冬季水體中的ρ(TAs)呈明顯空間波動,ρ(TAs)高值區集中在西北沿岸,其最高值達到87.3 μg/L,約為其他季節檢出最高值的1.3~1.7倍.ρ(TAs)空間變化可能受到不同時期氣候氣象及河流補給等的共同影響. 冬季冰封對水體中污染物具有濃縮效應[19],因沿岸與湖心水深及冰層厚度的不同,導致岸邊濃縮效應大于湖心,因此沿岸水體ρ(TAs)高于湖心;春季冰融后,湖水在強烈西北風影響下水體交換增強,驅使高ρ(As)區域逐漸由西北沿岸向湖心乃至東南部擴散,特別是夏季又多偏東北風[19],使得整個湖泊夏季ρ(TAs)呈無顯著空間波動的特征;秋季氣溫劇降,受河流補給稀釋及西南高東北低的湖盆地勢影響[20],ρ(TAs)高值區逐漸匯集在湖心及西南部.
2.1.2水體中As的組成
As在水體中能夠以溶解態或被懸浮顆粒物吸附的形式存在;其中,As的生物毒性主要來自其溶解態. 調查發現,呼倫湖水體中的As以溶解態為主,占水體中ρ(TAs)的70.6%~99.8%;ρ(DTAs)與ρ(TAs)相關性達0.973(P<0.01),表明ρ(DTAs)的時空分布與ρ(TAs)較為相似.

圖3 呼倫湖水體不同季節As形態分布Fig.3 Distribution of As species in different seasons in water of Lake Hulun

圖4 呼倫湖表層沉積物w(TAs)的空間分布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w(TAs) in surface sediments of Lake Hulun
基于水體中不同形態As的生物毒性差異,進一步調查了As形態的賦存特征(見圖3). 由圖3可見,As(Ⅴ)是呼倫湖水體中As的主要賦存形態,ρ〔As(Ⅴ)〕范圍在1.9~73.4 μg/L之間,平均值為41.62 μg/L,約占水體中ρ(DTAs)的99.3%±5.9%.ρ〔As(Ⅴ)〕與ρ(TAs)呈顯著正相關(R=0.972,P<0.01),表明二者之間有相似的時空變化趨勢. 與As(Ⅴ)相比,僅有個別點位檢測到As(Ⅲ)的存在,且ρ〔As(Ⅲ)〕(0.27~6.47 μg/L)明顯低于ρ〔As(Ⅴ)〕. 值得注意的是,冬季水體中檢測到的ρ〔As(Ⅲ)〕相對較高〔(1.71±2.08)μg/L〕,這可能歸因于湖泊冰封對表層底泥厭氧環境的促進,使得底泥中與Fe氧化物結合的As(Ⅴ)在厭氧微生物的作用下被還原為As(Ⅲ),并因其相對較弱的吸附性而發生向水體的遷移[21-23]. 另外,夏季呼倫湖水體中還檢測到微量的DMA (0.12 μg/L),可能來自于夏季浮游藻類對無機砷的生物轉化作用. 呼倫湖目前存在水體富營養化的問題[14],夏季迅速繁殖的浮游藻類可通過對無機As進行生物轉化,進而向水體釋放有機代謝產物,其中DMA正是主要代謝產物之一[1,4].
2.2 呼倫湖表層沉積物中As的分布特征
2.2.1w(TAs)的時空分布
這是市第一人民醫院婦產科開具的關于竹韻的婦檢證明。鑒定結果是這樣寫的:處女膜完整,無損缺,亦未發現修補痕跡,被檢查者尚未在過性行為。
呼倫湖表層沉積物中w(TAs)在1.64~15.49 mg/kg之間,平均值為8.76 mg/kg,與張曉晶等[12]調查結果相近. 其中,春季、夏季、秋季、冬季的w(TAs)平均值分別為(8.79±3.90)(9.39±3.95)(8.89±3.33)和(8.25±3.40)mg/kg;冬季w(TAs)相對較低,但各季節w(TAs)無顯著差異(P>0.05).
由圖4可見,各季節表層沉積物中w(TAs)的空間分布相似,均表現為由西北部向東南部遞減的趨勢,該特征主要受湖底細顆粒物分布的影響. 已有研究[24-25]發現,在自然條件影響下,沉積物中絕大多數元素的含量均隨粒徑的變小而升高,除細顆粒物較強的吸附作用外,還歸因于細粒沉積物一般具有氧化還原電位低、有機質含量高的特點,因此造成的氧化-還原環境更易使元素發生富集.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呼倫湖表層沉積物中w(TAs)與黏粒占比及粉粒占比均呈顯著正相關(R=0.802和0.843,P<0.01),而與砂粒占比呈顯著負相關(R=-0.863,P<0.01),證實了表層沉積物中細顆粒物分布對w(TAs)空間變化趨勢的顯著調控作用.
2.2.2As的賦存特征
呼倫湖表層沉積物中w(F1)、w(F2)、w(F3)和w(F4)分別為0.30~7.19、0.66~4.90、0.34~3.95和0.39~2.76 mg/kg,平均值分別為2.95、2.59、1.98和1.32 mg/kg(見表2). 相關分析顯示,w(F1)、w(F2)、w(F3)、w(F4)與w(TAs)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91、0.96、0.92和0.60(P< 0.01),表明各As形態含量,特別是w(F1)、w(F2)、w(F3)均與w(TAs)在空間分布上趨于一致.
從各形態占比來看,w(F1)、w(F2)、w(F3)和w(F4)在w(TAs)中的占比分別為11.0%~56.6%、22.4%~47.1%、12.6%~32.5%和3.4%~37.1%,平均值分別為31.7%、30.0%、21.9%和16.3%. 結果顯示,呼倫湖表層沉積物中的As主要以吸附在金屬礦物、黏粒等表面,或與金屬(氫)氧化物以共沉淀的形式存在,殘渣態占比相對較低.
2.3 呼倫湖As的來源分析

表2 呼倫湖表層沉積物中As化學形態含量及占比Table 2 Content and proportions of As chemical forms in surface sediments of Lake Hulun
研究[26-27]表明:滿洲里-新巴爾虎右旗成礦帶位于呼倫湖西-額爾古納河斷裂帶以西,即呼倫湖北側及西南側,典型礦床為鉛鋅銀及鉬礦床,且多集中于克魯倫河與額爾古納河兩岸;As常以硫化物的形式作為伴生礦存在于上述區域. 底層礦床的風化侵蝕與地熱、水巖交互等自然過程使包括As在內的眾多金屬元素從巖石圈進入地表環境[28-29],這可能為呼倫湖沉積物中的As提供了最初來源;進入地表環境的As可在徑流作用下發生長距離傳輸,并隨著河流向湖泊的輸入逐漸沉積[30],最終在沉積動力環境的影響下形成w(TAs)由湖泊西北部向東南部遞減的分布趨勢. 根據調查結果,3條入湖河流沉積物的w(TAs)平均值呈克魯倫河(9.97 mg/kg)>烏爾遜河及引河濟湖(5.51~5.95 mg/kg)的特征,且克魯倫河沉積物w(TAs)平均值高于呼倫湖,側面證實了成礦帶及河流運輸對湖泊中As累積的顯著影響. 此外,Fe作為一種對人為干擾不敏感的元素,可被用于區分沉積物中金屬元素的自然來源與人為來源[31],而粒度分布與物源及沉積動力環境之間密切相關[32]. 呼倫湖表層沉積物中w(TAs)與w(TFe)呈顯著正相關(R=0.890,P<0.01),同時與細顆粒物占比呈顯著正相關. 綜上,呼倫湖沉積物中的As以自然源為主,其累積與分布可能主要受到自然沉積過程的影響.
根據沉積物As賦存形態的分析結果,F1及F2形態在As中占比較高,并且這兩種形態的穩定性通常相對較低[21],特別是可交換態As由于其鍵合力微弱,對環境條件的改變最為敏感. 因此,沉積物中的As能在一定環境條件下向水體釋放,從而可能成為呼倫湖水體中As的主要內源. 由圖5可見,呼倫湖水體中ρ(DTAs)與沉積物中w(F1)、w(F2)均呈顯著正相關,進一步證實了水體中As的富集受到沉積物中不穩定As形態的影響.

圖5 呼倫湖水體ρ(DTAs)與沉積物w(F1)、w(F2)的相關性Fig.5 Correlations between ρ(DTAs) in water and w(F1) and w(F2) in sediment
2.4 環境因素對水體As分布的影響
2.4.1水體pH
根據已有研究[20]及筆者調查結果,呼倫湖水體的pH在9.0波動,偏堿性的盆地型湖泊有利于湖水中As的富集,這主要來自于大量OH-與沉積物中As的競爭吸附所引起的As解吸[6,8]. 由圖6(a)可見,呼倫湖水體的pH與ρ(TAs)呈顯著正相關,表明呼倫湖pH的升高促進了沉積物中As向水體的釋放.

圖6 水體ρ(TAs)時空變化的環境因素影響Fig.6 Influence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 of ρ(TAs) in water
2.4.2冬季冰封
根據調查結果,冬季呼倫湖水體As分布呈顯著空間波動,高ρ(TAs)水體聚集在西北沿岸,這可能受冬季冰封影響所致. 呼倫湖地處半干旱的高緯度地帶,具有長冰封期的特點[20],湖面冰凍時間約從11月初持續至翌年3月末. 一方面,湖面結冰過程對水體中污染物有一定的濃縮效應[19],使得水體ρ(TAs)顯著高于冰層中ρ(TAs)〔見圖6(b)〕,且湖心與沿岸區域的水深差異使沿岸淺水區域的As濃縮更為強烈;另一方面,冰蓋的形成能阻止大氣與水體的物質交換,而太陽輻射依然可以穿透冰體,在其內部形成良好的“保溫作用”,從而加強沉積物-水界面的厭氧環境[19,33],該環境條件易導致作為黏土礦物重要組成部分的Fe氧化物發生還原溶解[34],使得吸附在Fe氧化物表面或與其共沉淀的As從沉積物中釋放到水體. 上述結果可由呼倫湖冬季水體中ρ(TAs)與ρ(TFe)的顯著正相關性證實〔見圖6(c)〕. 由于呼倫湖沉積物中w(TAs)與w(TFe)呈顯著正相關,表明二者均呈西北部高于東南部的分布特征,加之西北部以富含有機質的細粒沉積物為主,有機質分解過程中耗氧相對較多,更易造成缺氧環境[35]. 因此在冬季冰封期間,西北部沉積物中因Fe氧化物還原溶解帶來的As釋放量可能較其他區域更高,加之沿岸淺水區域污染物濃縮作用增強,導致冬季呈現出西北部沿岸水體中ρ(TAs)明顯升高的特征. 相對而言,其他季節水體ρ(TFe)與ρ(TAs)不存在相關關系(P>0.05).
2.4.3入湖河流
由圖2可見,非冰封期間(春季、夏季、秋季)3條河流入湖口處的ρ(TAs)整體較低,其中春季與夏季烏爾遜河入湖口附近ρ(TAs)變化不明顯,可能是由于受到了西北風造成的水體交換影響. 為探討入湖河流對湖泊ρ(TAs)分布可能造成的影響,進一步調查了河流水體中的ρ(TAs),結果如圖6(d)所示,盡管克魯倫河水體中的ρ(TAs)高于其他兩條河流,但河流中ρ(TAs)平均值均顯著低于湖體(P<0.05). 因此,河流匯入對湖中ρ(TAs)可起到一定的稀釋作用,從而同樣影響著ρ(TAs)在湖水中的分布趨勢,相似的河流稀釋作用在韓知明等[19]對呼倫湖水體磷分布的研究中也有提及.
此外,水體ρ(TAs)的時空變化可能還受到其他眾多環境因素的影響. 如筆者調查結果顯示,春季、夏季、秋季水體ρ(TAs)的空間變異性(10.7%、15.9%、16.4%)均明顯低于冬季(42.7%). 已有研究[19,36]表明,呼倫湖全年多大風天氣,其中以西北風為盛行風向,夏季又多偏東北風;因此風力作用可能是促進春季、夏季、秋季水體擾動而使ρ(TAs)空間波動減小的原因,而冬季形成的冰蓋能有效阻隔風力對水體擾動的影響. 另外,與冬季冰封有利于底泥形成缺氧環境不同,非冰封期風力作用下的水體擾動可為水-沉積物界面提供溶氧補給;有氧環境中游離態As易以重新吸附在金屬氧化物表面等形式沉積在湖底[5],加之入湖河流的稀釋作用,從而可能使得夏季與秋季水體中ρ(TAs)有所降低.
2.5 呼倫湖As的潛在生態風險分析
2.5.1沉積物As潛在風險
該研究參照Singh等[37]提出的重金屬穩定度風險評估標準(risk assessment code, RAC),對沉積物中As的潛在釋放風險進行了評估(見圖7),As的RAC值范圍在11.0%~56.6%之間,約46%的點位沉積物中As處于中等穩定狀態(10% 圖7 呼倫湖表層沉積物中As的 穩定度(RAC值)累積頻率Fig.7 Accumulation frequency of As stability (RAC value) in surface sediments of Lake Hulun 根據張立杰[38]2014年對呼倫湖水體ρ(TAs)的調查結果,7月及9月ρ(TAs)平均值分別為13.39和8.32 μg/L,在世界衛生組織(WHO)規定的飲用水As濃度閾值(10 μg/L)上下波動;而筆者調查中ρ(TAs)平均值為2014年的3.5~5.6倍,表明近5年來呼倫湖水體中ρ(TAs)確實有所上升,該結果可能與近年來內源As釋放及相關自然環境因素的影響有關. 2.5.2水體As潛在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呼倫湖水體的偏堿性條件有利于部分不穩定As從沉積物中釋放,但受呼倫湖水域面積大[14]、入湖河流存在稀釋作用[19],以及湖底氧化/還原條件對As固定/遷移的調控等作用[6],使得目前呼倫湖水體中ρ(TAs)除冬季與春季部分區域外,基本不超過我國GB 3838—2002《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中Ⅲ類標準限值(50 μg/L). 此外,美國環境保護局在《國家推薦的水質基準》[39]中進一步提出了水體中As急性與慢性生物毒性的濃度閾值,分別為150和340 μg/L,均高于呼倫湖水體的ρ(TAs). 特別是從賦存形態來看,As(Ⅴ)是呼倫湖水體中As的主要形態,而As(Ⅴ)的生物毒性通常低于As(Ⅲ)[2-3,40]. 綜上,目前呼倫湖水體中的ρ(TAs)水平可能并不會對湖泊生物群落造成明顯的生態危害,后續應持續關注呼倫湖的ρ(As)變化趨勢,并開展對呼倫湖水體As生物有效性的相關研究,以深入了解As對呼倫湖水生態系統是否存在潛在影響. a) 呼倫湖全湖水體ρ(TAs)在6.6~87.3 μg/L之間,平均值為47.0 μg/L,其中ρ(DTAs)占比為70.6%~99.8%,且As(Ⅴ)在水體中有絕對優勢;不同季節ρ(TAs)平均值呈春季>冬季>夏季>秋季的特征,其中冬季ρ(TAs)高值聚集在沿岸區域,與其他3個季節的空間分布有明顯差異. b) 呼倫湖表層沉積物w(TAs)為1.64~15.49 mg/kg,平均值為8.76 mg/kg,且各季節w(TAs)空間分布一致,呈由西北向東南遞減的趨勢;F1和F2為沉積物中主要的As化學形態,致使沉積物As穩定度較低,這部分As在一定環境條件下易向水體遷移,從而成為水體中As的主要內源. c) 呼倫湖水體pH波動、冬季湖面冰封、入湖河流等自然環境因素均可影響水體中ρ(TAs)的時空分布,其中冰封是造成冬季湖泊西北沿岸區域水體ρ(TAs)顯著升高的主要原因.
3 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