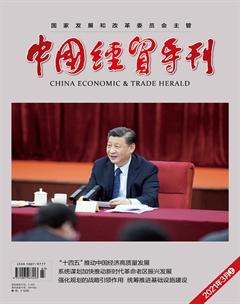克服“四個不同步” 實現“四個聚焦”促進國防實力和經濟實力同步提升
王海成 鄭騰飛 張于喆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國防實力要同經濟實力相匹配”,對“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實現富國和強軍相統一”作出了戰略擘畫。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經濟社會發展到哪一步,國防實力就要跟進到哪一步”。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深刻認識國防實力和經濟實力同步提升的必要性,梳理國防實力與經濟實力之間存在的“不同步”,在更廣范圍、更高層次、更深程度上將國防和軍隊建設融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體系之中,促進國防實力和經濟實力同步提升,構建一體化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對于確保人民軍隊在“十四五”時期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邁出重大步伐”,二〇二七年實現建軍百年奮斗目標具有重意義。
一、深刻認識國防實力和經濟實力同步提升的必要性
(一)國防實力和經濟實力同步是軍事創新實現新跨域的必然要求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由導入期轉為拓展期,致使現代戰爭制勝機理發生深層次變化,戰爭從以信息技術和精確打擊武器為核心的“初智”階段,躍升為以人工智能等技術為支撐的“高智”階段,世界各主要國家紛紛加大科技創新投入,企圖形成新的壓倒性技術優勢,搶占未來戰爭制高點。近代以來,我國曾錯失過科技革命、產業革命、軍事革命的機遇,倘若不能在這些領域占得先機,就會成為受制于人的“阿喀琉斯之踵”。面對世界新軍事革命的嚴峻挑戰,不能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要清醒看到我們在創新,人家也在創新,而且起點高、投入大、走得快,我們必須要加大科技創新力度,夯實能打勝仗的物質技術基礎。當前國防實力的增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依賴于經濟實力,國防建設的經費需求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
(二)國防實力和經濟實力同步,是我國由“富國”到“強國”的必然要求
從現實國情出發,中國是奉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社會主義大國,必須堅持國防實力和經濟實力同步。對于前蘇聯“國強而不富”,不顧經濟發展實際,大搞軍備競賽,最終導致亡黨亡國的歷史教訓我們有著清醒的認識。與此同時,“國富而不強”也絕非中國的可行選擇,國家經濟建設需要強大的國防實力作保證,國防實力不強,必將受到外部勢力的侵略和掠奪,經濟建設的成果就可能毀于一旦,經濟發展可能倒退十幾年、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代表性的案例,如科威特是海灣地區重要的石油輸出國,在世界各地擁有大量資產,但在伊拉克的進攻面前,卻毫無抵抗能力。
(三)國防實力和經濟實力同步,是國際形勢與祖國統一事業的客觀要求
從國際和國內形勢來看,我國面臨的風險挑戰不容忽視,反分裂斗爭形勢將更加嚴峻,“藏獨”“東突”等分裂勢力活動頻繁,國土安全依然面臨威脅,個別域外國家艦機對中國頻繁實施抵近偵察,多次非法闖入中國領海及有關島礁鄰近海空域,海外利益面臨國際和地區動蕩、恐怖主義、海盜活動等現實威脅。如果我國沒有強大的國防實力作為后盾,我國的國家利益、民族尊嚴和國際威望就會受到嚴重損害,我們必須要有危機感、使命感,努力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努力建設強大的國防。在抓好經濟建設的大前提下,注重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逐步增加對國防建設的投入,加大國防建設的力度,使國防和軍隊建設同國家的經濟實力相適應。
二、國防實力和經濟實力之間存在“四個不同步”
(一)經濟體量與國防建設支出規模不同步
從軍費支出規模看,2019年美國軍費支出7320億美元,占世界軍費總量的38%,而我國軍費支出為2610億美元,只有美國的36%。從軍費支出占比看,2019年全球軍事開支占全球GDP為2.2%,而我國軍費占GDP比僅1.2%,不及全球平均水平,并且遠低于美國(3.1%)、俄羅斯(4.6%)、韓國(2.4%)等主要國家的水平。在人均國防支出方面,美國是絕對的世界第一,2000—2019年累計人均投入38486美元,我國為1230美元。從軍費支出增速看,2019年美國GDP增速是2.3%,軍費支出增速則高達5.3%,而我國GDP增速是6.1%,軍費支出增速是7.5%。
(二)技術供給能力與提升新型作戰能力的要求不同步
目前,我國科技創新處于從量的積累向質的飛躍、點的突破向系統能力提升的關鍵階段。但是,我國技術供給能力與新型作戰能力的要求仍有一定差距,不利于戰斗力生成模式的轉變。裝備研發總體上水平不高,在軍工關鍵材料、關鍵元器件、動力技術等方面還存在“瓶頸”。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發展并不足,不適應科技持續和跨越發展的要求。長期以來,科技工作主要跟隨型號研制需要,在基礎性科研和關鍵技術的超前發展方面投入有限,導致知識積累與技術儲備不足,缺乏不少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
(三)國防工業生產能力與提升武器裝備現代化水平的要求不同步
國防科技工業作為國家戰略性產業,是國家安全和國防建設的脊梁,既屬于國防建設的范疇,又屬于經濟建設的領域,是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同步發展的天然載體和最重要領域。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國防科技工業適應國際形勢復雜多變和軍事技術飛速發展的需要,建立了專業門類齊全和科研、試驗、生產、服務手段基本配套的國防科技工業體系,為我國國防科學技術和武器裝備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和技術基礎。同時也要看到,國防科技工業一些深層次矛盾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老舊產品能力過剩,在海洋、太空、網絡空間、生物、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大量關鍵整機、核心技術、關鍵配套系統和高端產品存在明顯的供給不足,體系相對封閉,專業化配套不足,現代工藝手段不同步等矛盾仍比較突出。
(四)龐大基礎設施建設規模與國防功能搭載需求不同步
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加快轉型、城鎮化加速推進的關鍵時期,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很大,我國鐵路、公路、港口、機場、通信、電力、能源等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成就。我國在基礎設施建設中搭載國防功能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在建設、協調和管理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一是軍民通用標準體系通用程度低,部分鐵路、公路、橋梁、港口碼頭等大型基礎設施難以滿足部隊重型裝備的運輸、裝卸需求。二是重大基礎設施重復建設,例如,一些城市在當地已有軍用機場,適當改造即可實現軍民兩用的情況下,卻堅持上馬民用機場,由于支線機場航空運輸需求少、自身運營無法支撐機場運行而處于虧損狀態。這既導致資源閑置浪費,又干擾了軍用飛機飛行,影響部隊戰備訓練。
三、“十四五”時期要建立支撐國防建設的四大體系
“十四五”時期減稅降費將深入推進,雖然從中長期看有助于涵養稅源、增加財政收入,但短期財政收入大概率會低位運行,而財政支出仍將保持較快增長,加之兜住“保工資、保運轉、保基本民生”底線等各項剛性支出持續加大,財政收支平衡壓力加大。因此,要加快建立對國防建設的支撐體系,實現軍民兩大需求統合、資源聚合、能力融合,將各種相互關聯的軍民力量和資源集成為軍民一體、活力倍增的國家總體對抗博弈能力,實現國防實力和經濟實力的同步提升。
(一)聚焦增量提質,建立支撐國防建設的軍費保障體系
一是適度提升軍費開支規模,參考潛在可比國家的軍費與GDP關系,考慮到15年后中國的國際地位,逐步提升我國軍費開支水平,在參照國際經驗的基礎上,要彌補“忍耐期”缺口,要與新軍事變革相適應,盡快滿足“軍事快速發展”的要求,才能使得我國的軍事建設在新軍事變革的浪潮中不落伍。二是提升支持方向的精準性,切實把軍費開支分配到戰斗力貢獻度高的方向,加大向新型作戰力量的傾斜力度,盡快構建以需求為牽引、以規劃為主導的軍費配置運行機制,打通“需求—規劃—預算—執行—評估”的完整鏈路。三是提高軍費使用效益效率,要強化經費使用管理監督,嚴格按照戰斗力標準花錢辦事,確保每一分錢都花到提升戰斗力的刀刃上。
(二)聚焦協同共享,建立支撐國防建設的科技保障體系
一是聚焦戰略性、帶動性、全局性的關鍵共性基礎技術,人工智能、網絡信息等前沿、顛覆性技術,以及軍用動力、關鍵材料、核心元器件等瓶頸短板問題,大力實施產業基礎能力再造,促進軍民科技相互支撐和轉化,建立國防科技協同創新體系。二是推動軍民技術雙向流動,健全國防知識產權制度,實質性推進軍工技術解密,鼓勵軍工以多種方式推進軍工高技術向民用領域轉移,鼓勵軍工采用先進適用的民用技術。三是制定國防科技資源開放共享管理辦法,推進國防科技重點實驗室、軍工重大試驗設施等向社會開放服務,加強新建實驗室和重大試驗設施的軍民統籌,以國家重大科技專項為平臺,促進軍民技術融合和軍地創新合作。
(三)聚焦融合開放,建立支撐國防建設的產業保障體系
一是要積極發展核能、航天、航空等典型產業,調整優化船舶產業結構,大力發展應急安全、反恐維穩、海警邊防、城市安防、衛星應用等裝備,推動軍工為國家“大安全、大防務”服務。二是推動軍工開放,加快實施軍品科研生產能力結構調整,除涉及國家安全的戰略武器和核心領域外,充分吸納社會優質資源進入武器裝備科研生產和維修領域,擴大軍工企業外部協作,推進軍品科研生產有序競爭,推動軍工集團不斷提高外部配套率和民口配套率。三是統籌謀劃國防工業布局與定位,優化軍工能力布局,鼓勵軍工與地方加強戰略合作,落地一批重大項目,形成具有特色的國防工業基地。
(四)聚焦兼容共用,建立支撐國防建設的基礎設施保障體系
一是滿足特殊需要,在重大基礎設施的設計和建設過程中,要充分考慮軍事裝備特殊要求,公路、鐵路、機場、港口、碼頭、橋梁、隧道和航道等建設,要兼顧大型軍事裝備的載重、通行需要等。二是拓展作戰功能,新建、改建、擴建、遷建基礎設施,在滿足民用的同時,應當充分考慮軍事需求,采取工程技術措施,拓展作戰功能,如鐵路隧道建設要完善軍事運輸裝卸設施功能,公路建設要考慮軍用飛機的起降要求,港口碼頭建設要考慮軍用艦艇停靠的要求,電力和能源、水利設施建設也要考慮未來作戰的資源保障需求。三是預留軍事接口,在組織寬帶網、移動通訊網絡、地理數據庫等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中,在確保保密的前提下,應盡量軍民合用或預留軍用接口,以便安裝軍事裝備,鐵路機車、載重汽車、民用船舶、民用飛行器等大型交通運輸工具的建造中,要充分考慮戰時加裝改造的需要,必要時加裝海上通信、衛星定位、防護偽裝等裝備,以便能快速動員,征召使用。
(王海成,國家發展改革委產業所經濟學博士、助理研究員。鄭騰飛,國家發展改革委產業所經濟學博士、助理研究員。張于喆,國家發展改革委產業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