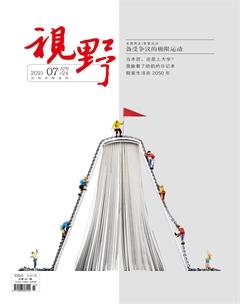我終于又讀書了
時瀟含

近來像有一個晃動不止的鐘擺,在我四壁空空的心中擺動。這種無止境的震動讓我既讀不下去書,也提不起筆,打開手機反反復復翻通訊錄,反倒惱了將手機丟到一邊。后來猛然看到加繆的一句話,忽然明白了我心中伴隨著心安理得的焦灼:我原本想成為一個哲學家,但是常常被心底浮現的喜悅打斷。
大約看到大把大把的時光自由地在我的默許下變成一張又一張的電影票根,手機上眼見的一格一格消減的電量,也是一件使人快樂的事吧,畢竟能自由揮霍的東西,不見得一天比一天多。
大約《海邊的卡夫卡》是一個和自由與反抗有關的故事吧。那些被詩人殺死在筆尖的自由,就猶如卡夫卡最終選擇回到他的世界,而非一往無前奔向莫可名狀的自由,與其說是醒悟救贖,或是對曾經的背棄,不如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回歸,由他流亡式的自省之路,由他故作堅強式的獨行。他渴望逃離他厭惡的親人,毫無眷戀的生活,擺脫他父親預言的與俄狄浦斯相似的命運,然而在他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打開的大門,在世界的邊緣徘徊的時候,他卻說后悔了。他卻心甘情愿回到他所厭惡的生活了。這讓我想起《麥田里的守望者》,這些拒絕讓寒冬熄滅夏天的少年們,最終說出了:你千萬別跟任何人談任何事,你只要一談起,就會想念起每一個人來。
日語書的措辭常常很有意思,讀來常常有些別扭。但將田村卡夫卡稱作少年,并解釋要寫一個少年的故事是因為少年是可變的時候,無法否認,我被這兩個字撞了一下。換一個矯情的說法,這些寫在水上的句子,宛若巨斧,鑿開了我心中的冰河。我忘了這句話是誰說的了,反正我確信,在我荒蕪的大腦里竄出來的,一定是遠方的燈火。之所以要寫一個少年,是因為他可變,這句對我來說還是預言的話,著實是我一直以來最恐懼的。那么,不是少年的人呢?大島說:“寶貴的機會和可能性,無法挽回的感情,這是生存的一個意義。但我們的腦袋里——我想應該是腦袋里——有一個將這些作為記憶保存下來的小房間,肯定是類似圖書館書架的房間。而我們?yōu)榱私庾约旱男牡恼_狀態(tài),必須不斷制作那個房間用的檢索卡,也需要清掃、換空氣、給花瓶換水。換言之,你勢必永遠活在你自身的圖書館里。”由此又想起了芥川龍之介對衰老的恐懼,甚至說是厭惡。難道與可以揮霍的時光一起消失的,是勇氣嗎?
我有時會想起和朋友們約好了要怎樣走遍世界。漸漸碾成了粉末,漸漸變成了自知永遠不會完成的發(fā)黃的愿望清單。怎樣變成了有假期也會欲言又止,怎樣變成了永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漸漸變成即使我們依舊樂此不疲彼此問著,什么時候有空見面,并笑嘻嘻地計劃把兩張愿望清單變成一張,但是不同的是,我們說這些的時候,已經知道我們恐怕不會出發(fā)了。
有的時候,對著發(fā)光的屏幕嬉笑打鬧過后,或是打出滿屏的宏圖壯志、盛世煙火之后,坐在桌子前,短暫的空白之中,我覺得這一次我又做錯了事,然而,被十八年間無數次的失敗支持著,我什么也不怕,屹然坐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