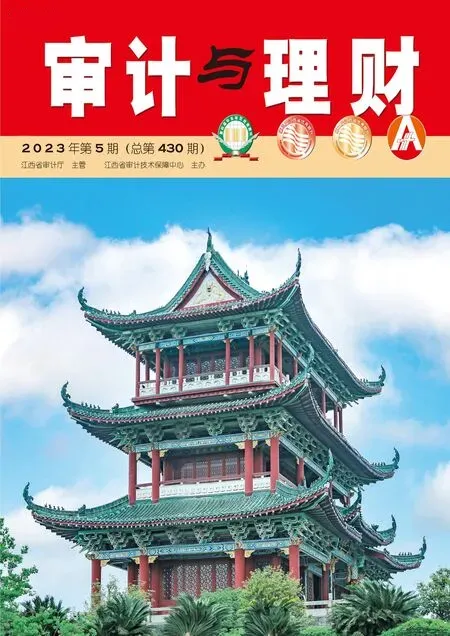小額貸款公司信貸風險防控探析
■唐麗香

一、小額貸款公司信貸風險的特征
1.客觀性
小額貸款公司的客戶會經常產生不按照合同約定償還貸款的現象,這就會給公司帶來較大的催收壓力,部分客戶甚至會形成違約事實。換句話說,只要有信貸活動存在,信貸風險就隨之存在,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小額貸款公司只能積極地采取科學合理的措施來預防信貸風險,嚴格把控信貸流程,將信貸風險帶來的損失降到最低。
2.不確定性
引發小額貸款公司信貸風險的因素有很多,有客戶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環境變化、以及意外事項的發生。小額貸款公司在事前并不能知曉信貸風險發生的時間與發生的概率,發生信貸風險與小額貸款公司是否事前識別風險、設置動態監控風險預警系統有直接的關系。
3.復雜性
造成小額貸款公司出現信貸風險的因素有很多,具體包括:法規法律的保障程度、內外部市場環境、借貸用戶實際信用情況等,如果小額貸款公司不能有效地防范以上任意一個風險,可能就會引發不必要的信貸風險。
4.可控性
信貸風險的變化和種類是有獨特特性的,因此小額貸款公司可以采用專業的技術與嚴格的內控體系,對風險進行事前識別與預測、事中監控與防范、事后化解,將信貸風險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之內,減少不必要的經濟損失。
二、小額貸款公司信貸風險防控程序
1.識別信貸風險
小額貸款公司需要全面分析貸款人的實際情況,具體包括:歷史沿革、股東構成、經營情況、信用情況、行業情況、實際控制人的家庭與愛好、健康狀況等,對信貸風險產生的原因、來源、性質等情況進行分類,判斷信貸風險造成的負面影響程度。
2.分析信用風險
小額貸款公司在對信貸風險點進行識別之后,采用統計分析、財務分析等分析方法來對信貸風險進行驗證,定性定量地對財務指標、項目收益預測、其他風險因素進行綜合分析,及時提出信貸風險防控措施。如果小額貸款公司不能準確地分析信貸風險,容易選擇信用不良的客戶,加大壞賬損失發生的概率。
3.評估信用風險
小額貸款公司中的貸款審批人員結合識別與分析信貸風險的結果,對客戶資料進行深入地審查,最終提交貸款審批意見。審查客戶資料的信息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是對客戶經理出具的盡職調查報告中的風險識別點進行判別,主要判斷是否還存在未識別出的較大信貸風險;第二是對信貸風險控制人員是否錯誤地進行信貸風險分析進行判別,以及是否要對信貸風險進行補充;第三,判別信貸風險控制人員提出的風險防控措施是否可行,并對防控措施進行補充。
4.信貸風險決策
小額貸款公司結合主要的信貸風險分析、防控措施、關鍵點等情況,決定是否向客戶發放貸款,并從多個角度來制定這筆貸款的信貸風險防控方案,保證信貸風險防控方案的科學性、合理性。
5.貸后管理
小額貸款公司需要不定期或定期地對放貸客戶進行監管和跟蹤檢查,密切關注影響貸款人償債水平的各種因素,其中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幾個:股東變動、高管變動、行業情況、經營情況、財務情況、資金狀況、司法訴訟情況、抵押物價值等。信貸風險會隨著市場經濟環境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因此雖然貸前調查貸款項目良好,但是在貸后很可能出現償債能力變差的風險,需要通過貸后管理來發現信貸風險,有前瞻性地加大信貸退出力度,才能有效防止信貸資產質量惡化。
6.責任追究
小額貸款公司在考核信貸風險過程中,如果發現問題就要開展責任追究程序。特別是對操作風險易發生環節的設計與處理,如有人為因素導致的問題,應采取相應的處罰措施,創造良好的執業環境,真正實現對操作風險和道德風險的有效防控。
7.制度建設與執行
小額貸款公司需要檢查審貸制度、流程是否完善,以及是否得到有效地執行,使得風險管控有章可循,制度得到真正落實。
三、小額貸款公司加強信貸風險防控的幾點措施
1.風險管理前移,從客戶選擇即開始進行風險管理,小額貸款公司需建立完善的客戶信用評級制度
客戶信用評級是指金融企業為有效控制客戶的信用風險,實現信貸資金的安全性、流動性和收益性,從客戶經營能力、盈利能力、償債能力、發展能力,以及客戶素質和信用狀況等方面,對客戶進行綜合評價與信用等級的劃分。小額貸款公司因其天生的屬性,其客戶群體資質不如銀行。因此,客戶信用評級工作對于小額貸款公司來說,尤為重要。小額貸款公司可從客戶的行業信息、區域信息、財務信用、信用信息、司法信息、基本面等方面建立一套完善的客戶信用評級制度。根據客戶等級給予不同的業務品類與授信額度。另外,隨著外部經濟環境的不斷變化,以及小額信貸公司的業務變化情況,需定期對客戶信用評級制度進行更新與修訂。
此外,公司可以利用累計的客戶信息,對優質客戶進行合理的激勵,增加客戶粘度。小額貸款公司要針對不同的業務建立客戶信用檔案,并根據客戶的還貸情況,對客戶制定科學合理的激勵或處罰措施。例如貸款客戶能夠及時地償還每筆貸款,甚至能夠提前償還貸款,小額貸款公司就可以在客戶再次提交貸款申請的時候,給予一定的貸款優惠條件,這是對客戶按期足額償還貸款的激勵,也是穩定客戶的一種方法。
2.做好貸前調查工作
在對客戶進行信用評級后,需對客戶進行實地盡職調查,全面了解客戶的整體實力。具體來說要對客戶所處的企業生命周期、股東構成、管理團隊、行業狀況、上下游關系與合作模式、財務狀況、資金狀況、資產實力、高度關聯企業情況、銀行征信情況、司法訴訟情況等,判斷客戶真實的貸款用途與還款能力。在與客戶進行業務交流的過程中,小額貸款公司可以向客戶提示違約的后果,培養客戶認真履行貸款合約的觀念。此外,從風險隔離的角度出發,貸前調查工作應采取雙人雙崗、以及定期更換盡調人員的原則,避免工作人員發生道德風險。
3.構建信貸風險的預警機制
小額貸款公司在運營中存在著諸多的風險,如果不加以控制,就可能成為困擾小額貸款公司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因此建立一套科學系統的小額貸款風險預警體系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將動態監控風險預警工作具體落實到一個獨立于信貸業務部門的職能部門,以保證貸款風險評估的客觀性、科學性、時效性。貸款風險定期評估是監測貸款風險度的一項具體工作,需要獨立、科學、客觀地對每一筆貸款生命周期中的風險狀況做出量化評估,達到一定風險水平的貸款,就需要有關部門及時采取措施化解、轉移風險。此外,設立專門的信貸風險管理機構也是為了防范信貸圈里的過分集中,利用機構的相對獨立性在信貸權力分配中建立起“防火墻”。但為了保證信息的流動性,保證各部門都能充分共享借款人的資信信息,還應該建立信息在有關部門流動的制度,防止畫地為牢、公共信息被一個部門私自占有的情況發生。其次,搭建科學合理的風險預警機制。風險預警機制主要是通過貸后檢查的方式,發現信貸風險的早期預警信號,運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盡早識別風險的原因類別、程度以及發展變化趨勢,以對發現的風險采取針對性的處理措施,及時防范、控制和化解風險。因此,風險預警機制涵蓋的主要內容有:貸后風險檢查、風險五級分類、風險控制措施等。信貸風險管理機構需定期通過電話回訪、走訪貸款客戶、查閱貸款客戶相關資料等貸后檢查方式,形成調查結果,并根據結果即時調整客戶風險五級分類等級。真實發揮風險預警機制的作用,使信貸風險得到有效防控。
4.提高信貸人員的素質水平
一部分小額貸款公司的信貸風險系由于信貸人員的不當操作所導致,因此小額貸款公司需要提高信貸人員的專業技能水平。首先,小額貸款公司的管理者要重視對信貸人員的業務培訓,定期聘請專業的信貸人員來進行授課,及時更新信貸人員的知識儲備、業務技能,讓信貸人員能夠靈活處理日常信貸業務,提升防控信用風險的能力。其次,小額信貸公司的管理者要加強對信貸人員的職業道德素質教育,樹立愛崗敬業、誠實守信的職業精神,避免徇私舞弊行為的發生。
最后,小額貸款公司的管理者要通過宣傳教育的方式,樹立信貸人員的信貸風險觀念,讓信貸人員認識到信貸風險的危害,這樣信貸人員才能夠積極地參與到防控信貸風險的工作中去。
四、總結
綜上所述,信貸風險作為小額貸款公司的固有風險,如果對其控制不當可能會嚴重影響到小額貸款公司的生存。因此小額貸款公司需要結合信貸風險的特點,積極地采取科學合理的措施來提高小額貸款公司信貸風險的防控能力,從而實現小額貸款公司健康、可持續地發展,為中小微企業的發展提供資金支持,為地方區域經濟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