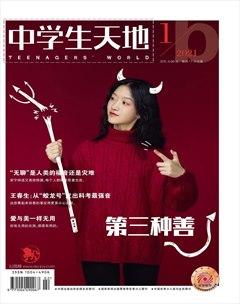快與慢
岑嶸


挪威有家電視臺,叫作挪威公共廣播電視臺(NRK),這家電視臺不走尋常路,制作了一些我們無法想象的電視節(jié)目。比如花18個小時直播釣魚,直到第3個小時才有一條三文魚上鉤;花8個小時展示單調的織毛衣全過程,連畫面里的織毛衣主婦都難掩睡意;花8個小時把鏡頭對準噼里啪啦燃燒的柴火,觀眾戲稱如果把電視機嵌在壁爐里就可以亂真了。
制作者將這些節(jié)目稱為“慢電視”。
那么這些超級無聊的“慢電視”有人看嗎?答案是有,且非常火爆。
比如NRK直播從奧斯陸到卑爾根的7小時火車之旅,沒有剪輯和制作,整個過程一秒不漏,結果觀眾達到120萬人,要知道整個挪威的總人口也不過530多萬,受歡迎程度堪比中國春晚。更夸張的一次是直播沿挪威海岸線的游輪之旅,整整“素顏”直播了五天六晚,結果有320萬挪威人收看了節(jié)目,可謂萬人空巷。
為什么這么無聊的節(jié)目如此受歡迎?
如果我們審視今天所處的世界,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原因,那就是“快”。
這個世界越來越快。我小時候坐的綠皮火車時速大約為100千米,今天的高鐵時速可達300多千米,而正在研制的超級列車時速更是將達到上千千米。
拿流行音樂來說,節(jié)奏正變得越來越快,歌曲前半部分較為舒緩的傳統(tǒng)習慣被舍棄了。因為現(xiàn)代人使用手機等電子設備聽歌時會變得越來越不耐煩,幾秒鐘后就會輕易跳到下一首。
哪怕我們走路的步伐也是如此。在20世紀90年代初,有個心理學家叫羅伯特·萊文,他和他的學生歷時3年,前往31座不同的城市,測量了行人的行走速度。他發(fā)現(xiàn)一個國家經濟越發(fā)達,工業(yè)化程度越高,步行的速度也越快。到了2006年,一位來自英國的心理學家理查德·懷斯曼重復了萊文的實驗,結果他發(fā)現(xiàn)同一段路程人們所花的時間又減少了10%。
心理學家斯蒂芬妮·布朗這樣描述眼下的世界:“忙亂的生活方式已經成為人們的一種嗜好,人們像瘋了一樣爭取做更多的事,努力保持在線,隨時待命,對新任務照單全收。”
既然世界如此之快,那么慢又有何意義呢?
人腦并不是超級計算機,在職場上我們看似超人,一刻不停地接受新信息,完成新任務,手頭同時處理多個任務,但這會讓我們的大腦很快耗盡供給神經能量的葡萄糖,隨后我們就會效率低下,注意力分散。
我們通過手機時刻了解世界各地發(fā)生的新聞,但這也讓我們的知識處于碎片化的狀態(tài),沒有人愿意靜下來閱讀經典原著,信息爆炸限制了我們進行深度思考和廣泛思考的能力。
快還讓我們變得越來越不耐煩。當一個網頁4秒鐘還不能打開,我們就會去點其他網頁,這個等待時間在1999年是8秒;人們對任何一種煩心事,比如排隊或塞車,產生的憤怒情緒或挫敗情緒,在過去的20年里猛增。
這個時候我們需要什么?慢下來。
當我們放松下來,讓思緒隨意游走,大腦會產生阿爾法波,這會提高我們的創(chuàng)造力。當我們躺在浴缸里或者沙灘上,說不定靈感就像阿基米德發(fā)現(xiàn)浮力一樣隨之而來。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有本書叫《思考,快與慢》,他說人的大腦中同時存在2種系統(tǒng):快速本能反應的快系統(tǒng)和深度思考的慢系統(tǒng)。人類在長久的進化中形成這2種系統(tǒng),快和慢在不同的情境同樣扮演重要的角色。
人的大腦是如此,整個社會也是如此,快和慢是統(tǒng)一的,并非彼此對立。我們既需要引擎,也需要制動。社會的特征就是飛速向前,而這個時候,還能慢下來就顯得尤其可貴。單一的快或者單一的慢都不能讓我們通往幸福之路。
慢是現(xiàn)代病的解藥,競爭和高速的背后往往是壓力和焦慮。緩解我們焦慮的“無聊經濟”也應運而生,NRK的“慢電視”受歡迎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越來越需要能讓我們喘口氣的產品。例如,曾經有一款名為“青蛙旅行”的佛系游戲風靡全球,游戲的內容是長時間地等待一只出門旅行的青蛙。再比如,我就喜歡聽各種下雨、流水和海浪的白噪音音頻,這個時候我什么都不需要去想,只是靜靜地聽著這些聲音發(fā)會兒呆。
正如NRK的“慢電視”制作人所說:“安寧閑適又高效快捷,每個人都需要雙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