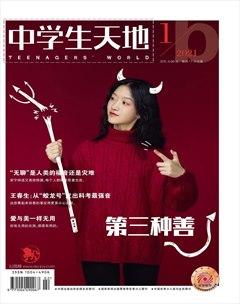第三種善


如果我們把善分成三種形式。
第一種是大的善。
如果問最善良的人是誰,或許你會想到每年2月出現在中央電視臺“感動中國”頒獎典禮上的“感動中國人物”,又或許會想到解救眾生、嫉惡如仇的英雄。因為他們做了常人難以做到的事,他們或者改變了一個人、一個社會,或者改變了整個世界。
第二種是小的善。
從小我們就被教導“勿以善小而不為”,所以小的善早已匯聚成流,淌過我們成長的每個角落。我們也常常用行動,向身邊熟悉的人、陌生的人伸出援手,傳達小小的善意。
而第三種善是什么呢?
有時候,善不一定要急著用行動去證明,用言語去表達。知止而后能善,當你不進行某些舉動,無形之中其實就在傳遞善。
月考剛結束,各科成績出來后,班主任便將年級排名告知了家長,幾乎所有同學都已經跟家長通了電話。不是同學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的排名,就是家長急切地想讓孩子知道自己的排名。可是我的家長與眾不同,我母親不太愿意告訴我排名,主要原因是怕我壓力太大(考得好壓力大)。我考試容易緊張,所以她就擔心我知道自己的排名后,下次會因為擔心考不到這個名次更緊張。
可是我的三個室友知道我發揮得不錯,十分好奇我的年級排名,她們似乎在期待著一個年級第一的誕生。于是,她們非常“樂于助人”地幫我給母親撥通了電話。在室友瘋狂地使眼色下,我無可奈何又不太堅定地問了排名。果不其然,母親大人在給我灌輸好長時間的雞湯后,才不情愿地說出了排名。
最終,這件事就這樣在三個人的滿足和兩個人的尷尬中結束。我知道了自己的排名,可我真的沒有她們以為的那么開心。
張雨澄:我的媽媽總愛在我身上“換位思考”。她總說:“如果我是你,我會做出什么選擇。”幾乎每一次我沒有按照她的意愿來做的選擇都會被打擊。可在我看來,“每個人都只活了一次,都在做判斷題”。我們都不是預言家,換位思考,替別人做選擇,并不一定真的能幫到別人。
阿離:我的外公外婆在農村住了大半輩子。他們的子女,也就是我的母親和舅舅,因為自己的生活富足了,就想把他們接到城里來住,但外公外婆在城里待不住,想回農村。在我母親和舅舅看來,老人家太固執了,不懂得享受生活。城里多好哇,交通方便,想買什么都能買到。可外公外婆被接過來之后,我明顯感到他們的情緒一直都不高,時不時在餐桌上念叨起菜園里種的蔬菜、來家門口找食物的大黃狗。城市生活對他們而言太不習慣了,不能勞作,沒有泥土為伴,整天除了吃飯睡覺只剩下無所事事。他們就連身體都產生了不適,失眠、頭暈、便秘等問題接連出現。母親自覺接他們來城里是一件好事,給了他們更好的生活條件,但也許農村才是最適合他們的幸福家園。
“別打擾她”
講述人:蒙舒羽
高中宿舍是12人一間,雖然平時大家嘻嘻哈哈地像一家人一樣相處,但難免也會有靜默的時刻。
有一次我一個人在宿舍,門突然被打開了,緊接著是請假了兩天、隱忍抽泣著的室友跌跌撞撞地走進來。室友回到自己床上后終于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我被她嚇到了,猶豫著要不要上前安慰,詢問她怎么了。恰巧另一個室友回來了,她見狀也愣了一下,便輕手輕腳地關上門,然后就靜靜地坐回位子上。我走過去低聲問她要怎么辦,她說先別打擾,讓哭泣的室友徹底發泄了再說。之后有人陸陸續續回來,她們想過去安慰哭泣的室友,都被我們阻止了,我們就只是幫忙解釋哭泣的室友心情不太好,先別打擾。大約過了半小時,哭泣的室友才慢慢冷靜下來,之后整整兩天她都沒在宿舍說一句話。
兩天過后,那個哭泣的室友向我們道謝,我們的“不打擾”給了她一個安靜的環境發泄自己的情緒。她悄悄告訴我們,父親的突然離世讓她悲痛萬分,但在家里又不敢表現得太悲傷,所以只能回到學校痛哭一場。
“別打擾她”,成了我們三人之間的小秘密。
明政宇:初中的時候,我有一個性格內向的朋友,他很少參加集體活動,稱得上是沉默寡言。我一直覺得同學間多互動、多交流是很有必要的,于是在某個夏夜,我和幾個同學約好打球,便決定把他帶上。他本是不愿去的,卻耐不住我半強迫、半懇求,終于和我一起出了門。他并不太懂籃球,在場上常常用出“天龍八步”的招數,投籃、傳球更是不在行。他幾次想下場,我都安慰他“沒事的”,要他繼續打。最后他摔倒了,明明是激烈的體育運動,他卻穿著一雙涼鞋。他的腳踝腫了一個包,我看到他的臉因為害羞而通紅,他執意自己站起來,不讓人扶。我想送他回去,他搖了搖頭,一瘸一拐地走了。我看著夜幕中逐漸遠去的瘦削的背影,內心充滿酸澀和自責:是我強迫地拉他來打球,雖然我的本意是讓他更開心,可讓他受傷的卻是我啊!真正的體貼應當如同春雨般潤物細無聲,而不是激烈得好似夏日的太陽,給予太多的熱和光,反而傷了他人。
田舒童:阿姨因為眼睛突然出血,已經在醫院躺了快一個月,一到周末,媽媽便帶著我去看她。在超市買水果的間隙,媽媽打了個電話:“我們等會兒就過來!”電話那頭阿姨的聲音剛結束,就聽見一個男聲:“又來了啊?你剛睡醒再躺會,我去買點水果。”一時我突然不知道頻繁地去看阿姨是不是一件好事……
別做評頭論足者
講述人:傅芷祎
我有一個成績很優異的表哥,在一所很好的大學讀博。但是逢年過節親戚們聚在一起時,總會有人提出質疑。因為他的同齡人或是找到了工作,或是已經結婚,一些長輩覺得這樣把青春耗在讀書上不值得。
或許他們是出于好意在給表哥建議,可我在表哥臉上看到的是局促不安,在表哥父母臉上看到的更是五味雜陳的表情,一邊還得打著圓場說:“隨他自己選擇吧。”
這樣的事情時有發生。當我們做出一個選擇時,總是能聽到各種各樣的聲音。一些評論來自并不了解事情真相的人,常常會帶著偏見,讓人感到不適。而我們有些時候也會成為評頭論足者中的一員,隨口說出一句話或者在鍵盤上敲擊一行字的時候,并沒有考慮到別人的感受。
這些評論帶來的傷害看起來微乎其微,但真是這樣嗎?當案件中的受害者被貼上“受害者有罪”的標簽時,當抑郁癥患者被各種各樣的所謂“建議”包圍時,他們受到的也許是更多的傷害。默默的支持、尊重和理解是取代評判更好的方式。
祝文麗:那天正是中秋,是闔家團圓的日子。我穿著我最喜歡的漢服上街了,一路上很多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我有些欣喜。但是,當我習慣了這種氛圍時,一個阿姨突然瞥了我一眼,不屑地說:“現在的小姑娘啊,一天天的不務正業,穿著奇裝異服,以為自己是誰呢!”我愣住了,頭一次聽到陌生人這樣的批評,我有些不知所措,最終像做錯事一般逃走了。現在想想,我當時或許應該好好給那位阿姨普及一下漢服。作為學生,我能力不足,無法改變人們對漢服的看法,但我想哪怕不愛,也請別傷害。小女子小麗,這廂有禮了。
陌生的食客
講述人:侯雨葳
媽媽開了一家燒烤小店,雞翅五元兩個,雞腿六元一個,而四只大蝦穿成一串則要二十元。
一天傍晚,一位婦女帶著一個七八歲的男孩走進小店,兩人的穿著都很樸素。那個小男孩跑到燒烤架旁,嚷嚷著要吃烤大蝦,當問清價格后,婦女猶豫著又退了回去。
婦女對小男孩說:“明明乖,太貴了。等明天你爸爸回來,咱買肉包餃子吃。”這時,我看到媽媽麻利地挑了兩個雞腿和一串烤蝦,徑直走到那對將要離開的母子跟前。
媽媽熱情地撫摸了一下小男孩的頭,笑著說:“好長時間不見,明明都長這么高了。來,拿著,阿姨送給你的,嘗嘗好不好吃。”
在和那一臉驚訝的母子道別后,我問媽媽:“你認識他們?”
媽媽笑了笑,回我說:“不認識。”
汪帆:某天自習課上我絞盡腦汁地想一道數學題,很久都沒有想出個所以然來,就打算放松一下,抬起頭環顧四周,哦,大家都在認真地學習。正打算繼續寫題時,我突然聽到一陣細碎的聲音,像是塑料袋的聲音,不會是有人偷偷吃零食吧?所謂“人類的本質就是看熱鬧”,我抬起頭,卻看見隔壁座位上同學的衛生巾孤零零地掉在了地上。十三四歲是對性懵懵懂懂的年紀,總是會對這些產生害羞的情緒。她還沒發現,我想了想,假裝不經意地把草稿紙滑落到了她的位子那邊。她聽到了,又是一陣窸窸窣窣的聲音,她滿臉通紅地把草稿紙遞給我,我謝過她,繼續低頭做題。整個教室安安靜靜的,沒有人看到這個小插曲,我也“沒看到”。
屠嘉怡:因為家長比較忙,所以他們在暑假給我報了一個全天上課的培訓班,“同學”中有一個才讀三年級的小朋友。和我一起上課的大多是同齡人,我們上課時,那個小朋友就拿上繪本或者作業在邊上安靜自習,顯得有些孤零零。她兩手端放在桌上,小身板挺得筆直,一直坐到輪到她上課為止。我有一次忍不住逗她,問她為什么坐這么端正,是不是害怕被老師批評。她看著我,小聲卻認真地說:“老師一整天都站著很累的,我能坐著就已經比老師舒服很多了。”我一時吃驚于這孩子的懂事與成熟,小小年紀能這樣克制自己,又何嘗不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善意呢?
怪兔子:夏夜,昏黃的燈光下,我正寫著作業,視線里突然飛進來一只小飛蛾,我下意識拿起橡皮就朝它扔去。橡皮離手的一瞬間,我的世界仿佛靜止了。為什么要拿起橡皮?我為什么想弄死這只飛蛾?它傷害到我什么了嗎?心里后知后覺地涌入了后悔、迷茫甚至感覺自己可怕的復雜情緒。那幾秒是最難挨的時間,我抬起的手忘了放下,我的眼睛緊緊盯著橡皮飛去的路線。幸好,幸好,我扔得不準,砸到了墻壁上,橡皮被彈了回來,我提起的心也重新落了回去。
汪汪:初中班里有一個男生個子不太高,瘦瘦弱弱的,和青春期正在快速長高的男生相比,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很多男生在和他打招呼的時候,會笑嘻嘻地拍他的頭,他們沒有惡意,卻未曾想到這也是一種“body shame”(身材攻擊),會傷害到他的自尊心。剛開始,我看見他回頭看和他打招呼的人時總是帶著一絲憤怒,到后來變成了無奈。而我選擇不效仿他們的方式,每次打招呼的時候要么拍一下他的背,要么勾他的肩。也許會有同學說,一個男生為什么要對這種事情斤斤計較,大家都只是開玩笑式地打招呼,有什么好在乎的呢?但誰還不是一個脆弱的人呢?只是這件事沒有發生在你的身上罷了。
共情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李世佳(華東師范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副教授)
從一生下來,我們就在不斷和身邊的人建立聯系——從最早照料我們的父母開始,到師長、友人,甚至是陌生人。這種人際關系的網絡對我們來說十分重要,它能夠讓我們獲得親密關系,擁有信任和被信任的安全感,獲取信息、知識和支持。一段穩固和健康的人際關系的基石是人與人互相理解和信任,但是理解和信任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在不斷的溝通和互助中逐漸發展壯大。無論是微小的善舉還是當“涌泉相報”的慈善,都是這種健康人際交往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對于大部分人來說,這種理解和同情他人的能力是天生的——心理學家發現24個月大的嬰兒已經能夠通過一些簡單的行動或面部表情來關心和安慰別人。能夠讓我們對他人產生善意的心理學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種就是共情的能力。共情,有時候也叫作移情或同理心,是指能夠站在他人的角度去理解或感受其正在經歷的事情,也就是進行換位思考或換位感受的能力。當我們看到父母愁眉不展的樣子,我們馬上意識到他們可能有什么煩惱,也能夠感受到他們的低落情緒,這就是共情。但是共情的力量還不止于此:這種感同身受地體會到他人痛苦的能力讓我們坐立不安,我們必須去做點什么來幫助他們,緩解他們的憂郁和悲傷情緒,于是善舉出現了。
但是共情并不等同于善良,很多時候我們想要去幫助別人,但可能并沒有真正站在被幫助者的角度去思考和感受,所采取的行動未必是對方真正需要的——所以善良必須要和共情并存,才能真正“雪中送炭”。
小編說:
第三種善或許是“看不見”的善,但恰恰是我們真正可以力所能及地去表達的小小善意。比如下一次,當你需要在別人或許會感到困擾的時間(比如清晨或夜晚)打電話時,別急著撥過去,不妨先發條短信問問:“你好,現在方便接聽電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