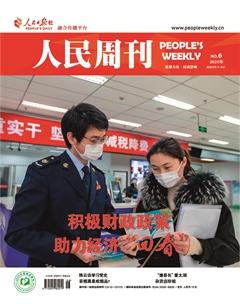探索農村建設用地“增值”之路
武鳳珠
3月10日,江蘇省江陰市華士鎮一宗工業用地以2597萬元的金額順利出讓,成為全市第一宗成功入市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3月5日,在山東省濟南市公共資源交易中心,商河縣殷巷鎮前蘆洼村的一宗工業用地以7025萬元的價格掛牌成交,標志著濟南市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邁出第一步;2月23日,湖南省瀏陽市自然資源局永安自然資源所將全省第一張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不動產權證下發到永安家具制造產業聚集區……
積極探索實施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是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再度明確的農村建設用地市場化方向。通過入市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增值”,我國各地紛紛響應,集體建設用地市場化的探索實踐不斷涌現。
從2015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關于授權國務院在北京市大興區等三十三個試點縣(市、區)行政區域暫時調整實施有關法律規定的決定》,允許33個試點縣(市、區)的存量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租賃、入股,到2019年8月,土地管理法修改通過,依法登記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以出讓、出租被正式納入法律條文,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日趨明朗。
集體建設用地,是一筆價值尚未被充分挖掘的“沉睡資產”。在許多村莊,只需要經過建設用地的一場“騰挪”,村民的生活便可以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在一個行政村范圍內,引導農民上樓居住,整合建設用地,統一建設基礎設施,幫助村莊發展旅游業,實現村民增收,這是天津市薊州區下營鎮團山子村的集體建設用地“盤活”探索。
“一定要把市場決定土地資源的配置放在首要位置。”談及“喚醒”農村“沉睡”的土地資產,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說。
“盤活”集體建設用地,為產業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團山子村位于薊州區北部山區,是距離黃崖關長城最近的村莊之一。多年以來,村民主要依靠種植果樹維持生計。由于許多果品種植的收入抵不上成本,近年來,村莊開始嘗試通過發展旅游業幫助村民增收。
“這個村莊三面環山,缺乏發展空間。村中不僅沒有廣場,就連宅基地也非常緊缺。村里沒有幾條像樣的公路,汽車都無法進入,很難進行改造提升,村莊的旅游業一直沒有得到較好的發展。此外,村莊中還有不少需要新增宅基地的‘剛需。”薊州區常務副區長秦川介紹。
面對村莊的土地供給難題,薊州區決定通過土地“騰挪”來“破題”:引導農民上樓居住,節約宅基地,在集體建設用地上統一規劃建設道路、鋪設水電管網、修建廣場,改善村莊公共基礎設施條件,為旅游業的發展奠定基礎。
“在最初的規劃階段,很多村民由于沒有看到住宅小區,所以無法接受宅基地退出政策。2018年,住宅小區建起;2019年,配套設施逐步完善。建好的小區吸引了一部分村民自愿有償退出宅基地、上樓居住,也滿足了一部分‘剛需的居住需求。”秦川表示,自愿有償退出宅基地是村民取得購買小區住宅資格的前提條件,退出的多余宅基地都實現了復耕或復綠。
引導村民上樓,是薊州區政府經過廣泛調查,順應村民意愿作出的決策。秦川介紹:“2015年下半年,區政府向全區的781個村莊發放了60余萬份問卷,進行了為期約3個月的入村入戶詳細調查。調查發現,受建設用地規模限制,有很多村莊已經10多年沒有分配過新增宅基地了,村民對宅基地分配有強烈的需求。我們詢問農民發現,有80%的村民愿意上樓居住。”
“我的調查結果也是農民更愿意上樓。一部分原因在于,很多農村女孩不愿意打理院落,而集中居住的樓房區有統一的基礎設施,自來水等的使用也都更加方便。”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黨國英認為,村民之所以愿意上樓居住,是因為對自己真正的居住需求不了解。
“真正有利于人類心理健康的居住形態一定是獨棟住宅,這是研究空間與人的心態之間關系的學科得出的結論。從經濟增長到人的心理健康,再到社會穩定,都與居住形態有很大的關系。”黨國英說。
當前,我國的多數村莊尚不具備為村民建設現代化獨棟住宅的能力;農村居民對現代文明的主要認知,往往以城市的高樓廣廈為“模板”。由于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務工,相比部分村莊的宅基地緊缺,宅基地閑置成為我國鄉村更普遍的現象。“在農村建設用地中,有70%是宅基地。目前,我國約有3000萬畝宅基地閑置。”蔡繼明指出。
如何在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允許的范圍內釋放出閑置宅基地的“價值”?以天津市薊州區為代表的引導農民上樓、騰退宅基地、整合利用建設用地,已經成為全國各地的“通行”舉措;各地村民利用自家住宅開辦民宿、開展農特產品電商銷售等,也已經使大量屬于非經營性建設用地的宅基地具有了經營用途;在北京市、陜西省西安市等省市,還有許多村莊將閑置宅基地租賃給懷揣田園夢想的創業者,使村莊成了敞開“胸懷”迎接四方來客的“共享村落”……
集體建設用地的“盤活”,可以為村莊產業發展和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定良好的基礎。“建設用地‘盤活,使農村有了新的人口、新的業態、新的生產生活方式,就有了鄉村振興。”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創新與產業中心副主任鄭鑫說。
有序實現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建設用地同地同權
團山子村建設的住宅小區,占地約23畝,可以容納100余戶村民。
2020年,村民逐漸入住小區。村莊的宅基地節約了,公共基礎設施用地增加了,交通條件改善了;由于采用農戶“點狀”退出、土地復耕的方法,耕地面積不僅沒有減少,還出現了小幅增長。
“在政府扶持下,團山子村增加了數十戶‘農家樂,村民的收入也得到普遍提升。住宅小區靠近旅游景區要道的一塊土地具有一定的商業經營價值,我們將它分割出來,作為天津市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第一塊土地掛牌出讓,掛牌價格達到了近100萬元。”秦川說。
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是使用權的流轉,而非所有權的交易。在世界銀行項目經理章巖看來,將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是我國土地制度中一個有突破性的“創舉”。“這有助于建立一個運作高效、公平的市場。目前在全世界,有越南和埃塞俄比亞兩個國家在緊緊跟隨我國的步伐。”
與此同時,由于當前我國多數村莊的基礎設施尚不夠完善、缺乏足夠的產業配套,而城市無論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還是產業體系都已經發展成熟,相比城市建設用地,農村建設用地的市場競爭力十分有限。那么,放開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是否會出現城市地價高、農村地價低的“懸殊”,從而不利于農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即使政府將某個村莊納入開發規劃,村莊也不會輕易將土地‘拿出來,農民是可以討價還價的。而且,一旦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建設用地同地同權,集體建設用地的價格自然就會提升,因此,不會出現集體建設用地比國有建設用地廉價太多的情況。”黨國英說。
在黨國英看來,把集體建設用地統一推向市場更有利于市場化。“區分經營性建設用地和非經營性建設用地,在實踐中并不好操作。若想實現徹底的改革,就不要區分經營性建設用地和其他建設用地,在規劃的管控下,把集體建設用地統一推向市場,隨行就市即可。只是在集體建設用地增值以后,需要建立健全配套的稅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