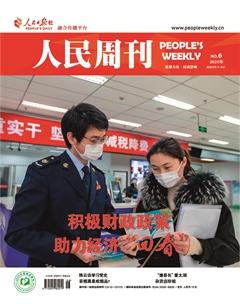讓書香伴成長
何娟

首都圖書館,親子閱讀歡樂多。
4月2日是國際兒童圖書節,也是中國兒童閱讀日,一代代兒童泛舟書海長大成人,兒童閱讀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新年伊始,中宣部明確“推出一批培根鑄魂、啟智增慧的少兒讀物”為2021年主題出版五方面選題重點之一。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兒童讀物成為各界代表委員密切關注的領域,“推進全民閱讀,建設書香中國”被寫入“十四五”規劃綱要。“全民閱讀”上升為國家戰略,讓孩子好讀書、讀好書,兒童閱讀成為全社會共同守護的凈土。
怎么讀——親子閱讀的正確打開方式
一年之計在于春,正是少兒讀書時。周末,走進首都圖書館少兒閱覽室,有爸爸為兒子解讀英雄的故事,媽媽陪女兒探索宇宙的奧妙,奶奶通過繪本童書教孫子識字……窗外山河無恙,室內盈盈書香,歲月靜好不過如此。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國龍認為,親子閱讀體現了現代家長的育兒理念,“與孩子共讀一本書,是對孩子成長最有效的陪伴。但是表面上的歲月靜好,也可能隱藏著一部分家長‘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焦慮心態。”
張國龍稱贊現在是“閱讀的黃金時代”,為下一代的成長學習、圖書的繁榮發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優越條件。“閱讀的良好習慣需要從小培養、長期養成,有些家長一聽說‘閱讀要從娃娃抓起,可能會誤解為‘我的孩子不能比別人落下一本書,那么他可能已經輸掉了閱讀的含金量。”人們常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閱讀的質量有高下之分,但好的閱讀者從不急于求成。“我們學習奧數、英語可以在短期內實現速成,語文成績不在于一朝一夕,文學修養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閱讀習慣持之以恒受益終生,功利性的閱讀對形成健全人格、培養高尚思想沒有任何幫助。”張國龍強調,閱讀沒有“彎道超車”的捷徑,如果家長把親子閱讀視為精英教育的“溫柔攻勢”,那么孩子可能就會失去閱讀的樂趣和體驗。
著名主持人蘇揚,是6歲雙胞胎男孩的爸爸。他跟記者分享了親子閱讀的感受。在孩子大約1歲的時候,蘇揚就為他們購置了4個書架。孩子幼兒園畢業時,書架已經塞滿了各種兒童讀物。值得一提的是,在蘇揚家中,孩子的書房也是他們的兒童樂園,他從不把玩具和書本刻意分開,一邊拼樂高,一邊念童謠,是蘇家父子相處的常態。電視鏡頭前和電臺直播間大氣沉穩的“金話筒”主持人,陪兒子一起讀書的時候則總是隨意坐在積木堆里,或者閑適地靠在床沿、墻邊,兩個孩子就更加盡情釋放天性,躺在床上、趴在陽臺、抱著玩具,甚至四仰八叉的樣子,都是他們在家讀書的日常打開方式。“讓孩子在快樂中閱讀,我就算工作再忙再累,也會被輕松愉快的氛圍感染到。但在尊重孩子天性的同時,家長肯定也要發揮引領者的作用。”依托專業優勢,蘇揚會經常為孩子們讀古詩、念童謠、講故事,但卻不會在咬字發音方面對孩子提出更多的要求。“我能感覺到他們是需要我的,需要我讀給他們聽、幫他們解釋,看到害怕的故事需要安撫。如果非得強調孩子也能跟著你讀得很準確,那對他來說就是負擔,他可能就會不喜歡。”
高質量的閱讀,在聲調、音色、節奏、韻律等方面都可以給孩子帶來愉悅的感受,也可能在今后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我的孩子經常跟我讀古詩,但未必都能理解古詩的含義。比如唐詩《尋隱者不遇》,我們一起讀完了很久之后,有一天他突然來問我‘松下問童子,是不是問的小孩子,或許更久以后,比如他爬個山,看到類似的場景都能想起咱們中國古詩里的風景。”蘇揚認為,兒童閱讀的主體是兒童,親子閱讀更重在親子。“我珍惜現階段的親子時光,也有可能再過幾年他們就不需要我了,需要獨自閱讀的空間。但我現在能做的,就是培養他們良好的閱讀習慣。”

首都圖書館,兒童閱讀。
讀什么——童書市場蓬勃發展
開卷數據顯示,20年來,少兒圖書銷量持續上升,并在2016年首次超過社科類圖書。
經典作品彰顯時代生命力
通過走訪北京多家書店,記者發現,部分家長為孩子選購兒童讀物,對名家暢銷書都頗有偏愛。此外,“中國古典四大名著”等推薦書目也廣受歡迎,被奉為“青少年必讀經典”。基于這種選購標準,有家長獨自“包辦”采購業務,分分鐘實現“快消式”買書。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借助“算法推薦”“爆款營銷”等互聯網手段,這種現象在電商平臺更為明顯。張國龍指出,閱讀不宜偏窄,廣泛的閱讀可以幫助孩子獲取豐富的信息,拓寬知識面。家長選購童書一定要尊重孩子的意見和想法,不能無視孩子自身需求。“兒童沒有自主購買能力,但是家長應該滿足他的興趣愛好,可以買本你認為他應該看的,再買一本他喜歡看的。”
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書讀百遍其義自見,經典對人的教育意義和人對經典的解讀能力同樣重要。“小娃撐小艇,偷采白蓮回。不解藏蹤跡,浮萍一道開。”白居易的《池上》被選入小學語文教材,五言絕句朗朗上口,天真幼稚、活潑淘氣的孩童形象躍然紙上,受到不少兒童讀者的喜愛。“小孩子不可以獨自劃船,偷采白蓮也不環保。”張國龍在成長日記中記錄下5歲兒子對這首詩的理解,閱讀經典是一場古今對談,讓人豁然開朗。“推廣經典讀物,賦予新時代的解讀,讓孩子在閱讀中感受傳統文化的魅力,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才能幫助孩子成為一個更好的讀者。”
文化自信助力本土原創
開卷數據顯示,新書對整體市場的貢獻呈逐年下降的趨勢。2020年,沒有一部新書躋身圖書銷售少兒榜單前十名。
2020年,《淘氣包馬小跳漫畫升級版》等本土原創兒童暢銷書因為觸及“自殺”等話題遭到抵制并被下架,部分家長在互聯網上發動“少兒閱讀保衛戰”,為兒童文學設置“少兒不宜”的邊界,呼吁提高童書創作、出版的紅線。對于這波熱潮,業內人士卻有更為冷靜的觀點。兒童文學作家、評論家安武林認為,家長作為兒童閱讀的把關人,以偏概全斷章取義,因為一兩個細節否定一整部作品,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如果文學創作有禁忌,那就是表達上的尺度問題,如果連碰都不敢碰,這也是作家的失職。把孩子的自殺等問題歸罪于童書,是推脫自己的責任。”
在經典童書強勢暢銷的局面下,新生代兒童文學作品也有異軍突起的案例。近年來,《小狗錢錢》等兒童讀物在成人世界成為網紅圖書。“以前沒被注意到的童書,在成年讀者群體走紅的現象越來越多,說明我們還有很多亟待發現的優質兒童讀物。一本好書可以影響幾代讀者,為孩子選購童書,家長應該自己先讀,認真審讀。”張國龍說。
講好時代故事,培育時代新人,成為當下兒童文學創作者的使命與擔當。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是本土兒童文學創作者的支撐力量和靈感來源。閱讀推廣人李彥池認為,本土原創童書是文化自信的成果體現,更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載體。“比如我們的故宮、孫悟空、花木蘭都應該成為少兒讀物的內容主角,出版機構也應當加大扶持和推廣力度,為孩子播下文化自信的種子。”
引進童書增添多元魅力
說到兒童讀物,很多人都會想到《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等外國兒童文學。起源于歐洲的繪本,近年也在國內的童書市場形成流行趨勢。“少兒繪本也是目前國內兒童讀物本土原創熱情最高漲的板塊,有越來越多的出版社、作者、插畫師投身其中。”圖書出版人鞏少華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學創作對文字有較強的依附性,用現代化的圖文表現手法詮釋中國傳統的“以字表意”,用適合現代兒童閱讀習慣的方式延續文化脈絡,是一個需要長期摸索和積累的過程。
日前,有德國兒童繪本直指“新冠起源于中國”,引發輿論嘩然。在內容尺度、價值導向等方面,部分外籍童書多次引發爭議,如何甄選海外童書,做好兒童閱讀的把關人?鞏少華認為,引進童書必須認清國內外文化差異,堅定文化自信,明確價值觀導向,深入了解國內兒童的閱讀現狀和精神文化需求,選擇適合國內兒童閱讀習慣和審美方式的作品。此外,他建議適當引進在藝術性和文學性兩方面具有前沿突破性,且有利于開闊國內兒童國際視野的作品。“一方面,引進童書可以激活市場增加經濟收益,形成良性的行業競爭,驅動本土原創力;另一方面,不同種類的海外童書也給廣大兒童和家長提供了多元化的選擇,感受來自不同國家優秀文藝作品的多樣魅力。”
電子讀物激發市場活力
“掃描二維碼下載APP,借助VR增強、3D互動等技術手段,星河璀璨盡在眼前,天體流轉在指尖,全新的閱讀體驗、宇宙的神奇妙不可言。”在北京一家新華書店,張蕾打開平板電腦給記者展示了一本名為《飛向太空》的多媒體讀物,“我兒子是個太空迷,才三年級,沒給他配手機,但因為這本書,我給他買了個iPad。”全媒體時代,童書出版探索線上線下融合發展,電子讀物在童書市場異軍突起。傳統觀點認為,閱讀應該依托紙質媒介為載體,才有書香的味道。“除了孩子視力受損,最害怕的還是互聯網的負面影響,希望能有專業的、健康的輔助兒童閱讀的電子產品。”張蕾說。
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圖書零售市場規模首次出現負增長,同比下降5.08%。分析人士指出,紙質圖書的危機未必就是閱讀的喪失,疫情推動閱讀從線下轉移到線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兩種形式都將長期共存。“很多家長都意識到兒童閱讀的重要性,又各有各的力不從心。有的家長工作太忙,又確實存在養家糊口的壓力;有的家長文化水平有限,擔心自己解讀不好、發音不對,害怕孩子問的問題自己答不上來,對于他們來說,兒童電子讀物就是很好的輔助工具。”張國龍認為,電子讀物進入童書市場,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家長可以根據個人的實際情況和兒童閱讀的實際需求進行選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