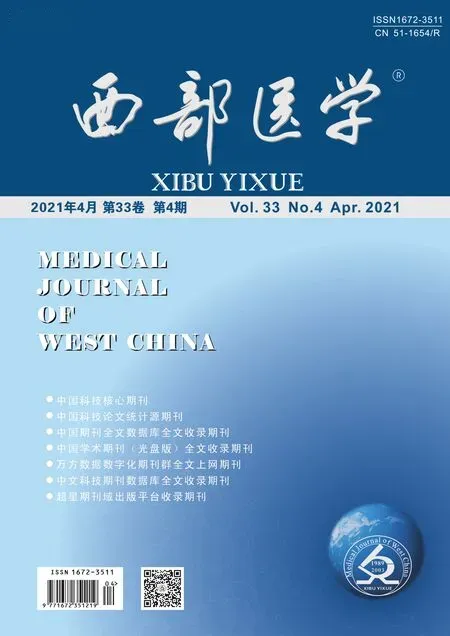ΔD-二聚體與肺栓塞發生事件的相關性*
駱艷妮 王崗 王小闖 李佳媚 張靜靜 侯彥麗
(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重癥醫學科,陜西 西安710004)
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是內源性或外源性栓子阻塞了肺動脈及其分支所引起的肺循環障礙的臨床和病理生理綜合征。肺血栓栓塞癥 (Pulmonary Thromboembolism,PTE)是來自內源性的血栓,是最常見的PE類型,引起PTE的主要血栓來源是深靜脈血栓(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血栓是血液有形成分在血管內發生粘集、凝固形成病理性固體凝塊的過程,血栓形成后打破了凝血功能的平衡,多數凝血因子相繼經酶解激活,從無活性前體轉變為活性形式,直至最終形成凝血酶。凝血酶作用于纖維蛋白原生成纖維蛋白單體(Fibrin Monomer,FM)和纖維蛋白聚合體(Fibrin,Fbn),FM經活化因子ⅩⅢ交聯后形成交聯的纖維蛋白,再經活化的纖溶酶水解產生纖維蛋白降解產物(Fibrin Degradation Product,FDP),D-二聚體[1]是最簡單的纖維蛋白降解產物。臨床中D-二聚體檢測方便、快速,經常采用其作為PE的陰性預測指標[2-3],但臨床工作中發現發生PE后,D-二聚體有明顯的上升。目前尚少研究關于PE時D-二聚體的動態變化,因此本研究探討了發生PE時,D-二聚體變化趨勢,旨在觀察D-二聚體變化(ΔD-二聚體)在PE診斷中的價值。
1 對象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共納入我院2017年6月~2018年7月行肺動脈血管造影檢查(CT Pulmonary Angiography,CTPA)的260例患者為研究對象。根據ΔD-二聚體(間隔1 d)結果分為ΔD-二聚體>0組與ΔD-二聚體≤0組,收集患者的臨床資料:年齡、性別、診斷、影響PE的危險因素:下肢靜脈血栓[4]、腫瘤、呼吸系統疾病、心血管疾病等,及間隔1 d的2次D-二聚體值。根據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肺血栓栓塞癥的診斷與治療指南》[5-6]制定的標準,確定PE人群和非PE人群。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1.2.1 納入標準 CTPA檢查的患者在行CTPA前一周內有2次D-二聚體值(間隔1 d)。
1.2.2 排除標準 影響D-二聚體值的藥物因素:抗血小板藥物(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抗凝藥物(肝素、低分子肝素、華法林[7]、利伐沙班[8]等口服抗凝藥);溶栓藥物(尿激酶、鏈激酶、重組人組織纖溶酶原激活劑);膿毒血癥[9];彌散性血管內凝血;腎功能不全[10];重癥肝炎;1個月內有手術、外傷者;已經使用抗凝治療。
1.3 研究方法 采用免疫比濁法檢測血漿D-二聚體。儀器采用日本SYSMEX CA1500全自動凝血儀,試劑為原裝配套試劑,校正物質控物均為德國 DADE 公司提供,標本中D-D與抗人 D-D 單克隆抗體膠乳顆粒發生抗原抗體反應后產生凝集導致濁度增大,通過檢測濁度變化量,與標準曲線對比后自動得出樣本中 D-D 水平。
1.4 指標定義 第一次D-二聚體為D-二聚體1;第二次D-二聚體為D-二聚體2;ΔD-二聚體為:兩次D-二聚體的差值(ΔD-二聚體=D-二聚體2-D-二聚體1)。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共收集患者260例,主要以男性為主(n=147,56.5%),平均(60.72±16.33)歲。其中,ΔD-二聚體在肺栓塞組與非肺栓塞組中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按照ΔD-二聚體是否大于0分為兩組,PE在ΔD-二聚體>0組與ΔD-二聚體≤0組中比較,差異亦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1 ΔD-二聚體在肺栓塞組與非肺栓塞組中的對比[M(Q25, Q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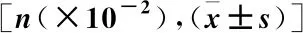
表2 研究對象的一般情況
2.2 Logistic回歸分析 單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ΔD-二聚體>0發生PE組的危險度是ΔD-二聚體≤0的2.755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調整了年齡、性別、心血管系統疾病、呼吸系統疾病、下肢靜脈血栓、腫瘤多因素后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ΔD-二聚體>0發生PE的危險度是ΔD-二聚體≤0的2.829倍,差異亦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ΔD二聚體與肺栓塞的Logistic回歸分析
2.3 亞組分析 腫瘤是發生PE的危險因素,為了探討腫瘤對ΔD-二聚體與PE患病率關系的影響,本研究按照是否患有腫瘤分為腫瘤組和非腫瘤組。在非腫瘤患者組,ΔD-二聚體>0發生PE的危險度是ΔD-二聚體≤0的3.038倍;調整年齡、性別、心血管系統疾病、呼吸系統疾病、下肢靜脈血栓、腫瘤后結果顯示:ΔD-二聚體>0發生PE的危險度是ΔD-二聚體≤0的2.870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亞組分析中ΔD-二聚體與肺栓塞的相關性分析
3 討論
PE是以肺循環障礙為主要表現的臨床和病理生理綜合征,以胸痛、咳血、呼吸困難為主要臨床表現,但這些癥狀并不具有特異性,引起PE的主要原因是DVT。DVT形成表示體內凝血系統與抗凝系統的平衡被打破,凝血因子活化形成凝血酶,作用于纖維蛋白原形成FM和Fbn,FM最終在纖溶酶的作用下形成FDP,D-二聚體是FDP的一種,其水平的增高表明體內凝血酶的生成及血液呈高凝狀態和繼發纖溶亢進,是血栓狀態的一個敏感指標[11],D-二聚體水平的高低受腫瘤、創傷、感染、缺血性心臟病[12]、年齡、妊娠[13]等多種因素影響,D-二聚體在多種疾病中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變化,各類血栓性疾病組和正常對照組D-二聚體含量水平比較均高于正常對照組(P<0.01)[14],血漿D-二聚體水平分別與PE的危險分級呈正相關[15]。
有研究發現,發生PE時,相比于低水平D-二聚體,高水平D-二聚體的患者出現血壓降低、心動過速、或低氧血癥的可能性更高,肺動脈阻塞指數、肌鈣蛋白I水平相應升高,右室增大更明顯[16],因此高水平的D-二聚體可以預測PE的嚴重程度。一項D-二聚體數據采集與時間相關性的基礎研究發現,家兔急性PE模型D-二聚體曲線峰值多位于栓塞后3~7 d,于栓塞后14 d左右開始回落[17],故D-二聚體的動態變化對PE的診斷及治療評價具有一定價值。本研究選擇PE明確前1周的兩次檢測結果。有研究關于出院前血漿D-二聚體水平是急性PE患者的復發深靜脈血栓的獨立預測因子[18],由此證明高水平D-二聚體是PE的高危因素。本研究結果提示,ΔD-二聚體>0發生PE的危險度是ΔD-二聚體≤0的2.755倍,也就是說D-二聚體升高,發生PE的可能性增加。
本研究發現,在非腫瘤組患者中,ΔD-二聚體>0組發生PE的風險遠遠高于ΔD-二聚體≤0組,而在腫瘤患者中無差異。腫瘤患者高凝狀態,是發生PE的高危因素,腫瘤合并PE時D-二聚體明顯升高,有研究D-二聚體取2.79 mg/L作為肺癌患者圍術期靜脈血栓栓塞癥的最佳診斷值[19],關于血漿D-二聚體與非小細胞肺癌病理特征之間的相關性,在T1期肺癌中,D-二聚體> 112.5 ng/mL與惡性淋巴結受累之間存在明顯的關系[20];一項流行病學調查結果提示,合并有PE的肺癌患者將D-二聚體的臨界值設為1.13 mg/L可以提高PE診斷的特異性,而不會影響其靈敏度[21]。因此,合并腫瘤后D-二聚體明顯升高;分析腫瘤患者基礎D-二聚體值高,非腫瘤患者基礎D-二聚體值應該較低,發生PE時非腫瘤患者與腫瘤患者相比ΔD-二聚體變化較大。本研究也證實了這一觀點,ΔD-二聚體在非腫瘤患者中對于PE的診斷更有價值。因此在非腫瘤患者中,考慮PE時更應該關注ΔD-二聚體的變化。
臨床以CTPA作為診斷PE的金標準[22],但增加放射線暴露,造影劑容易誘發腎病,對于血流動力學不穩定的危重患者,CTPA檢查具有不可操作性;D-二聚體檢測方便、靈活、及時,關注D-二聚體變化可以協助臨床醫生警惕并盡快明確PE并指導治療,改善患者預后。本研究還存在一些局限性:臨床資料的收集方面存在明顯的選擇性偏倚:納入例數較少,而前瞻性、多中心的臨床研究更有說服力;動態觀察也許更能說明D-二聚體的臨床應用價值。
4 結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ΔD-二聚體>0與PE之間有較高的相關性,關注D-二聚體變化可提高PE的早期診斷率,在非腫瘤患者中更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