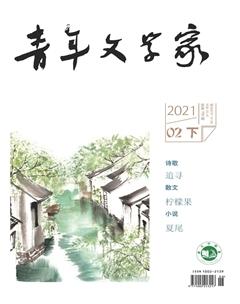論《綠化樹》中的人性異化
摘? 要:《綠化樹》描寫章永璘在物質極度匱乏的社會環境下饑餓的生活狀態與為了活著苦苦掙扎的生存困境。章永璘為了擺脫饑餓,身陷充滿壓抑、占有的異化世界。小說審視主人公的苦難歷程,旨在表現生存掙扎中的人性異化,揭示饑餓給人造成的創傷。
關鍵詞:《綠化樹》;饑餓;壓抑;占有;人性異化
作者簡介:周蓉蓉(1995-),漢族,廣西靈山人,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1)-06-0-02
張賢亮的小說《綠化樹》描寫了“右派”知識分子章永璘在1961年12月到1962年1月兩個多月的勞改生活。故事選取的時代背景正是我國“三年自然災害”與“大躍進”的災難性惡果依然持續的歷史時期,當時章永璘遭遇物質匱乏、精神困厄的現實困境。本文擬探析章永璘為了活著必須苦苦掙扎的苦難歷程,審視小說中的人性異化現象。
“異化”是“主體在發展的過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動而產生出自己的對立面,然后這個對立面又作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力量而轉過來反對或支配主體本身”[1]250。“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這一事實所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同人相異化。當人同自身相對立的時候,他也同他人相對立”[2]45-48。小說《綠化樹》中“異化”具體表現為章永璘被食物支配、章永璘自身的“變形”及章永璘與其他“右派”知識分子之間冷漠甚至相互對峙的關系等。
一、在死亡的邊緣苦苦掙扎
對于章永璘等人來說,饑餓、生存與死亡是沒有鮮明界線的。饑餓是他們在饑荒歲月中可以感知自己還活著的標記,他們活著最本原的追求就是解決饑餓,而他們深刻體驗過的、從未遠離的死亡威脅直接來源于饑餓。
(一)揮之不去的饑餓記憶
因為長期的物質饑餓體驗,章永璘有填飽肚子的熱切渴望,把活著視為首要的追求。在農場勞改,章永璘每個月得到的糧食不超過“二十斤”,每天吃的是定量的稀粥和兩個小小的稗子面做的饃饃[3]22。因為每天得到的食物極其有限,還要進行辛苦的勞改活動,所以章永璘常常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饑餓的存在:餓到極致時,“饑餓會變成一種有重量、有體積的實體,在胃里橫沖直撞;還會發出聲音,向全身的每一根神經呼喊:要吃!要吃!要吃”[3]28。這種被感官放大的饑餓感覺與膨脹的食欲是敏銳而強烈的,它們既是來自章永璘的胃里,也是來自他記憶的深處。因為老鼠偷吃了他那兩個不舍得吃的稗子面饃饃,原本沒有出現的饑餓感覺突然如潮水般涌動。現實的饑餓感覺與饑餓記憶錯亂、交融,催生出一種害怕挨餓的焦慮與恐懼心理,讓他失魂落魄。這是饑餓的“后遺癥”,是深深隱藏在章永璘身體里和記憶中的創傷。章永璘的饑餓記憶就是他胸前遺留下來的湯汁污點,不會洗掉,也不能洗掉。
(二)為了活著而活著
章永璘作為一名知識分子,自然希望得到知識的洗禮,渴望尋求精神上的滿足。但在饑荒歲月中,饑餓的肚皮總能將章永璘拉回現實中,讓他暫時把尋找食物視作所有的追求,為了活著而活著。饑餓無處不在,為了獲取食物,章永璘做了許多自己厭惡的事情:他制作敞口的打飯用具,是為了減少湯汁漏出盆外及通過制造視覺誤差來獲得多一點點食物;他對炊事員諂媚,是為了從蒸饃饃的籠屜布中刮出多一點點饃饃渣;他獨自做完打爐子的活兒,是想偷偷地吃稗子面做的煎餅;他欺騙老鄉,是想以更少的錢換回更多的食物;他一進入馬纓花的房子,就想找吃的……尋找可以果腹的食物而投機取巧也已經成為他本能的沖動。食本原,千方百計尋找食物以果腹自保本來無可厚非,但是背離道德原則,丟棄正義、情義而選取卑劣、變態的謀生手段終究有失人的風范。當章永璘得到馬纓花的幫助可以填飽肚子后,時常翻閱《資本論》,無奈的是:肚子餓時,他腦海中只有“小麥”等與食物相關的詞,并聯想到“面包、饅頭、烙餅直至奶油蛋糕”,饑餓磨滅了他的精神追求[3]53。正如章永璘那字字如血如淚的心理獨白控訴的:“四年的禁錮,四年的饑餓,處分解除后依然戴在頭上的‘右派帽子,已經把我任何別的志向都摧毀了”[3]69。章永璘十分清醒地看到了自身所處的困境:同時面臨物質饑餓與精神饑荒,他苦苦掙扎著謀求改變。于是,他想到了死,希望通過死,湮滅因為掙扎地活著而要承受的痛苦和羞恥,擺脫精神危機與苦悶又虛無的生活。死亡意象出現的時候,正是章永璘認識到自身的墮落、進行深刻的自我檢討與懺悔的時候。在章永璘不斷涌現的“死意”背后,有一顆渴望獲得新生的心。
二、人異化為非人
在饑荒年代,章永璘一次又一次被食物支配理智與行動,變為“生活的全部目的都是為了活著的狼孩”,逐漸“非人化”[3]28。饑餓的另一頭緊緊連接的是人人自危的恐懼與可怕的死亡威脅,人們的欲望、情感和理智備受壓抑,久而久之不免轉向病態與異化。
(一)壓抑:異化世界的悲慘現象
章永璘被饑餓逼迫到充滿焦慮、恐懼、絕望的黑暗角,身體與心靈都遭受嚴重的壓抑與殘酷的折磨,不僅食欲被壓抑,性欲也被壓抑著。第一次見到馬纓花并接過她給的鑰匙之時,章永璘把那還有體溫的鑰匙看作了馬纓花的手,反復看、反復撫摸,使得一直被埋藏在他內心深處的情欲才開始抬頭并得以投射,但他的身份與饑餓境遇使他難堪,他甚至不敢正視她。后來,馬纓花對他表示了愛意,他才開始欣賞她的容貌,接受她給予的食物,在她身上傾注關于愛情與情欲的想象。因為害怕失去恩人贈予的食物與來自殘存道德意識的壓抑,章永璘始終用懺悔壓制心底暗涌的性欲,不敢做出逾矩的行為。章永璘在馬纓花幫他縫扣子時,擁吻了她,但在馬纓花以會傷身體、妨礙他讀書為由撲滅了他的性欲望后,他自己又通過決絕而深刻的檢討與懺悔進行了二次壓抑。“性壓抑常常與負罪感相伴相生”[4]103。當章永璘的性欲被壓抑時,他的負罪感甚至是崩潰的感覺都會變得越來越普遍,而沉重的生存壓力和為了謀生不擇手段、違背良知產生的深重罪惡感依然與日俱增,它們無時無刻不在撕扯、壓迫著章永璘本就脆弱而破碎的心。有學者認為章永璘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進行的深刻反省與批判,“其實只是白日種種心理負重的一種變態宣泄,只是二十五歲青春血液摻雜圣水以后的一種病狀凝結”[5]。章永璘不是在一次又一次壓制自己的性欲望中漸漸成為自己懺悔中假想的、把恩人毒害的怪物,就是在壓抑不住自己的欲望時轉向爆發。
“心理變態者或神經癥患者因沒有能力與他人建立良好關系并滿足他們想得到他讓人承認和贊許的強烈心理需要,所以在憎恨與破壞行為中找到了某種樂趣”[6]40。第一次坐在海喜喜的馬車上,章永璘因沒有受到海喜喜管教而不安、壓抑。面對謝隊長習慣性的管教他又感到恥辱,并暗罵謝隊長是“喜怒無常的小人”[3]33。章永璘與營業部主任都因為政治運動被打為“右派”,可是他們沒有同病相憐,卻始終保持冷漠甚至對峙,互相提防,挑撥離間,缺乏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信任、同情與坦誠。他會因為營業部主任挖到胡蘿卜而心生不快與鄙夷,審視營業部主任的言行并與之暗暗較勁。長期的勞改苦難畸變了章永璘的心靈,使他成為一個異常敏感、脆弱、心理病態的個體。
(二)占有:異化世界的畸變關系
“章永璘自始至終卻都是自私的,他對馬纓花所謂的愛不過是一種利己的需求和占有”[7]。章永璘按時領取馬纓花提供的食物,享受她給予的家庭溫暖,但是直到即將與她組建家庭的時刻,他仍沒有男人的擔當,還是被供養、被保護的孩子形象。章永璘一直貪婪地占有馬纓花的憐惜與付出,并想一直維持這種不平等的依附關系。他們的關系已經被扭曲,被一種異質力量——饑餓、利益主導。章永璘想跟馬纓花結婚,一是因為謝隊長與海喜喜覺得他們應該結合;二是他認為繼續占有馬纓花的食物與愛有悖于外在的倫理道德觀念;三是與馬纓花結婚可以改變他作為資產者的血統,使得后代也有體力勞動者的血統。可見,與馬纓花結婚自始至終都不是因為愛情,是他實現自己的私欲的工具,是他為了自己的貪婪占有實現合理化尋求的許可證,附著強烈功利性色彩。章永璘對馬纓花的柔情很大程度上只是因為感激,也止于感激,馬纓花也可以等同于多分了兩個饃饃給他的炊事員。小說最后,馬纓花長途跋涉來看他,可是他沒見她,甚至“還沒來得及思念她就沉沉入睡了”[3]179。誠然,他們那被摻雜了許多雜質的感情已經慢慢被吞噬,也將會隨著時間消散得無影無蹤。章永璘不舍得付出,不懂得愛人,正像他在自白中所說:“在我的身上,從來沒有過為了別人,為了所愛的人而獻身的精神,從來沒有”[3]164。他只愛自己,不愛他人,他只會一味地占有、掠奪,這也是在異化世界中情感缺乏的表現,“正是壓抑才導致了異化觀念的出現……人過度的占有欲是因為自私,貪得無厭則是一種病相”[8]27。
饑餓的生存困境長期壓抑章永璘的食欲、情欲等自然屬性與全面的發展、群體認同性等社會屬性,他的心性、他體內作為正常人應該有的文明人的素質才發生了變形、扭曲,甚至異化。他的苦難是主要歸咎于那個充斥著饑餓與政治高壓的饑荒歲月,非正常化的社會環境嚴重地擠壓著章永璘的生存與發展:歷史給他定罪,奪去了他除勞動權利以外的一切權利,把他拋棄在充滿饑餓的荒野上,他只能在被壓抑的生存困境中像餓獸一般拼命地掙扎。
參考文獻:
[1]周揚.周揚近作[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5.
[2]馬克思.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3]張賢亮.綠化樹[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4](美)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對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學探討[M].黃勇薛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5]許子東.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張賢亮——兼談俄羅斯與中國近現代文學中的知識分子“懺悔”主題[J].文藝理論研究,1986(01).
[6](美)馬斯洛.馬斯洛人本哲學[M].成明編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7]姜又琳.試論張賢亮對女性的“占有式”書寫——以《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為例[J].玉溪師范學院學報,2017(10).
[8]周立秋.異化的生存論闡釋[D].吉林大學,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