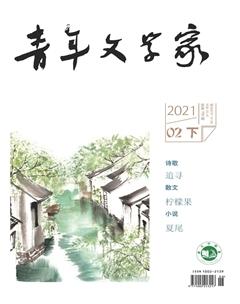孔子“君子”人格獲得路徑芻議
摘? 要:“君子”人格是孔子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論語》中對“君子”人格定義為:仁、義、中庸。并提出“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四條 “君子”理想人格的標準,此標準可以通過忠恕之道、知行合一、見賢思齊、博學于文等四條路徑達到。“君子”人格在提出以后,對后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關鍵詞:孔子;君子;人格定義;路徑
作者簡介:于明珠(1997.1-),女,漢族,山東人,現就讀于揚州大學文學院2019級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先秦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1)-06-0-03
引言:
“君子”一詞從最初代指社會地位高的人到成為道德人格的代名詞經歷了幾百年,最終完成這種定型的是孔子。孔子為了重建禮樂制度和人們之間的道德體系提出“君子觀”這種理想人格。 在《論語》中孔子對“君子”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這種理想人格作為最高追求,后世儒家謹守不移。本文將通過梳理“君子”人格的定義,探討“君子”人格的獲得路徑。
一、“君子”人格的定義
根據《論語》,筆者總結出孔子的“君子”學說的含義。其中,“仁”是根本要求,“義”是價值準則,“中庸”是最高道德標準。以“仁”為本,遵守“義”的要求,追求“中庸”,通過自己不斷地努力,就能獲得一個完備的“君子”人格。
(一)“仁”—君子人格的根本要求
“仁”是“君子”人格的根本要求。《論語》中“仁”共提到了一百零九次,在不同情況下含義不同。“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1]在孔子眼中,身為君子,沒有吃完一頓飯的時間離開仁,就是在倉促匆忙的時候也要和仁同在,就是在顛沛流離的時候也要和仁同在。所以做君子,就是不離開“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2]即仁者愛人。這里的愛人不僅僅指愛自己的親人,朋友,更指每一個人之間都相親相愛,寬以待人,互相尊重,互幫互助。要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把別人的快樂當做自己的快樂,把別人的痛苦當做自己的痛苦。“仁者愛人”就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不同于墨家的“兼愛”,孔子主張的“愛人”是有差別的愛。造成這種差別的標準并非是地位或者財富,而是是否合乎“禮”。所以做到“仁”,就要“克己復禮”,不管是和別人相處講話還是做事,都要合乎“禮”的規范,不逾矩。時時刻刻約束自己,自然也就會“其言也訒”,但這并非是這個人癡傻,而是因為他們謹慎,在每說一句話都要反省是否合乎“禮”之道。如果做到了這些,別人就會認為你是“仁人”。
(二)“義”—君子人格的價值準則
在與人相處時,要時刻懷“仁”,還要以“義”為行為準則。義為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提供了一個價值準則。即以義為先,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3]作為君子,有高尚的人格,在與人相處,做人做事時,不會厚此薄彼,為人公正,處事靈活。這就是孔子提出的為人處世原則。提到“義”,勢必會想到“利”。“義利觀”亦是《論語》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孔子通過對“義利觀”的闡述,對君子的行為準則在道德層面做了界定。“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作為君子,要關注的必然不是小利益,而是大道義。君子要“重義輕利”。但是孔子并不認為“重利”不好,只是要求要取之有道。這也為后來的儒家學者所繼承。當“義”和“利”甚至是與“生”發生沖突的時候,要“重義輕利”,“舍生取義”。孟子在《魚我所欲也》中明確闡釋了他的選擇。生命是君子所追求的,道義也是他追求的,當生和義只能二擇其一時,那么君子會舍棄生命而堅持道義。這個思想,幾乎成為中國古代士大夫乃至近現代志士仁人的行為準則,甚至是自己的理想綱領。明代馮夢龍曾提出:“雖不得其死,然大丈夫殺身成仁,視死如歸,功在當時,名垂后世,何不可愿之有哉?”那些在歷史上“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人,在后世的文學作品中不斷演繹,比如程嬰、公孫杵臼等,甚至成為后世的“偶像”。“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4]孔子認為,身為君子,就要在“義”與其他事情發生沖突的時候“取義”,而“成仁”便是 “取義”的結果和體現。孔子為了“仁”和“義”,可以殺身、舍生。這是孔子所追求的最高道德人格。一個人將“義”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就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三)“中庸”—君子人格的最高境界
在“禮”的約束下,以義為行為準則追求“仁”,這樣是為了達到“君子”的最高境界,“中庸”。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5]“仁”是孔子的道德追求。“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境界。何晏在《論語集解義疏》中提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所以“中庸”就是“宜”,就是適當。儒家的思想植根于人,所以為人中庸,并非平凡或者平庸,而是指人在做事時要“適當”,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人制宜,因物制宜,因事制宜。而且制宜的原則就是“仁”和“義”。中庸就是走中道,“德”的最高境界是中庸,君子最高境界是走中道,而非天道或者地道。“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人是不可能到達“天道”的,天與地是萬物根本,所以孔子不談天的道德。“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6]人能做到的“道”,就是“德”。將天下的人按照“義”的原則去公平對待就是“人道”。中道即人道,人道即仁道,所以仁道是符合人性的,誰都不能違反。這就是“常”即常有常存。故“庸者,常也”。中庸是孔子界定的“君子觀”的最高境界,是一種德行,是人生所能達到的一種最高的道德境界,如果達到了這個境界,甚至超越君子,而達于位于君子之上的圣人。當孔子評價一個人為中庸時,是指這個人已達到或者已經接近至境,事事合禮,大善如水,沒有私心,他做的每件事,所的每句話都是“人道”。孔子自述“六十耳順,七十而隨心所欲,不逾矩”正是這種境界的體現。當然,在《論語》、《中庸》中,孔子曾一再感嘆達于“中庸”非常難,這也正說明“中庸”的可貴。在孔子眼中,達到這種境界的只有堯、舜、禹、文王、周公等寥寥數人矣。正是這種境界的可貴和困難,才成為“君子”的畢生所求。中庸看似是“中”,其實亦是“極”。
仁、義、中庸構成孔子“君子觀”,有了這些,就是君子。君子是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的人格。孔子在《論語》也給出了成為君子的方法。
二、“君子”人格的獲得路徑
《論語》中孔子不僅論述了“君子”人格的含義,亦給出了如何獲得“君子人格”的方法。君子人格,是個人內心在道德層面所遵從的一種規范。這種規范的標準就是“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道”是君子立志的最高目的,但是“君子”是一種可獲得的人格,因此,“道”是可以追求的。最高的“道”就是中庸,在此基礎上,它的核心即“忠恕”。立志雖要目標高遠,可追求的“道”也是需要不斷深化的。人能做到的“道”就是“德”。要“據于德”。“德”就是內心的修養。成為君子的過程中,要將內心的修養轉換為道德的行為,這個轉換的方式就是知行合一。“依于仁”,仁者愛人,就是要保持內心的愛,這個過程是很難的如何不做錯,就要時刻見賢思齊,反躬自省。游于藝,就是對“六藝”游刃有余。要想“游于藝”,就要“博學于文”。如此,將外在的道德規范內化于道德主體的心中,成為道德主體,也就是君子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實踐中自覺地遵守這些道德規范。
(一)忠恕之道
“忠恕之道”是孔子思想中非常重要的道德理想。也是獲得“君子人格”的重要路徑。儒家學者以“忠恕”作為君子追求的“道”的具體途徑,一以貫之。最早將“忠恕”放在一起的是曾子。“孔子呼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7]在這里,明確出現了孔子心中的“道”的內容,亦提出了與人相處的原則和追求:忠恕。儒家的“忠”,是做自己,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8]時內心無愧,堅持自我,就是“忠”。是否“忠”不是別人判斷的對錯,而是做的事情是否合乎自身的道德追求。“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9]。朱熹說:“推己之謂恕。”所為“恕”,就是自己不想遭遇的,也不會強加給別人。“恕道”是一個平等概念,意味著人尊重自身的感受,進而尊重他人的感受。忠與恕,是孔子的“道”,也是后世君子立志的目標,要想成為君子,首先要學習“忠恕之道”。
(二)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獲得“君子人格”另一重要途徑。君子內心的道德修養要在與人交往中反映出來,“據于德”,即將內心的道德規范轉化為外在的道德行為,就是將理論應用于實踐。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10]從這可以看出,孔子認為實踐應該重于理論。“知”與“行”,應該是內與外的關系。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子曰:“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11]孔子贊賞的是知行合一的人,反對夸夸其談,只有嘴上說說的人。“行”就是實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12]在孔子看來,仁愛是人與人之間交流最重要的根基。“能近取譬”是最重要的實踐。能近取譬就是推己及人。一個真正擁有仁愛的君子,不僅僅自己要立得住,也要讓別人立得住;不僅要自己事事行得通,也要去幫助別人事事行得通。推己及人,就是實踐“仁”的方法。
(三)見賢思齊
及時反省自己是儒家修身的重要方法,也是成為君子的重要路徑之一。在成為君子的過程中要“依于仁”,這個要求在踐行時常常會行差踏錯而不自知,所以要“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13]這是先賢提出的修身方法,要時時刻刻反省自身。君子自身就是道德體,君子人格不能靠別人賦予,而是靠自己內在的道德修養指導為人處世。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4]孔子認為當道德個體想到“仁”,“仁”就到了。這就是強調了道德修養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見賢思齊”是道德個體自身主觀的追求,但是自我反省不能閉門造車,而是應該多與別人相處,在于別人相處中,“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5]。儒家學者對這一條謹守不移。另外,孔子提出“反求諸己”,有了問題并非推卸責任,怨天尤人,而是反躬自省。
要想獲得“君子人格”,必須將這件事長久以往地做下去,把反省自己作為像一日三餐一樣重要而尋常之事。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反求諸己時,已經走上了成為君子的正途。
(四)博學于文
孔子眼中,文是非常重要的。君子就要“游于藝”。“博學于文”是“游于藝”的途徑。子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16]孔子認為,君子廣泛學習文化知識,在用禮來約束自己,就不會離經叛道。博學于文,是為了成才。這里的文,包括廣泛的典籍,典章制度,以及最重要的“六藝”。六藝一種說法是指:詩、書、禮、易、樂、春秋。這是孔子為弟子開設的六門課程,后來成為后世儒家學者傳習的六門學科。春秋時期的文字一般記錄在竹簡或者絲帛之上,無數人著書立說,但只有少部分人的思想被記錄并傳播開來。在大浪淘沙中留下的文,是非常貴重的。所以孔子非常強調文的重要性。孔子認為,“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17]天生就懂得道理的人最厲害,最聰明。通過學習而懂得道理的人次一等,遇到困難才去學習的人又次一等。遇到困難還不學習,就是下等的愚民。但是實際上,像舜這樣在孔子的認知中屬于天生的圣人的人幾乎沒有。在尋常人中,沒有天生就懂得道理的人,但是通過學習懂得道理就很聰明了。另外,孔子講的是通過學習懂得道理,而不是知道道理。僅僅知道,還不足以將文中的外在約束內化于心,只有懂得道理才能將文中的在在約束融進自己的生命,成為自己內在的道德修養。孔子不但提出博學于文,還給出了如何博學的切實可行的辦法——學思結合。不僅要學,還要在學習中不斷思考。“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18]如果只學習不思考,就像沙上建塔不牢靠,如果只思考不學習,就像空中樓閣沒有根基。所以學習一定要與思考相結合。“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19]“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20],這些都說明了思考的重要性。
注釋:
[1][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論語·里仁》,中華書局,1980年,第2471頁。(以下所引十三經原文皆出自阮元《十三經注疏》。)
[2]《十三經注疏·論語·顏淵》,第2504頁。
[3]《十三經注疏·論語·里仁》,第2471頁。
[4]《十三經注疏·論語·衛靈公》,第2517頁。
[5][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中華書局,2016年,第21頁。
[6]《十三經注疏·論語·公冶長篇》,第2474頁。
[7]《十三經注疏·論語·里仁》,第2471頁。
[8]《十三經注疏·論語·雍也》,第2479頁。
[9]《十三經注疏·論語·顏淵》,第2502頁。
[10]《十三經注疏·論語·學而》,第2458頁。
[11]《十三經注疏·論語·公冶長》,第2474頁。
[12]《十三經注疏·論語·雍也》,第2479頁。
[13]《十三經注疏·論語·里仁》,第2471頁。
[14]《十三經注疏·論語·述而》,第2483頁。
[15]《十三經注疏·論語·述而》,第2483頁。
[16]《十三經注疏·論語·顏淵》,第2504頁。
[17]《十三經注疏·論語·季氏》,第2522頁。
[18]《十三經注疏·論語·為政》,第2462頁。
[19]《十三經注疏論語·子張》,第2532頁。
[20]《十三經注疏·論語·衛靈公》,第25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