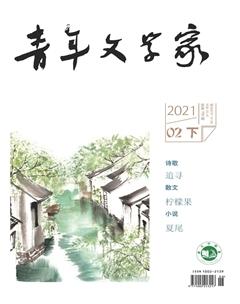“朱買臣休妻”故事的流變
摘? 要:“朱買臣休妻”故事自漢代以來廣泛流傳,關于他見棄于妻的故事成為后來文學創作的題材。“朱買臣休妻”故事出于《漢書》,史家記載此事僅寥寥幾筆。但自唐宋以后,此故事進入文學作品后日漸豐滿,其情節和人物都發生異變。以“朱買臣休妻”為題材的作品在各個時代填入新的情節和內容,逐漸形成更加飽滿的故事文本,其中朱買臣與其妻的形象也在不同的階段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關鍵詞:朱買臣休妻;流變;價值取向
作者簡介:紀亞蘭(1996-),女,漢族,江蘇南通人,揚州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俗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1)-06-0-02
西漢大臣朱買臣一生跌宕起伏,始出于貧賤,后富貴至盛,終因事被斬。他“見棄于妻”的故事雖僅是其一生功業和宦海生涯的小插曲,但以之為題材的作品廣泛流傳于民間。現今可知最早演繹的朱買臣休妻故事始于元代的南戲《朱買臣休妻記》[1];雜劇有庾天錫《會稽山買臣負薪》《朱太守風雪漁樵記》;明清傳奇有顧瑾《佩印記》,單本《露綬記》,《爛柯山》以及《漁樵記》。[2]此外京劇有《馬前潑水》,鼓詞有《朱買臣休妻》,寶卷有《朱買臣寶卷》等。各類文體對朱買臣故事的演繹,可見其流傳之廣。因而分析“朱買臣休妻”故事在不同時代的流變,可反映這一時期的價值取向和民眾心理的變化。
一、“朱買臣休妻”本事及流衍
(一)“朱買臣休妻”的本事
“朱買臣休妻”一事最早見于《漢書·朱買臣傳》,其主要情節大致如下:朱買臣家貧好讀書,與妻以砍柴為生。買臣愛好于砍柴途中大聲誦詩讀書,其妻數次阻止不成,深以之為恥,請休離。買臣言以日后共享富貴相勸,妻子不信,買臣以休書許妻離去。后買臣一人砍柴,歌于道中。故妻與新夫見其饑寒交迫,以飯食相贈。后來,朱買臣發跡,拜為會稽太守,將二人接入府中。一月后,妻子上吊自盡。買臣贈其丈夫銀錢,令其安葬。與買臣休妻故事相類的還有太公望因貧被妻離棄;西晉國子博士王歡妻因家貧自請休離。此類丈夫因貧窮被妻子拋棄的故事以其跌宕起伏的情節成為傳奇的熱門題材,“朱買臣休妻”這段公案亦進入文學創作,同時受當時敘寫風潮與創作者價值取向的影響而發生異變。
(二)“朱買臣休妻”的演變
“朱買臣休妻”故事流傳自《漢書》,買臣妻因恥于買臣謳歌道中的癡傻行為離去,但即便另嫁,見買臣饑寒困窘,仍予他幫助。朱買臣亦處心忠厚,雖曾被妻子討休,但仍因一飯之恩,特居而食之,由此可看出二人性“善”的一面。自唐以后,買臣妻的形象產生變化。《白氏六帖事類集》載:“朱買臣,賣樵薪,其妻恥之,請去。”[3]此句意指朱買臣妻恥夫樵薪,嫌貧離去。明代《山堂肆考》載:“漢朱買臣,其妻恥夫貧窘,遂自嫁于青杉吏人。及買臣為會稽太守,其妻審知其為前夫也。即脫簮珥拜伏舟次,冀得斷弦再續。”[4]買臣妻嫌貧另嫁,是為不貞不潔,在丈夫富貴后希望斷弦再續,便是厚顏無恥了。至于清代,“朱買臣休妻”故事基本與前代相類。文人筆記或史書中“朱買臣休妻”的故事大致不脫離《漢書》所載,亦未有人物性格摹寫。但隨著朱買休妻故事進入文學作品,此故事逐漸豐滿,并產生不同的故事版本和鮮明的人物形象。尤其至明清時期,買臣妻由于其“越禮”的行為而導致其形象在作品中被丑化。
二、“朱買臣休妻”的文學敘寫
(一)“逼休”對夫權的挑戰
漢至唐宋時期“朱買臣休妻”故事大多符合《漢書》記載,唐宋以前,朱買臣休妻故事多見于詩歌與筆記中,這一時期關于買臣妻的評價尚在“愚”中,未有尖刻的人格上的刻畫。
宋元以后,戲劇創作進入繁榮期。《元曲選》有《朱太守風雪漁樵記》雜劇,寫朱買臣岳父以激將法逼朱買臣上京求取功名,但朱買臣一朝富貴,不愿與妻子復合,后經人道說出原委,一家人方才團圓。雜劇中買臣妻雖非真心逼休,但新增“逼休”一節成為朱買臣休妻故事的情節關隘,用以摹寫買臣妻嫌貧愛富的嘴臉。元代社會民風相較于前代開放,“逼休”或僅是在描寫當時尋常的夫妻口角,但在理學森嚴的明清兩代,“逼休”行為是對夫權的挑戰,是不能容忍的。因而后來的作品一旦脫離了團圓結局的約束,買臣妻便朝著潑辣野蠻、狠心貪婪的惡婦形象發展。如明代《爛柯山》傳奇有《逼休》一折,敘寫朱買臣賣柴分文未獲,妻子崔氏與他吵鬧,討要休書。清代《朱買臣寶卷》中買臣妻崔氏逼休更加兇狠,不僅將買臣“罵得七死八活”,而且要得一封休書,連夜便跟著媒婆嫁到張三木匠家中。
因而文學書寫延續“否極泰來”的模式,書生在金榜題名后面對曾經打擊自己尊嚴的妻子,向她們炫耀發達之后的顯貴似乎也是他們當時進考的動力。此外,金榜題名、否極泰來亦是承載著幾千年來讀書人的普遍心愿。
至于明代話本小說《國色天香》所收《買臣記》,大抵依據《山堂肆考》衍生而來。此外,又有《萬錦情林》收《羞墓亭記》,大致與《國色天香》相類。
(二)“馬前潑水”對勢利者的鞭撻
“馬前潑水”情節首次出現于雜劇《朱太守風雪漁樵記》。《漢書》中未記載買臣妻求和一節,更無馬前潑水一說。“馬前潑水”敘買臣妻求和,朱買臣有意刁難,以水覆地,讓妻重收覆水。追溯“潑水”一說,乃是太公望之事。《燕在閣知新錄》中便指出:“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今覆水以為買臣事,非也。”[5]將“馬前潑水”與“朱買臣休妻”故事捏合,除增加故事的曲折性外,更具羞妻之意。因此,潑水一出更是“大快人心”,符合當時社會大眾的心理。即便在夫妻團圓的《朱太守風雪漁樵記》中,“逼休”是劉家女逼其上進的激將法,朱買臣在知其原委前亦以潑水“狠狠報復”了劉家女。
中國傳統儒家倫理不能容忍丈夫被妻子拋棄,故而朱買臣以覆水難收羞辱,極大挽回了其作為丈夫的尊嚴。清代以來流行的“方卿羞姑”故事有異曲同工之妙,它“集中反映了普通民眾改善生活境遇、渴望揚眉吐氣的強烈心聲,表達了他們對嫌貧愛富、為富不仁者的痛切憤慨。所以,此情節經久不衰,尤其得到普通民眾的熱烈歡迎。”[6]“馬前潑水”亦是如此。
三、價值取向影響下的人物敘寫
(一)“嫁夫隨夫”觀念下再嫁女的污名化
陳寅恪先生所說:“夫說經多引故事,而故事一經演講,不得不隨其說者聽者本身程度及環境,而生變易。”[7]故事在流傳過程中必然受到當時人文價值取向的影響產生變化,“朱買臣休妻”各類版本故事受該時期社會價值觀的影響,帶有創作者身處大背景下的時代色彩。
買臣妻形象的轉變與社會對再嫁女的態度有關,女子改嫁的風氣自漢至宋代較為盛行,民眾對此并不以為恥。這一風氣延續至宋代,至南宋末年理學興起后婦女守節被重視起來。宋趙汝鐩的《古別離》中:“嫁狗逐狗雞逐雞,耿耿不寐展轉思。”[8]意為女子婚嫁后從夫,即便生活窘困,也不可離棄丈夫。因此,明清時期女子再嫁不能為人接受,更遑論強迫丈夫休妻的情況。因而,昆劇《爛柯山》《朱買臣寶卷》中買臣妻“悔嫁”“癡夢”“求合”情節便是要襯出她人格的無恥來。《朱買臣寶卷》寫崔氏癡夢:身著“鳳冠霞帔”,滿頭“珍珠奇翠”,使女家仆環繞。寶卷將崔氏觍顏去朱買臣衙門認親,對朱買臣小心翼翼地討好心態刻畫得栩栩如生,頗具諷刺效果。
寶卷著力塑造崔氏潑辣狠毒的一面,卷中有一段針對娶了崔氏的張木匠的一段唱詞:“奉勸世上真君子,不可討了有夫婦。有夫婦女該犯罪,討子居來攪不清。”[9]意在規勸世間女子莫動再嫁之心,亦勸男子莫娶有夫婦。寶卷中崔氏不僅在人格上被丑化,而且在命理上亦受到審判,成為“掃把星”“敗家貨”。總之,文學作品演出的“朱買臣休妻”故事有一個較長的發展過程,再嫁女的形象亦因時代風氣的影響在作品中逐漸被污名化。
(二)人性觀念下溫和的人物沖突
當然,此前作品對于崔氏的口誅筆伐過于尖刻,引起了后人的同情。李漁在評論朱買臣休妻故事時,便道:“古語云,酒食朋友柴米夫妻,做丈夫的人不能夠封妻蔭子也就于夫綱有愧了,連柴米二字尚不周全,使妻妾子女熬饑受凍,這等的丈夫怎怪得妻子埋怨?”[10]此為買臣妻抱屈。當代在演出朱買臣休妻故事時亦更多從人性的普遍性出發。對傳統《潑水》一折,現代人有不同的觀感,“戲情在所謂嫌貧愛富者。然對于朱買臣之一片忠厚待人,反埋沒之矣。”[11]因而當代昆劇本中的《潑水》,朱買臣在見到前來相認的故妻時,改為態度較溫和,甚而讓朱買臣有意收回崔氏。當代戲對朱買臣形象的處理雖已脫離原本傳奇賦予角色的性格,但他更加符合現場觀眾的價值取向和情感訴求。[12]
總之,“朱買臣休妻”故事依舊活躍于當代各類民間說唱文學中,是寒士發跡變泰的典型。其故事的曲折性和特殊性成為當代文學不可或缺的主題。考察“朱買臣休妻”在各類文藝中的演變亦可一探妻子逼休與當時社會風氣碰撞下綱常倫理與民間婚姻觀念的沖突和相互影響。
注釋:
[1]邱劍穎:《梨園戲〈朱買臣〉傳統本創作考略》,《福建省藝術研究院》,2012年第4期,第274頁。
[2]莊一拂:《古代戲曲存目會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頁。
[3]〔唐〕白居易:《白孔六帖》卷十七,《四庫全書》第89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56頁。
[4]〔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三十,《四庫全書》第97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23頁。
[5]〔清〕王棠:《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五,《四庫存目》第100冊,山東: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00頁。
[6]王定勇:《明清以來蘇州彈詞“方卿羞姑”的傳播》,《藝術百家》2017年第6期,208頁。
[7]陳寅恪:《西游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17—218頁。
[8]《朱買臣寶卷》,咸豐七年(1857年)抄本。
[9]同上。
[10]〔清〕李漁:《連城璧十二集》,《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頁。
[11]王玉佩:《張恨水散文》第3卷,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頁。
[12]陳春苗:《從“朱買臣休妻”故事的當代整編看昆劇全本戲之整編》,《戲曲研究》,2008年第3期,第37-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