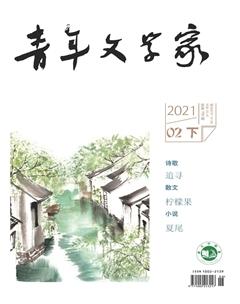李白詩歌中的女性隱喻淺析


摘? 要:借助女性身份言說是李白詩歌的一個重要特征。李白詩歌中的女性隱喻的建構機制建立在詩人對女性形象的認知和自我認知之間的心理相似性,從而主要產生兩個方面的映射: 一、李白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女性映射自身才華和追求;二、李白將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女性的社會地位映射自身的官場地位。李白詩歌中的女性隱喻不僅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而且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
關鍵詞:李白;女性隱喻;心理相似性;隱喻建構;映射
作者簡介:周燕(1987-),漢,江西井岡山人,三亞學院講師,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1)-06-0-02
一.引言
作為中國詩歌史上最璀璨的星,李白被世人尊稱“詩仙”,其詩歌數量和質量都是一騎絕塵。李白善于觀察生活、體察民情,穿梭于生活各個角落,定不會遺忘抑或悲憤、抑或哀婉、抑或纏綿、抑或鏗鏘的女性群體。他一生創作了近千首詩歌,其中一百三十多首詩有關婦女題材,可以說是創造了豐富的女性隱喻。
二.理論框架
Lakoff和Johnson在《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提出隱喻不僅是一種修辭方法,而且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思維方式,體現了概念系統由具體向抽象的認知機制。隱喻包括始源域和目標域,基于始源域和目標域之間的相似性,實現由始源域向目標域的跨越映射,有利于我們認識新鮮的、未知的、陌生的、抽象概念。這種映射主要以我們的身體經驗、社會經驗和文化經驗為基礎,具有系統性、單向性和局部性等特點。
三.女性隱喻淺析
隱喻是詩歌的靈魂。李白詩歌中的女性隱喻,借助女性身份言說,但其真實意圖并不是描述女性本身,而在于托物言志,這是中國古典文學最具有民族特色的表現。在這里筆者著重選其中篇章,對李白詩歌中的女性隱喻進行詮釋。如下表:
隱喻的認知機制是人們利用熟悉的,具體的,易于理解的A事物(始源域)來認識未知的,抽象的及難以理解的B事物(目標域),根據兩者事物之間的物理相似性和心理相似性進行A到B的跨越映射。構成隱喻的四大要素(即本體、喻體、喻詞、喻底),例如“人生是一場旅行。”中“旅行”是始源域,即本體,“人生”是目標域即喻體。因為人生和旅行具有人們認知的心理相似性,比如充滿很多不確定性,有困難也有順利等等是喻底,“是”是喻詞。因此人們可以借助旅行來理解人生。同理可證,李白詩歌中的女性隱喻的認知和建構機制就是使用人們熟悉的女性來寄托李白的思想、意志、情感、體驗、欲望等深層次的心理。
(一)利用女性的地位建構隱喻
李白描寫女性詩歌中經常用的一個喻體就是中國傳統道德倫理中女性的地位。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父權社會。女子依附于男性而存在,社會地位從屬和低下。女子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夫為妻綱。女子沒有話語權,沒有獨立人格,更沒有人生自主權,就像《毛詩·小雅》頌道:“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或唐代李華的《雜詩六首》里寫到“女蘿依松柏,然后得長存”,沒有獨立人格的女人唯有依附于男人,就像松蘿唯有依附于松柏,方可得以生存。中國古代的社會結構是“家國同構”,決定了政治關系實質上是由血緣關系來確立的,傳統儒家以“君父—臣子”來表達這種關系。因此在政治生活中,君為臣綱,臣子依附于君主而生,君主在上,臣子在下。孔子曾說:“君待臣有禮,臣事上以忠”,后來這句話被后世逐漸演變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臣關系猶如家庭里的父子關系,作為子女,必須絕對服從父親的命令,父親在家庭中有著絕對的權威,這就是眾所周知的三綱五常中的“父為子綱”,在婚戀觀上表現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君臣關系,父子關系和夫妻關系表現為上下、尊卑、從屬以及陰陽的關系。在國家中,君為上,是尊貴的主宰者,臣子是卑下的追隨著,在家庭中父,夫為上為尊,子女和妻子為下為卑,從屬于父親丈夫。在傳統的陰陽觀點中,君、父、夫體現天的“陽”面,而臣、子、妻則為天的“陰”面。因此,為人臣,為人子如同為人妻,地位低下,身份卑微,被他人主宰命運。基于女子地位和臣子地位的一致性,對命運同悲的身份認同感的強烈情感共鳴使得李白在詩歌中大量運用女性隱喻來抒發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郁郁不得志,官場上懷才不遇的憤怒以及被君主重視欣賞的渴望。表1中的例1-4中的征人婦和商戶,她們依靠丈夫安身立命,一旦失去丈夫就會陷入悲慘的境地,猶如李白依靠君王的喜好才能施展才華和抱負。表1中的例5、6、7李白表面上描寫婚姻中的女性渴望丈夫的一心一意,從一而終,卻遭受丈夫的背叛和拋棄。實質上詩人借棄婦自貶,抒發不得君心,不得重用的焦慮,失意和無奈。
(二)利用女性的外貌建構隱喻
“美人”是詩歌文學創作中使用頻率最高的意象之一。詩人多用美人隱喻原因有二。一是審美導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愿得黃金三百萬,交盡美人名士。”愛美之心,人皆有之。這是人的本性,追求美麗和美好的事物。然而美麗的事物容易引起人們的嫉妒和破壞,當美人遭受遺棄和破壞時更能讓世人發出可惜,可憐的感嘆,如蘇軾在《薄命佳人》中嘆到:“自古佳人多命薄,閉門春盡楊花落”。二是價值導向:中國古代信奉“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因此古代文人最佳的出路就是通過科舉考上,走進官場,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抱負和最高理想。為了刺激讀書人懸梁刺股,有人作詩“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顏如玉”,所以古時候成功人士的標配是高官厚祿和美女環繞。這也體現了封建社會中國知識分子“官本位”的價值觀念,讀書的目的就是走上仕途,濟世安邦。隱喻的建構機制是相似性,不僅僅是本體和喻體之間存在的客觀相似性,而且也包括認知主體在本體和喻體之間主觀建立起來的普遍的心理相似性。王昭君作為四大美人之一,因未賄賂畫師,遭到算計,被迫出使西塞,落得個“自古妒蛾眉,胡沙埋皓齒”的凄涼下場。李白與她們同病相憐,空有滿腹才華和一腔熱血,卻得不到君王的賞識和重用,只能寄情山水。陳皇后被漢武帝利用完之后拋棄在深宮,打碎了“漢帝重阿嬌,貯之黃金屋”的童話,可惜了阿嬌以色侍他人,哪得幾時好,還沒有美人遲暮,恩先斷,正是李白被皇帝貶官,不得統治者喜愛被厭棄的真實寫照。李白的理想是功成身退,可惜一生郁郁不得志,因此借阿嬌的嘴訴說哀怨憂愁。班婕妤妤好德重德不重色,因趙飛燕的“奪寵”,導致了失寵后的班婕妤因“恨無窮”變得頹廢不堪,影射詩人因才高八斗,壯志豪情在政治上遭人嫉恨而被奪寵的遭遇,以及對帝王專制下個體無法自主人生命運的無奈與悲哀,從而隱喻自己受壓抑的生存處境和受挫折的仕途象以及對“士不遇”現象進行社會批判與深度反思。
四、結語
李白借助女性身份書寫自己的感情,是因為詩人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處境和女性在社會家庭生活中的處境類似,所以這種認知上的心理相似性催生了李白的創作靈感,使得李白創造一個個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和意境悠遠的女性隱喻。
參考文獻:
[1]Lakoff, G.,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25-27.
[2]Lakoff, G., Turner, M.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204-13.
[3]徐有富. 唐代婦女生活與詩[M]. 北京: 中華書局, 2005.
[4]平岡武夫. 李白的作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楊義. 李杜詩學[M]. 北京出版社,2001.
[6]王文戈. 隱喻的文化功能[J]. 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 4) : 117-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