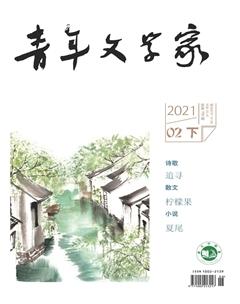自我實現與超越
摘? 要:《復仇女神》是菲利普·羅斯《命運四部曲》系列小說的最后一部,也是他的封筆之作。小說以阿諾德之口講述了脊髓灰質炎和二戰大背景下主人公巴基的坎坷經歷和不同尋常的自我實現之路。本文試圖通過分析小說中的“父與子”關系之“追隨-背離-回歸”來透視羅斯在年過古稀之時對于猶太傳統與美國現代主流文化的閾限性、集體與個人、人生意義等問題的終極審視與思考。
關鍵詞:需要;自我實現;父與子;羅斯;猶太
作者簡介:林微(1994-),女,漢族,黑龍江省牡丹江人,英語語言文學碩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學、猶太文學等。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1)-06--02
按照猶太傳統的“父與子”母題,可將“父與子”關系分為家庭羅曼司式的父子關系、父輩與子輩、師傅與門徒、上帝與信徒,甚至是視角更為宏大的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的關系等等。“父親”往往象征著權威、傳統與固守,而“兒子”則代表著服從、適應和突破。[4]本文通過“父與子”母題分析《復仇女神》中主人公巴基和阿諾德對于自我實現之路的追尋過程從而理解羅斯暗含于文本之中對于猶太人身份和傳統走向的成熟思想蛻變。
一、“父與子”關系之追隨
傳統上,猶太人就有追隨圣父耶和華的信仰。據《舊約》記載,篤信上帝耶和華的希伯來人被上帝選中為天選之子,他們與上帝締結圣約,盟約要求他們將上帝視為唯一的神并按上帝的授意從事。[5]被上帝受膏的彌賽亞諸如亞伯拉罕、以撒、以色列、摩西等都曾與上帝達成盟約,為希伯來人民傳達圣意,上帝必將拯救那些堅信他的子民,也必會懲治無端作惡、破壞約定的人。
猶太人歷史上也篤信集體精神。追溯猶太人的歷史淵源,我們就能窺見其遭受迫害的原由。然而意志堅毅的猶太人憑借著難以磨滅的民族信仰和團結一致的集體精神最終存活了下來,猶太人民也終于得以安家和建國,這深深地體現了父輩與子輩齊力同心所創立的不朽傳奇。
《復仇女神》中的“父子”關系首先體現在巴基與外祖父身上。羅斯塑造了子女對父親的血緣歸屬和自然崇拜,同時也體現了子女對父親傳統意志的傳承。這種追隨父輩的行為不僅出于血緣紐帶的本性,也出于人性本身的需要。根據馬斯洛的自我實現理論,只有當低級需要得到滿足,人類才會將目標瞄準更高一級的需要[2],最終達到精神境界的滿足與擢升。巴基由外祖父母養育成人,雖然缺失了父母之愛,但是外祖父如父親一般的堅忍不拔以及外祖母的溫柔慈愛正好彌補了巴基愛與歸屬的需要,尤其在外祖父正統猶太教的熏陶之下,巴基成為了一名品質堅毅的體育老師。
其次,“父與子”的關系還包括師長和學子之間的關系。因此,“父子”關系也體現在巴基與其學生阿諾德身上。他在與孩子們的交往中正好扮演了父親的角色。孩子們的尊敬和仰慕不但滿足了巴基作為“父親”受尊重的需求,而且還滿足了他對于歸屬與愛的需要。相應的,他也給予孩子們細膩的關愛,提供給孩子們師長如父親般的強大后盾,讓孩子們在愛與歸屬的需要上得到滿足。作為在傳統猶太環境長大的羅斯,也如阿諾德一般依賴他的“父親”,我們從羅斯將紐瓦克市搬到小說中就可以看出父輩的傳統力量對他的影響。這種深刻的影響力便是源于深厚的“父子”情感和血緣紐帶的追隨與擁護。
二、“父與子”關系之背離
猶太人受難史的起源通常被歸結為違背了與上帝的契約。在《創世紀》之中,亞當和夏娃違背上帝的旨意偷食禁果,這打破了與上帝的約定,上帝降下懲罰使之遭受無盡的苦難。[5]此外,在《舊約》之中仍有證據指出猶太人與上帝“父與子”關系產生的裂痕給猶太人招徠苦難。在上帝經年累月的庇佑之下,希伯來人開始有恃無恐、作奸犯科,曾經順從的子民也為了安寧轉而去信奉其他的神祇,這讓上帝怫然不悅,降下災難。可見,“父子”關系中也不乏“父與子”之間的沖突。
此時,環境更為輕松、文化更加包容的美國無疑成為諸多逃亡中的猶太人首選的理想國。然而,美國并沒如猶太移民想象之中的那般理想,他們在與美國文化的交融之中產生了不可避免的沖突,常常因為身份的特殊性而面臨進退維谷之境。對于固守猶太傳統還是努力適應美國主流文化往往讓他們產生困惑,尤其是出生在美國的猶太人后代,他們受父輩傳統文化的影響,也受到來自美國主流文化的同化與滲透。
在文化適應的程度上,父輩猶太人更希望保留祖輩世世代代的傳統文化與精神并相信只有通過猶太人內部的團結一致才能夠抵御外在的非猶太人敵對勢力,而后代則更希望積極融入美國文化,努力實現自我價值。因此,在文化和歷史兩種維度之中,“父與子”的關系產生了沖突。作為第二代移民后代,羅斯嘗試通過文學的手段去爭取民族、文化和精神的開放和自由。然而羅斯的見解卻不能被傳統猶太父輩所接受,使他不可避免的處于尷尬的境地之中,在傳統猶太文化和美國現代主流文化中夾縫生存。
“父與子”關系的沖突在羅斯筆下的《復仇女神》中也有所展現。勢不可擋的脊髓灰質炎還是席卷了猶太社區,運動場上的孩子,相繼患病,甚至死亡。與此同時,瑪莎不斷勸誡巴基離開紐瓦克到安全的印第安山來工作。在死亡恐懼的重壓之下,巴基選擇了逃離紐瓦克,這使他辜負了外祖父的期許,也罔顧責任與擔當的教義,選擇了一個更為輕松的環境來擺脫沉重的壓抑。猶太民族生活在美國社會就意味著文化適應和不可避免的同化,正如小說中巴基的所做的選擇那樣,面對苦難,“兒子”自然而然會傾向于選擇消解并在社會生活中挑選一條更為平坦、容易的道路。相反,猶太父輩們則傾向于固守傳統,因為歷經千年壓制與迫害的猶太人在歷史、文化和宗教幾經苦難的洗禮之中,讓猶太人民見證了集體團結的力量并因此深深堅信猶太族群是一個大的整體,只有民族內部團結一致,努力維護民族傳統和文化才不會被外族勢力打敗。
隨著巴基的離去,越來越多的孩子感染了脊髓灰質炎,命懸一線,孩子們想要得到來自巴基“父親”的強大精神支撐和庇護,這種安全感和歸屬感的喪失使得兩者之間產生了沖突,讓“父與子”的關系產生了背離。正如羅斯所遭遇的,他的作品是為了個人和猶太集體能夠更好地適應美國主流文化,而許多猶太人、批評家,甚至是他的父親都批評羅斯貶損、折辱了猶太人形象。[3]在羅斯多部小說中我們都能看出隱含于文本中的他對于生活和有關猶太問題的個人觀點進行了投射和縮影。羅斯渴望通過美國社會真正地實現自我并通過個人創作給予大眾以猶太人的一種新鮮的呈現,試圖通過揭開面具、平和猶太受害者身份來縮短猶太族裔與美國主流文化的距離感。但是羅斯的這種創新、大膽的嘗試并不為傳統身份的猶太“父親”所接受和支持,因而矛盾和誤解造成“父與子”之間的嫌隙越來越大。
三、“父與子”關系之回歸
小說中巴基和阿諾德在脊髓灰質炎瘟疫的肆虐下幸免于難之后轉而開始追求感情的歸宿和心靈的依托。在《復仇女神》最后一部分,人到中年的阿諾德與晚年的巴基再次相遇,個人的境遇已然完全不同。阿諾德沒有自甘墮落,雖然他和巴基一樣身體落下了殘疾,但是他卻選擇重新經營自己的生活,努力實現自我價值,而不是在受害者身份中自怨自艾。“父親”巴基則在內心的責問之下以得到了內心的救贖。他認為自己是“傷寒瑪麗”、“隱形之箭”[1],這一切災難是因為違背了自己的職責,離開紐瓦克市引起的。此處正好隱喻了猶太人違背與上帝的誓約,上帝給猶太人降下災難,同時也和小說的題目相呼應,復仇女神懲罰那些做了違背傳統標準的事情。巴基將罪過歸結為自己對傳統的違背,他甘愿領受懲罰,因而從中超越自我實現。
阿諾德則認為只有積極融入社會才能自我實現,而巴基則認為只有實現內心的救贖,站在人類發展永恒的角度,為他人謀求更好的發展并消解自我內心的負罪感才能真正實現自我。[2]二者都是為了滿足需求、更好的生活,為了能夠立足社會,目標都是為了更好的存在于這個世界,但是在文化的適應力和傳統的揚棄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使得“父與子”之間的關系形成了兩級分化,這種分化不僅僅體現在傳統家庭和社會之中,更體現了傳統猶太文化和現代美國主流社會之間的極大的沖突與矛盾。在“父與子”關系的閾限性中雖然充滿矛盾,但也能讓人看到希望。正如在小說尾聲,阿諾德回憶了巴基扔標槍的一幕,“當標槍越過巴基的肩膀,急速的沖出去的瞬間,對于阿諾德這群孩子們來說他是不可戰勝的。”[1]這也象征了身為子輩的阿諾德對于“父親”巴基傳統化身的認同,雖然積極融于現代生活,但還是向傳統回歸了,在“父與子”的閾限中,也即“傳統與現代”的過渡中努力尋找平衡,也是對自我身份的一種努力追尋。在父輩的引導之下,子輩亦實現了精神上的升華。
結語:
在羅斯寫實小說《遺產》中,代表著傳統與現代的兩人在生離死別之際才真正放下成見,在血緣紐帶中,在現代變遷的閾限性之中彼此讓步,也實現了傳統與現代發展的平衡。這可謂是通過血緣紐帶,實現了羅斯猶太性與民族性的回歸,也超越了個人的自我實現奔向了集體的、族群的,甚至全人類的自我實現之路。在羅斯為我們所描繪的如災難般的《復仇女神》圖景中,羅斯以普通猶太人“父與子”之間的沖突隱喻并影射了傳統與現代的沖突,以小見大,從而展現了全人類面臨精神困境的終途,蘊含了人類生存的意義的深刻內涵。
參考文獻:
[1]Roth, Philip. Nemesis [M].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2010.
[2]馬斯洛. 自我實現的人[M].許金聲譯.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
[3]喬國強.美國猶太文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4]劉洪一.走向詩學文化——美國猶太小說研究[M].袁華清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5]王新生.圣經精讀[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