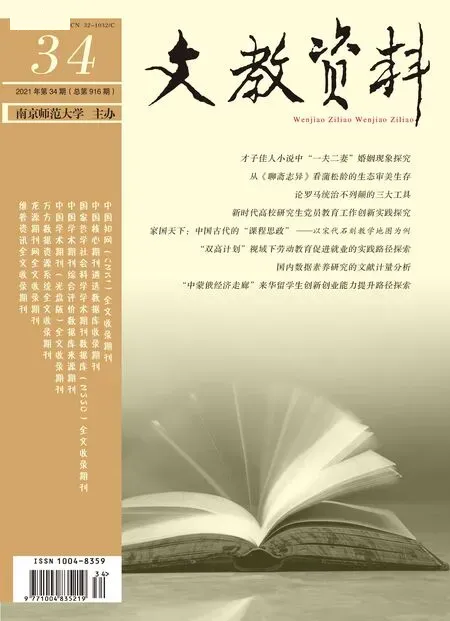才子佳人小說中“一夫二妻”婚姻現象探究
王 晨
(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7)
明末清初涌現的一批才子佳人小說中出現了大量的“一夫二妻”獨特現象,即一位才子同時與兩位佳人成婚,兩位佳人之間不分主次高下,只以姐妹相稱。美國學者馬克夢(Keith McMahon)首先關注到此現象并對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原因進行了探討。他對這一現象作出三點解釋:一是對傳統男人及第后被迫要拋棄糟糠之妻再娶問題的修正和解決;二是將包辦婚姻與自主婚姻對稱化,一個男人既娶了一個包辦的門當戶對的女人,又娶了一個自己認識的佳人;三是將其作為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之間的平衡點。他的觀點顯然受到了結構主義的影響,忽視了中國傳統社會嚴禁一夫多妻的背景。《大明律》中規定:“凡以妻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大清律》全盤接受了此條律法對一夫一妻制的規定。小說中頻繁出現的“一夫二妻”現象顯然與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社會現實之間存在矛盾。
本文對明末清初17 部涉及“一夫二妻”現象的才子佳人小說進行梳理,考察如何處理社會秩序要求和文人幻想之間的矛盾,深入文本分析“一夫二妻”是否真如男性文人構想的那樣和諧,并結合明清之際的社會情況,對才子佳人小說中頻繁出現的“一夫二妻”現象的原因進行探討,最后根據“一夫二妻”現象對才子佳人小說中的女性關系進行新的解讀。
一、才子佳人小說中的“一夫二妻”現象
馬克夢強調“一夫二妻”小說中兩位佳人之間的平等地位,認為“兩位妻子誰也不處于妾的從屬地位”。才子佳人小說極力構建兩位佳人在姓名、外貌、年齡、才華等多個方面的對稱性和相似性,保證其在婚姻中享有均等的地位和權利,維持婚姻中的友愛氛圍與和諧的家庭關系。通過對17 部涉及“一夫二妻”的才子佳人小說進行文本細讀,發現盡管兩位佳人具有極大的相似性,但在社會地位上仍存在細微的差別。佳人父輩社會地位的高低影響了佳人在婚姻中的長幼次序。才子佳人小說中的兩位佳人的平等僅限于家庭范圍,在社會現實和禮制要求上仍存在名分上的大小之分,對此小說作者進行了靈活、隱晦的處理。兩位佳人之間的關系也并不像小說表面上顯現出來的那樣和諧。
宋元強在《清朝的狀元》中根據狀元父輩功名和官職的高低來區分狀元的出身。才子佳人小說同樣強調佳人父輩的功名和官職。按照這個思路,表1 整理了17 部“一夫二妻”小說中佳人父輩的出身。

表1 17 部小說中佳人父輩的出身
由表1 可見,除了《宛如約》《合錦回文傳》《燕子箋》等極少數作品中的佳人出身平民甚至賤民外,絕大多數的佳人父輩都出生于仕宦家庭,但在官職大小上存在差別。佳人父輩官職大小與佳人在婚姻中的長幼地位對應。《巧聯珠》中的佳人方芳蕓之父為正二品的工部尚書,胡茜蕓之父為從五品的刑部郎中;《麟兒報》中的幸昭華之父為禮部尚書,毛燕之父僅是小小的推官。雖然小說表面上按照年齡大小令佳人以姐妹相稱,但本質上年齡的安排受到佳人出身的影響。且小說中強調父輩科舉出身的佳人往往在婚姻中占據主要地位。《玉支磯》和《人間樂》中都著重強調其中一位佳人之父的進士出身,這位佳人與才子先結識并情投意合;另一位不提及科舉功名的佳人父親則被塑造成略顯負面的形象,以致佳人與才子的結合是其父兄的安排。
一些小說通過最高統治者,即皇帝的批準使“一夫二妻”在現實中合理化。才子佳人通過文武功績或卓越才華得到皇帝的賞識與接見,作為規則的制定者,皇帝將“一夫二妻”作為對才子的特殊嘉獎。《合錦回文傳》中梁棟材“為武寧侯,仍兼翰林學士,加兵部尚書”,得到皇帝的特殊批準,其二妻同被封為一品夫人;《生花夢》中將門女子馮玉如勇武善戰,被皇上認定為“奇女”,與才子的另一妻子同贈三品淑人誥命。
雖然才子佳人小說作者極力為讀者營造“二妻”的平等氛圍,但通過文本細讀,可以發現這種平等僅限于家庭范圍,只反映出男主角及其家庭內部對兩位佳人的態度。《燕子箋》中酈飛云和華行云為爭誥命而爭吵;《二度梅》中梅璧之妻陳杏元被封正一品夫人,另一妻鄒云英則被封從一品夫人;《英云夢》中吳夢云被封一品正夫人,英娘被封一品亞夫人。雖然皇帝御旨中都以“妻”稱呼二者,但兩位佳人在社會地位上還是有主次差別。更多的才子佳人小說對這個問題采取了隱晦的回避態度,《麟兒報》《宛如約》《人間樂》《玉支磯》中皇帝賜婚的旨意都是給才子及地位居長的佳人的,并未對“一夫二妻”的結局與現實的矛盾作出正面回應。
二、“一夫二妻”現象頻繁出現的原因
那么為何才子佳人小說中頻繁出現“一夫二妻”現象呢?本文試從小說傳播的影響和社會風氣的角度入手探究背后的原因。
(一)《玉嬌梨》的影響
《玉嬌梨》約成書于明清之際,是現知最早的一部才子佳人小說。《玉嬌梨》存在很多版本,影響力遠及海外,對之后才子佳人小說的創作也產生了很大影響。《玉嬌梨》中采取的“一夫二妻”模式也為之后的許多才子佳人小說所接納。但《玉嬌梨》本身對“一夫二妻”進行了合理化處理。它吸收了民間社會中的一門兩祧習俗,即兄弟二人,若兄有一子,而弟無子,則此一子既為兄之子,同時又嗣弟之后。如此,則兄弟二人各與此子娶妻一人,若兄所與之媳生子,則為兄之孫,反之,則為弟之孫。
《玉嬌梨》中才子蘇友白是符合一門兩祧的條件的,其父蘇浩已去世,只有他一個獨子,叔父蘇淵則六十有三,而“下無子息”。雖然法律上嚴禁一夫二妻現象,但古代通常有些法條因民間力量強大而無法真正落實,一門兩祧即屬其中之一。由于《玉嬌梨》為開山之作,對于后來的才子佳人小說影響甚大,導致后來一些小說只是繼承了其一夫二妻的模式,但對于才子本人是否符合一門兩祧的條件并不特別注意。
(二)清朝婚姻制度演變的反映
滿族在進入中原前一直流行一夫多妻制,“無論貴賤,人有數妻”。雖然他們的一夫多妻并不意味著諸妻之間是完全平等的并列關系,也存在正次之分,但與漢族社會的一夫一妻多妾制有嚴格區別。前者的妻,即使是次妻,也仍然是妻;后者的妻則只能有一個。而妻和妾在禮法上有很大差別。
隨著清朝的建立,婚姻制度也開始由滿族傳統的一夫多妻制向漢族的一夫一妻多妾制轉變。清朝統治者在法律上規定了一夫一妻制的正統地位,但從法律規則的頒布到實施再到社會風氣的改變需要一個過程。“從入關前的崇德年間到康熙時期,正是滿族家庭向漢族的封建宗法制家庭急劇轉變的時期。”但這一階段“無論從規定上,還是從人們的觀念上,尚處于混亂的過渡狀態”。直到雍正與乾隆初期,這個轉化進程才大致完成。
在崇德到康熙年間,雖然“一妻”的地位被確立起來,但作為“側室”的地位在這一階段是模糊的。“在一夫一妻制出現之前,她們是地位低于正妻的妻子而不是妾,在一夫一妻制確立之后,她們的地位下降,卻始終未與妾等同”,直至乾隆間才下降為妾。
以上是一夫一妻制在貴族中的確立過程,但其在滿族平民中的實施有所不同。雖然《大清律》從法律上吸收并確立了一夫一妻制,但從《崇德會典》“其夫若另娶妻,前妻去留在本夫,若婦欲自者去不許”中可看出其對平民要求并不嚴格。根據清朝《內務府來文》中記載的幾例乾隆年間婚姻糾紛案例,這些因婚姻糾紛對簿公堂的滿族人并未以“二妻”為怪,直到因其他婚姻矛盾鬧到官府面前,才依律被懲處“有妻更娶妻”之過。由此可見,直至乾隆年間,雖然法律上禁止一夫多妻,但民間社會的此種風氣仍較普遍,甚至在滿族民眾間直到清末仍可見一夫多妻的痕跡。
綜上,可以看出才子佳人小說中出現的“一夫二妻”情況實則是對清朝婚姻制度轉變時期混亂風氣的反映。但以漢族文人為主要作者的才子佳人小說中頻繁流露出對“一夫二妻”的向往則顯示出清朝統治者政治拉攏的成效。實行一夫多妻制帶有政治意味,崇德年間貝勒岳托曾上書皇太極,對于有妻的投誠漢族官員也可以“以女妻之”,以作為拉攏漢人效忠清朝的手段:“凡一品官,以諸貝勒女妻之;二品官,以國中大臣女妻之……如謂彼有原妻,諸貝勒大臣不宜以女與之,此實不然。彼即離其家室,孤蹤至此,諸貝勒大臣以女妻之,豈不有名?且使其婦翁衣食與共,雖故土亦可忘矣!”才子佳人小說作者對滿族這一婚姻傳統的接納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他們對現有政治體制及清廷統治的認同。
三、“一夫二妻”背景下的女性關系
雖然“一夫二妻”來自男性文人筆下的美好幻想,既要享受雙美齊聚,又要求和諧的家庭關系,但客觀上卻為解讀女性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
塞吉維克(Eve K. Sedgewick)在《男人之間:英國文學與男性同性社會性欲望》中應用“情欲三角”的概念來解讀文學作品中二男一女的三角關系,指出“情欲三角”中兩名男子追逐同一名女子是為了維持二者之間的男性同性社交關系,由此同性之間的感情和交往可能較異性之間更加密切。才子佳人小說中“一夫二妻”三者之間的關系可以視作另一種“情欲三角”,從這個角度出發解讀,兩位佳人之間的關系則顯得曖昧且意味深長。
首先,才子佳人之間感情的純情化與佳人之間的色情化描寫形成對照。才子佳人小說多“文雅風流”,才子佳人往往以詩傳情、以禮自持,不涉私欲,僅僅在合巹夜用“巫山云雨”“陽臺”等詞語含蓄地形容。但《春柳鶯》《巧聯珠》《人間樂》《情夢柝》《麟兒報》《鐵花仙史》等6 部小說中都出現了兩位佳人“假結婚”的情節,且在《春柳鶯》《情夢柝》《麟兒報》中對兩位佳人的“新婚之夜”進行了曖昧且色情的細膩描寫。
在這6 部小說中,《麟兒報》《鐵花仙史》是由于一位佳人為才子守節,面對被逼婚的情況時,女扮男裝逃婚出走,被另一位佳人選中為婿;《春柳鶯》《人間樂》《情夢柝》中的佳人則出自為才子謀求與之有婚約的另一女子的目的,女扮男裝與另一佳人成親。雖然都是為了使才子享受“雙美”的結局服務,但客觀上卻造成了女性關系之間的張力。成親這件事本身就帶有一定的曖昧色彩,《情夢柝》中有沈若素和秦蕙卿之間新婚互動的細節描寫,《麟兒報》中幸昭華和毛燕新婚之夜的色情描寫更是多達一千余字。如此大篇幅和露骨的色情描寫集中于兩位佳人之間,與才子和佳人僅以“云雨一番”簡單帶過的性描寫形成對比。黃淑祺在《李漁戲曲〈憐香伴〉中的女性情誼》一文中梳理了中國古代女性同性情誼的歷史記載,指出其書寫特點是缺乏欲的描寫,而特別在情的追求上有所表現。才子佳人小說中的“一夫二妻”作品則表現出與主流女性情誼書寫不一樣的特征。
其次,才子佳人小說對兩位佳人之間的感情處理更為細膩。比起“私訂終身后花園、一舉及第中狀元、奉旨成婚大團圓”的才子佳人之間的固定愛情模式,兩位佳人之間的相處加入了更多細節化的描寫,互動和感情逐漸加深的過程被呈現得更加完整。兩位佳人時常題詩唱和,互相欣賞,這種情誼類似男性文人之間的同性知己。《玉嬌梨》中 “二小姐各要逞才,得了題,這一個構思白雪,那一個練句陽春。只見兩席上墨花亂墮,筆態橫飛,頓刻間各各詩成四韻”,“只因這兩首詩,你敬我愛,又添上許多親熱”。《飛花艷想》中兩位佳人“每日不是你尋我問奇,就是我尋你分韻。花前清晝,燈下良宵,如影隨形,不能相舍。說來的無不投機,論來的自然中意”。
再次,比起才子佳人之間感情的脆弱性,佳人之間的情誼顯得更加穩固。才子和佳人走到一起要經過很多障礙,如小人的挑撥、家世的起伏、仕途的變化等等,導致才子和佳人的愛情在小說過程中常常系于一線之間,十分脆弱。仕途、家族等因素都會給才子追求愛情的道路上制造障礙,如為了參加科舉或是官職調遷,才子不得已要與佳人分離;有的才子為了追求佳人,化身書童或小廝進入佳人家中尋找機會,但一旦被佳人的家長發現,他們往往選擇逃走或是被趕出佳人的家庭。而兩位佳人由于同是女性的身份,少了一些世俗眼光上的阻礙,二人的相處可以在禮制范圍內變通,反而給她們同性情誼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環境。
兩位佳人在達成雙棲的一致意見后,在婚姻過程中也會出現阻礙因素。兩位佳人面對這些風波時互相幫扶,有著堅定的態度和一致面對困難的決心。面對不能共事一夫的情況,她們寧可犧牲個人幸福,也絕不拋棄自己的好朋友獨自于歸。《玉嬌梨》中白紅玉對盧夢梨說:“賢妹不必多慮,若有爭差,愚姐當直言之。如賢妹之事不成,我也不獨嫁以負妹也。”《巧聯珠》中方芳蕓對胡茜蕓許諾:“倘事不成,我斷不獨歸聞郎,使你有白頭之嘆。”胡茜蕓則回復:“我也斷不拋你而去。總是你我一言之后,死生同在一處。”兩位佳人在這個過程中也會給對方安慰和支撐。《飛花艷想》中雪瑞云在看到梅如玉“每每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時,“時常來勸慰她,只是至情關系,哪里放心得下”。兩位佳人之間的相處正如作者所寫的那樣,“同舟相濟,同難相扶;閨中弱質,反勝丈夫”。
本文并非簡單地把兩位佳人之間的關系作為同性戀去處理,只是希望給解讀中國古代女性的關系和生存空間提供更多可能性,避免將婚姻中的女性單純作為男性的附庸來認識,這樣會忽略其作為個體的復雜性。男性文人出于滿足自己欲望的目的安排一夫二妻的結局,而為了促成這個結局的合理,他們不得不安排更多的細節來描繪兩位佳人之間的感情,結果反而突出了女性之間的情感聯結。
四、結語
綜上,本文通過對明末清初涌現的“一夫二妻”的才子佳人小說進行梳理,發現“一夫二妻”并非像小說表面看上去那樣和諧平等。通過對佳人父輩出身的梳理,發現佳人在婚姻中的長幼次序實則與其社會地位高低密切相關。小說作者會利用皇帝修改規則,使“一夫二妻”結局得以合理存在,但更多作品對這一問題采取了隱晦的回避態度,使“二妻”平等僅局限在家庭的小范圍內。對于才子佳人小說中頻繁出現“一夫二妻”現象的原因,從小說創作與傳播的角度看,是由于才子佳人小說鼻祖《玉嬌梨》的巨大影響,之后的作品繼承了其“一夫二妻”模式。從社會風氣的角度看,“一夫二妻”是清軍入關及清朝建立后婚姻制度演變過程的如實反映,漢族文人對滿族人婚俗的接納和向往展現出清朝統治者政治拉攏的成效。雖然“一夫二妻”是男性文人為了滿足自身幻想的產物,但客觀上卻加強了女性之間的情感深度,為解讀中國古代女性之間的關系和研究她們真實的生存境遇提供了新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