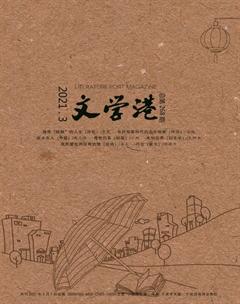物質(zhì)、人情和農(nóng)耕社會的日常(創(chuàng)作談)
項靜
2020年我們的世界發(fā)生了很多改變,因為疫情的原因盡量克制出門的欲望,計劃中回家也是一拖再拖,寫一篇跟家鄉(xiāng)有關(guān)的小說就有了點寄情的意味。2019年開始,我準備寫一個系列的小說,都是以人物為主的,寫那些在我腦海中經(jīng)常來回飄蕩和反復(fù)思念的人,這篇是其中一篇。到2020年,我在城市生活的年數(shù)已經(jīng)遠遠超過了農(nóng)村生活的時長,鄉(xiāng)村和鄉(xiāng)土寫作也不再是備受關(guān)注的題材,甚至已經(jīng)是比較土氣的代言。我經(jīng)常問自己還能寫什么?記憶也越來越空疏,但我所經(jīng)歷過的那個鄉(xiāng)土生活本身一定是扎實的。我只能使用虛構(gòu)的工具,去填補和縫合記憶的空白,我想用一種綿密的語法去表現(xiàn)那里的生活——物質(zhì)、人情和農(nóng)耕社會的日常。而實際上,固然了解一些鄉(xiāng)土的現(xiàn)實,但畢竟已經(jīng)隔膜了,我所能寫的是那里的風度和精神,我想每一個有鄉(xiāng)土生活經(jīng)歷的人往往都難以忘記,也難以祛除那個空間給予自己的痕跡。我想把這些痕跡用小說的方式寫出來。
小時候經(jīng)常跟奶奶去一位孤老太太家串門,她們有一種遠房親戚的關(guān)系,以姐妹相稱。老太太住在一間簡陋的房舍里,腰背駝得厲害,很艱難地繞到灶臺去燒水,特別糊弄地把早飯剩下的熱一熱中午吃。我奶奶每次過去她家,會幫她烙幾張餅,做一些餃子之類的復(fù)雜飯食,一次多做一些,留備她多吃幾頓。我在鄉(xiāng)人們的閑談中知道她的兒子在戰(zhàn)場上犧牲了,兒子的名字叫天賜。村里人經(jīng)常說起那個叫天賜的少年,如何聰慧怎樣的脾性,如何騎馬戴花離開我們村,又如何在戰(zhàn)場上犧牲掉的,好像他們都親眼見過一樣。這個不幸的消息最初被隱瞞了很久,孤老太太不認識字,到村部總能拿到一封封“虛假”的信,都是本地干部以兒子的名義寫給她的,然后再念給她聽。之后很多年,她才知道真相,緩慢地接受了噩耗,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已經(jīng)恢復(fù)了內(nèi)心的平靜。她在我心中留下的形象就是拄著拐杖去領(lǐng)撫恤金,紅色的證書放在一只籃子里,吊在拐杖上,走一步籃子搖晃一下,讓人覺得沉甸甸的,仿佛是時代巨大的暗影壓在一個偏遠之地普通人身上的重量。很多年后,我去過中越交界的一些村鎮(zhèn),清晨逛早市的時候,聽周圍的人說起街面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戰(zhàn)事,仿佛看到我們村那個走散了的天才少年。
小說中的放映員有我家一位親戚的影子,因為經(jīng)常借宿在我們家,一種天生的多才多藝,并且是無師自通,繪畫和唱歌特別厲害,我記得小朋友們都特別崇拜他,似乎他引領(lǐng)著一種跟本土生活不一樣的風潮。小說中寫到過一個細節(jié),就是早上起床盯著看他如何梳妝打扮,那是最早見到男生這么愛美。做放映員的那段日子,他在我們那一帶是風云人物特別受歡迎,他跟本地男青年的追求和想法完全不同,周旋在各種女孩之間,但從不談婚論嫁,跟我父母年紀差不多,但我快讀小學的時候,他還沒有結(jié)婚。最終他娶了一位小他十多歲的女孩,女方父母非常抗拒,還引起了一場大風波。他喜歡喝酒,到處都有人請他吃飯,或者以請他吃飯為榮,在電影失去農(nóng)村市場之后,他沒有及時轉(zhuǎn)變想法,很多跟他一起的人離開這個行業(yè)去打工,去做生意,只有他非常寥落地繼續(xù)做這件接近黃昏的事業(yè)。1993年他身體出了大問題,英年早逝,死于常年酗酒和郁郁不得志。
這篇小說粘合了兩個英年早逝,但在我記憶中閃閃發(fā)光的人物,我嘗試去講述一個狹小空間里生命之間的精神傳遞,有一個偶像就像一盞燈在前面,后來者潛移默化地被偶像的光芒所吸引,哪怕拍電影這種不可能的事情,也在孤注一擲地堅持著。隨著時間的發(fā)展,理想主義的東西消失了,生活也恢復(fù)到了日常的面貌。但那個最初的光芒發(fā)出者,那種充滿光芒的日子是值得記憶和書寫的,小說中的人物都是內(nèi)斂的,他們在內(nèi)心默默含蘊著這種美。小說的結(jié)尾是我老早就想好的,每個人生活中都有你不愿意再去拜訪的偶像,你不愿意再去見他(她),寧愿他們留存在記憶中的高光時刻。喬治·奧威爾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開篇很有感情地寫過一段話,“我喜歡他,希望他也同樣喜歡我。可是我也知道,要保持我對他的第一印象,我必須不再見他;不消說,我的確再也沒有見過他。在西班牙,人們總是這么萍水相逢。”我明白那種感覺。
非常感謝《文學港》雜志,我這一寫作計劃中的8篇作品有2篇發(fā)在這本雜志。感謝我的責編雷默老師對我的信任和認可,也感謝他愿意跟我一起討論很多細節(jié)問題,緩解了初學寫作者內(nèi)心的焦慮。從一個評論寫作者轉(zhuǎn)換渠道變成小說寫作者,思維和行文方式都是不同的,但寫作就是模仿,評論是模仿,寫小說也是,模仿那些創(chuàng)造此種文體模式的人們說話的樣子。評論家寫小說有很多方式,我愿意選擇一條最普通的方式,循規(guī)蹈矩去體會他人內(nèi)心的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