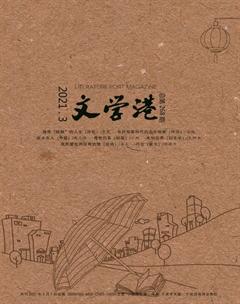好戲如佳人
儲勁松
在青陽聽青陽腔
富貴陵陽鎮(zhèn),風流謝家村。
最近兩年,我三次到皖南的青陽縣,也三次到陵陽鎮(zhèn),這個在春秋時期即為江南名邑的小鎮(zhèn)子,有徽墨歙硯的靜逸氣,清婉淋漓的水氣,也有梨花入井欄的人間煙火氣。傳說古之仙人陵陽子明于此地得道成仙,鎮(zhèn)子因而得名。仙人的居所,自然是上佳福地,陵陽鎮(zhèn)往古來今富貴安樂,每次來都生欣羨之心。鎮(zhèn)上的謝家村卻是第一次來,走在被腳板磨得發(fā)亮的青石路上,看瓦舍人家古祠石獅,如入南朝深處。
村子以謝為名,因為村子里的居民是東晉名將謝石的后昆,村中謝氏宗祠里就供奉著謝石的塑像。他是謝安之弟,曾與侄子謝玄、謝琰等人,以八萬精兵大破前秦苻堅百萬之眾于淝水,這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戰(zhàn)。但風流二字作何解釋?眾人論說紛紜,也多遐想。我以為當作“江左風流”來解,永嘉之亂后衣冠南渡,江南“舊時王謝”兩家歷時五朝,不單功勛卓著權(quán)傾朝野,而且文采風流名公輩出,謝家村的風流,當指風度、氣韻和文采。
村子古老而安靜,皂角樹千柯萬葉如此地謝氏人家。風從村莊背后的九華山來,簌簌吹人衣衫,涼意自兩腋生起,以為將要長出翅翼,化作田間的一只白鷺。在村頭溪邊看見幾樹桃,幾樹毛桃仍青澀,如少年胡須初絨絨,一樹五月桃已七八分熟,淡綠養(yǎng)眼,桃尖一點嫣紅如美人臂上守宮砂,端的婉媚風流。有人說,那是美人尖。
忽然想起昨夜聽青陽腔小戲《美周郎》,那扮小喬的青陽女子,眉梢上的風情嬌嬌俏俏,亦如桃尖一點紅,戲臺上的周郎,雖然姿貌稍欠英武,慷慨恢廓和風流蘊藉仍直追“公瑾當年”。
很早就知道青陽腔,乃因吾鄉(xiāng)名戲岳西高腔為青陽腔遺脈,與之有戲曲流變和文化傳承關(guān)系。
明代中葉,中國戲曲中的南戲,在民間不斷發(fā)展壯大成為明傳奇,名家名作輩出。嘉靖年間,余姚腔和弋陽腔流傳到池州府青陽縣一帶,與青陽方言、土戲和民間音樂結(jié)合形成青陽腔。到了萬歷年間,青陽腔紅遍江南江北,人稱“徽池雅調(diào)”,又與昆山腔并稱“時調(diào)青昆”。所謂時調(diào),時興的小調(diào)小曲,足見其風靡的程度。明末清初,青陽腔傳入與池州一江之隔的岳西,本地文人組班結(jié)社,請專人教習(xí),并將其與本土民歌小調(diào)相融合,孕育出岳西高腔。岳西高腔生根并活躍的主要土壤是民間燈會,其戲曲文學(xué)、戲曲音樂、表演藝術(shù)和基本活動形式都自成體系。至今,岳西民間仍有十多個高腔劇社,縣里有高腔傳承中心,戲曲學(xué)者還整理出版了厚厚兩大本《中國岳西高腔劇目集成》和《中國岳西高腔音樂集成》,搜尋到眾多珍貴的高腔詞曲古抄本。
少年時每逢過年,岳西城鄉(xiāng)都有燈會,從正月初一一直演到上元節(jié),高腔戲是燈會的保留節(jié)目。只是我那時懵懂無知,無論是黃梅戲、高腔、京劇、昆曲、梆子還是山歌,一概是催眠利器。看戲或者說聽戲,是需要年紀的,閱歷漸長人生漸老,漸漸能聽出戲味,漸漸也能入戲了。有一年在劇團看黃梅戲《小辭店》,至殉情那一段,柳鳳英“一見墳臺珠淚灑”,我不知不覺淚滿眼眶,心也如伊似刀挖。有一年在紹興沈園聽越劇《沈園情》,飄飄然以為身在天上人間。有一回在固鎮(zhèn)垓下,聽皖北人唱淮北大鼓《戰(zhàn)垓下》,以為有風云之氣蕭殺之聲。有幾回看岳西高腔《拜月記》《龍女小渡》《天官賜福》,身上像有百蟲一齊抓撓,很想穿上戲衣在戲臺上扭捏念唱一番。
聽一聽岳西高腔源頭的青陽腔,是我的一個心愿。此次來青陽,托同道諸師友之福,終于在青陽腔博物館小劇場里看了一回。青陽腔戲歌《畫里青陽》、青陽腔表演唱《拜月》、九華民歌《喬木的菊花會說話》、青陽腔小戲《美周郎》里,都有熟悉的聲腔熟悉的味道。尤其是壓軸戲《美周郎》,周瑜與小喬新婚之夜相互試探、相互表白的一場戲,讓同行諸君和我大受感染。
華堂瑞靄燭搖光,畫屏巧繡鳳諧凰。百年好合的大婚戲夠傳統(tǒng)夠古老了,千百年來戲人不知道演繹過多少回,“小喬初嫁了”,更是古今人熟得不能再熟的陳年故事,青陽腔《美周郎》卻古韻翻新聲,聽得人心兒拎、腸兒顫、眼兒熱。
一個扮相閉月羞花欲迎還拒,鶯鶯燕燕地唱:“我戀那卿卿我我長相守,夫唱婦隨琴瑟和同。我不要那打打殺殺,爭霸天下的英雄。家家太平九州安寧,才是我的夢。”一個扮相倜儻風流自負文武全才,大馬金刀地唱:“罷罷罷!她若是弱不禁風小女子,燕雀心胸又怎能伴大鵬搏擊長空?周瑜不愿玩世不恭,寧缺毋濫不要木俑。”
明知是戲,是男女調(diào)情忸怩作態(tài),心里眼里卻都在泛潮。
戲唱到末了,周郎小喬兩情相悅你儂我儂,小喬縱身投入周郎懷中,那周郎來了個結(jié)結(jié)實實的公主抱,插科打諢惹人發(fā)笑。正經(jīng)戲臺上不可能有的情節(jié),說是荒誕不經(jīng)也好,謂之神來之筆也未嘗不可。
演員謝幕的時候,我轉(zhuǎn)頭看鄰座的魏振強兄,他還沉浸在戲里出不來。后來他說,那晚體驗到了一種久違的感動和優(yōu)雅。
世人常說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其實人生不如戲精彩,不如戲風雅,也太拖沓太混沌,愛恨情仇是非成敗都淹沒在時間的茫茫煙水里。這幾天重翻莊子《齊物論》,至罔兩問景和莊周夢蝶兩個橋段,以為莊子是個戲精。他看得通透,演得絢麗。
在青山之陽,九華山麓,青陽雄健又靈秀。我到過青陽很多地方,喜愛這里的清美山川、幽邃村鎮(zhèn)、淳古人情和文章元氣,也愛這里戲臺上的青陽腔,以及當?shù)赜讶怂f的青陽腔。他們的鄉(xiāng)語有吳音亦有楚風,溫婉、柔軟而內(nèi)斂,像《美周郎》里的念白。
在青陽,富貴的不止陵陽鎮(zhèn),風流的也不止謝家村。
聽 戲
寒雨接連下了好些天,日夜瀝瀝如嫠婦,不下雪怕是不得晴了。雨滴持續(xù)砸在塑料遮陽篷上,哐哐,砰砰,硿硿,像小區(qū)拐角那個雄武屠夫操刀剁大骨,耳膜里轟隆震顫如案板,嘈雜無趣得很,夜里聽來更覺得興味索然。
想起少年時冬季在故園聽雨:木格子窗外雨亮如蛛絲,黑松、毛竹和刺杉經(jīng)雨水一洗,越發(fā)顯得精神也越發(fā)蒼翠養(yǎng)眼,草垛如黃袍老僧在山坡上打坐參禪,掉光了葉子的木梓樹枝杈瘦勁如鐵畫。冬雨都不大,篩在魚鱗瓦上,細細碎碎的聲音幽閑而綿軟,像村里的女孩子們說悄悄話,又像眾多蝽象列隊旅行,好聽也耐聽。荷爾蒙在體內(nèi)噼啵燃燒的青春時代,除了上個清閑的班,似乎一年到頭我都無所事事,也似乎總是郁郁寡歡,大把的青春、力氣和雄性激素無處揮霍。水寒山老的冬天尤其感到幻滅和寂寞,下雨天就坐在東廂房的寫字臺前,看雨水從瓦溝里慢悠悠地落下來,滴到院子邊沿的一溜水宕里,叮叮然,嗒嗒然,水宕里的水泡陸續(xù)鼓起來又依次破裂。雨聲小的時候,常常會聽到鄰家程奶奶的收音機里,隱約傳來鑼鼓鐃鈸的聲音,以及裝腔作勢啊啊呀呀的戲文。記得當年我寫詩,在習(xí)作里曾經(jīng)這樣寫過:
寂寞是冬日的雨絲
憂傷是雨點里的戲詞
程家奶奶瘦小而清秀,識得文斷得字,七十多歲了還戴著老花鏡坐在天井邊的小馬扎上,津津有味地閱讀《三國演義》和《海上花列傳》。她有一只袖珍收音機,平素從不離身,聽廣播劇《西游記》,聽單田芳評書,尤其愛聽戲。聽戲并不稀奇,當年村子里的大人都愛聽戲,聽的是本鄉(xiāng)本土的采茶調(diào),也就是黃梅戲,男女老少也都能唱幾句《打豬草》《王小六打豆腐》《夫妻觀燈》《女駙馬》。但程家奶奶聽的卻是高大上的京戲,《智取威虎山》《霸王別姬》或者《鎖麟囊》。這些足以把她與村里其他只會東家長西家短兒女如何如何媳婦如何如何的老奶奶區(qū)別開來。她是大戶人家的閨秀出身,臥房里藏著一對玉鐲子,幾十塊袁大頭,均用綢布包著,還有十幾個明清時期的青花瓷器罐子,里面裝著粗鹽、冰糖、霜果、云片糕、菜種子和豆種子。我和她的孫子是發(fā)小,所以我都見過,然后悄悄告訴了父母。父親當時說了一句話:“富家有舊物”,我至今記得很清楚。我從程家奶奶那里得到的直接教益,一是人要讀書,二是知道除了黃梅戲之外,還有一種戲叫京劇。
童年時心如麻雀叫喳喳,少年時心若野馬噠噠噠,都是極不耐煩聽戲的。戲臺上的人,穿那樣洇紅滴綠可笑古怪的服裝,涂那樣白一道黑一道紫一道藍一道的大花臉,拿鞭子當馬騎,七八個人冒充百萬雄兵,走三五步當作打遍天下,木頭做的棍棒刀槍上戳下戳左舞右舞就算惡戰(zhàn)了三百回合,甩著水袖捏著嗓子假模假式地說白,拖著極長尾音的忸怩唱腔半途像要斷氣似的,這些統(tǒng)統(tǒng)無趣得很,咭咭哐哐、咚咚將將、倉才臺臺的音樂尤其聒噪,比烏鴉叫還難聽。特別不能理解的是,大人們都聽得如醉如癡如泣如慕,就連拖著兩掛鼻涕說話都不利索的二傻子,也抖動著嘴唇跟著鸚鵡學(xué)舌。
但在我的童年時代,對鄉(xiāng)人來說,聽戲仍然是一件大事,是開洋葷。
當年,吾鄉(xiāng)岳西有一個黃梅戲劇團,團里好幾十號人物,導(dǎo)演、編劇、作曲、演員、舞美、樂隊一樣不缺,是安慶地區(qū)人才最齊全的縣級劇團之一。劇團就設(shè)在縣城十字街的中心地帶,一大片仿古木結(jié)構(gòu)建筑,既古色古香又鶴立雞群,把它周圍那些磚混結(jié)構(gòu)的破敗民居全部壓了下去。劇團不單有山城最高級的房子,也是本縣的文化中心。里面有一個大劇場,兩層看臺,二層是木閣樓,總共能容納千把人。戲臺很是寬大,地上鋪著木地板,唱武戲時演員把舞臺踩得轟隆轟隆一片子響。舞臺左右?guī)铮刂佟⑶描尮摹⒋档炎拥臉逢牐輪T像變戲法似的出出入入,幼兒時覺得特別神秘。
那個戲臺上,嚴鳳英、王少舫演過《天仙配》,馬蘭演過《紅樓夢》,韓再芬演過《女駙馬》,黃梅戲的三代代表性人物都曾經(jīng)在這個臺子上粉墨登場,引發(fā)一次又一次轟動。一直到今天,曾經(jīng)看過他們演出的鄉(xiāng)里人仍然引以為榮,說起那時百村上鎖萬人空巷看戲的事情,眼里有無限向往,心中也生出許多惆悵。
我幼年的時候,鄉(xiāng)下實在窮得很,穿破衣爛衫不說,糧食也不夠吃。男女老少肚子里無非園蔬、紅薯、芋頭和野菜,在南方已經(jīng)生長了幾萬年的大米平常很難吃到一頓。紅燒肉只有過年時才有,切成斧頭腦一樣的大塊頭,謂之“斧腦肉”,三五塊堆放在藍邊老海碗頭上,下面墊著干茄子、豇豆角或者腌菜葉,家境稍好的人家也墊黃豆。那肉藏在竹碗柜最里面,來了拜年客才端出來。切得大不是因為慷慨,反而是因為寒酸,除非不識相的人,誰會打“斧腦肉”的主意呢?飯桌上,雖然主人家一直在殷勤相勸:“吃肉哇吃肉哇,莫客氣,莫見外!”客人被勸不過,本來在夾青菜蘿卜的筷子終于猶猶豫豫地舉到肉上頭,一兩寸距離,停一兩秒,然后堅決地撥開肉,搛下面被油潤過的干菜吃。來客里若有小孩子饞不過,不小心搛了一塊肉吃了,主人家表面上波瀾不驚,心里肯定咯噔一下:壞了,哪里找另一塊肉補上缺呢?孩子的父母則面紅耳赤,恨不得地上忽然裂開一條縫,自己好鉆進去,因為孩子沒教養(yǎng),就等于父母沒教養(yǎng)。那時候的人雖然貧窮,卻是要臉的,有廉恥。所有人包括三歲小孩子都明白,那肉是用來看的,不是用來吃的,古代有看魚下飯,我們當時是看肉下飯。飯吃完了,斧腦大肉完好無損,主客都如釋重負偷偷噓一口氣。后來我上小學(xué),在語文課本上學(xué)到“心照不宣”這個新詞,腦子里閃現(xiàn)的自然不是“心照神交,唯我與子”,而是污垢滿面的飯桌上那一碗“看肉”。
長年無肉吃,嘴里不只是淡出鳥來,而且淡得冒酸水。不過沒有人有怨言,因為家家戶戶如此。那時候村民組一二十戶人家,誰家有幾只腌菜缸幾只陶甕子,放在哪個角落里,別人都是清清楚楚的。貧寒不是頂可怕的事,可怕的是富足之后被葷腥喂養(yǎng)得過分膨脹的貪婪之心。物質(zhì)上貧困,精神上也貧乏,偶爾去縣劇團聽一場戲,或者村里放露天電影,就算是饕餮盛宴了。電影不常有,一年最多一兩次。寬白的屏幕下午就掛在大操場上,被風吹得微微地鼓起來,像一道招魂攝魄令,惹得全村的人以及遠近幾十里的鄉(xiāng)親魂不守舍,黃昏時就扛著板凳竹椅候在屏幕前面,等待放映機的那一束幽藍的光呈放射狀打到銀幕上,里面出現(xiàn)風景和人物,上演和素常生活完全迥異的奇妙事件。看一次電影算過了一次年,而且是殺豬烹羊的肥年。我記得村里放過的電影,除了抗戰(zhàn)片,還有《劉三姐》。劇團倒是經(jīng)常唱戲,但看戲是要花錢的,除非安慶來了名角兒,或者上演新戲,鄉(xiāng)親們才舍得去聽一場。
有一年寒冬,天下著大雪,劇團新排的一部戲首次上演,似乎是《西樓會》,要么是《碧玉簪》,村里的老少大清早就相約著晚上去聽戲。我們家離縣城不遠,三四華里,有一條坑坑洼洼的機耕路直通城中,路兩邊是水田和溪流。天黑得早,胡亂煮一鍋南瓜蒸一鍋紅薯吃了,一隊人馬在竹林窩路口集中后,個個舉著葵骨火把,用稻草綁住腳上的解放鞋來防滑,浩浩蕩蕩向劇團進發(fā),人人心里也有火把在燃燒,郎里個郎,浪里個浪。大人們確鑿是去聽戲的,聽的是門道,孩子們純?nèi)皇菧悷狒[,何況大人還早早就許諾給買瓜子糖果吃。
那天的戲主角是誰,唱得如何,何時開演何時謝幕,我第二天是一點印象都沒有了。只知道戲臺上花團錦簇熱熱鬧鬧,戲臺下人頭挨著人頭好比冬天地里的蘿卜。只記得戲開演之前,照例有劇團雜務(wù)打著手電筒挨個查票,對逃票混進來的毫不客氣地攆出去,雙方爭嘴吵架,另有調(diào)皮的逃票者與雜務(wù)滿場兜圈子,死活不肯出去,好笑得很。
我不是去聽戲的,是去戲耍的,也是去睡覺的。正戲開演之前通常有小丑上臺暖場,那小丑蒜頭肉紅鼻子,上面刷一團石灰,兩腮涂著胭脂紅得像猴子屁股,他在臺上不停地翻斤斗,擠眉弄眼,一番雜耍百般搞怪,惹得觀眾喜笑顏開。暖場之后,小丑打恭作揖退出舞臺,正戲開鑼了,戴方巾拿紙扇的小生和穿綾羅綢緞甩水袖的正旦甫一亮相,才唱了三五句戲文,那些臺詞就幻化作一群瞌睡蟲子,嗡嗡營營地飛上了我的頭。旦角生得再美,生角長得再俊,都勾不起我的一點興致。劇場里真暖和,比家中四壁漏風的泥巴屋要舒適多了。
半夜醒來的時候,在父親的臂彎里,一隊人馬仍然打著葵骨火把回村,紛亂雜沓的腳步把地下的積雪踩得吱吱響。我手里還緊攥著兩顆舍不得吃的水果糖。
第二天,幾個昨夜聽過戲的發(fā)小聚在竹林里打雪仗,然后坐在草垛下談?wù)撃菆鰬颉F剿兀B坦克能不能爬上直立的懸崖,母雞吃螞蟻會不會死,我們都要爭得面紅耳赤,但那天大家很容易就達成了共識:小丑好戲,斤斗翻得好,說的話惹人笑;正戲一點都不好戲,什么才子佳人,什么出將入相,全都是假的,遠遠不如看電影《地道戰(zhàn)》《地雷戰(zhàn)》《小兵張嘎》過勁、來事。好戲、過勁、來事,均是吾鄉(xiāng)土語,意思大致是:好玩、牛逼、有意思。
縣劇團也出過好幾個本地過勁的名角兒,走到哪里都是眾星捧月,那十二分的風光可不是假的。許多人從百里之外的鄉(xiāng)下,帶著干糧爬山涉河徒步趕來,就只為親眼一睹他們舞臺上的風姿神韻。假若上廁所時碰巧遇見演員本尊,回到家是可以夸耀很長時間的。若是有人有幸嫁了或者娶了其中的一個,簡直是齊人之福,必遭大眾艷羨和妒忌。
后來我工作了,接觸過當年的幾個本地名角兒,雖然黃梅戲風光已經(jīng)不再,劇團也解散了,他們作鳥獸散,有的進了文化館,有的在圖書館當管理員,有的下海經(jīng)商,有的靠賣早點、開飲品店謀生,但言談舉止之間,仍然戲味十足。好比寫文章的人一輩子都有寫作的情結(jié),唱戲的人即使離開了戲臺,他們依然是戲人。只是沒有戲臺的戲人,神情是落寞黯然的。這些年各地都重視城鄉(xiāng)文化建設(shè)與發(fā)展,列入民生工程,當年的角兒最年輕的也接近花甲之年,城鄉(xiāng)文化的再度繁榮讓他們再次找到了位置,擔當起培育新人的任務(wù),有時縣里的大型演出他們也登臺表演。偶爾和他們閑聊,談起劇團和他們自己的前世今生,也像戲一樣。
劇團其實還在,或者說,劇團的房子仍然還在,只是早就被一把鎖鎖住了,灰撲撲地夾在瓊樓玉宇之間,仿佛卑微的仆役。劇團解散后,劇場作過幾年會場,縣里的兩會和三干會都在里面開。再后來,被鑒定為危房,會也不能開了,于是干脆關(guān)了門。因為處在老城區(qū)的中心,那一塊還是非常繁華,毗連劇團東門的那條一兩百米長的劇團巷,成為美食一條街,南北風味匯聚,整天整夜熱氣騰騰食客滿座。昨晚飯后,我散步經(jīng)過那里,想起當年進城聽戲的事,恍然如夢中,耳邊依稀還傳來啊啊呀呀的戲文。
許多年里,我還是不聽戲,還是像少小時一樣聽不進去。忽然到了中年,有一天夜里讀書時,為了找個伴,無意中點到了網(wǎng)絡(luò)上的戲曲按鈕,是昆曲《牡丹亭》,姑且聽之,然后一直聽到入睡前,覺得其間滋味好,其間好滋味。第二天清晨醒來,又打開手機聽大弦子戲。從此以后,伴我夜讀伴我晨醒的,不再是流行歌曲,而是戲曲。戲比歌妙,水袖舞、小腳點、紗帽閃,皇親國舅、小姐書生、市巷托缽僧“乞我一文大光錢”,戲文里盡是人間興味。也就理解了為什么李漁要寫戲、唱戲、辦戲班,為什么唐玄宗李隆基要在聽政之暇親自教授太常樂工絲竹之戲,為什么《紅樓夢》里一再寫到唱戲、聽戲、梨園弟子。以前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會像提鳥籠子進茶館吹噓順治爺初入關(guān)時如何如何的晚清遺老遺少一樣,以聽戲為雅好。聽戲好比讀史,是需要年紀或者說閱歷的。
今夜冷雨敲窗,我讀古人碑帖,聽《做文章》選段,川劇的、豫劇的、瓊劇的、黃梅戲的以及大弦子戲的《做文章》,一一依次聽來,急管繁弦淺唱低吟里,有無邊風月,有往古來今,亦有雨雪霏霏,也唱盡了古今文人的窮形盡相。寫文章的人,不就是戲文里被“之乎者也、兮哉夫維、詩云子曰”逼迫得幾乎要投井上吊的徐子元么,那般犯難、痛苦、欲死還生。起先一想,戲文戲文,戲與文,文人與戲人,從來都是相依相附惺惺相惜,無文不成戲,戲為文添翼,戲人為何要唱戲為難文人?轉(zhuǎn)念一想,自己又噗嗤而笑:娘的,那臺詞還是文人寫的。
想起六年前的一個下午,山中雪花紛揚銀堆白磊,百竿翠竹瀟瀟如魏晉六朝人物,我在一座亭子下面寫《作不出文章》。當時好風景,快意如何之,若給我白宣一張湖筆一支,東坡所謂“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又有何難?無紙也無筆,只好在電腦上這樣敲打:
作不出文章,就讀讀書吧,養(yǎng)養(yǎng)氣,也養(yǎng)養(yǎng)器。老子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易·系辭》說“形乃謂之器”,我姑妄解之:氣是元氣,器為識量。文章,一氣以貫之;待人,一量以容之。少年時好大言,好文學(xué),好在柳蔭月色下臥沙灘上與眾少年侈談人生。后來不敢了,人生這個詞太重、太濃、太正,寫文章時自覺地全部換成人間、人世、人間世或者人世間。
那篇舊作,我現(xiàn)在想補上一句:文章就是生活的興味。而生活,就是教訓(xùn)和曲折。古今戲文唱盡了大江東去,也唱盡了江流宛轉(zhuǎn)。
人間雨淋漓,不如聽戲吧。
好戲如佳人
說起來有些滑稽,我少年時讀書,根本不看作者姓甚名誰,一本書讀完,作者全然被忽略了。鴨蛋好吃,未必要認識那只下蛋的母鴨。不像后來,讀書挑剔,專奔有名有姓的母鴨而去。萬家寶更是一個陌生得古怪的名字,雖然《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的劇本早早讀過,舞臺上的話劇也看過,而且印象深刻。及至后來知道這四部戲是曹禺寫的,曹禺就是萬家寶,萬家寶就是曹禺,竟然驚詫莫名。
曹禺的話劇實在是極好的,少年時讀覺得好,中年時再讀仍然覺得好。不像有些書,有些作家,放十年二十年再看,以為不過是哄孩子。23歲寫《雷雨》,25歲寫《日出》,26歲寫《原野》,30歲寫《北京人》,至此,中國現(xiàn)代戲劇的泰斗曹禺人生中最重要的四部作品全部完成。所謂天才作家,所謂年少英雄,無非如此。自古文章作手,有年少了了大未必佳者,有少時稚嫩老更成者,有連綿山峰時峰時壑者,曹禺屬于第一類。四峰矗立,他自己也是邁不過去的,近現(xiàn)代與其劇本相頡頏的,只有老舍。
舊中國,黑暗糜爛的地獄,以金八和閻王為代表的群鬼猙獰可怖,以魯大海和小東西為代表的草民鮮血淋漓。在上個世紀初葉,雄雞未唱,晨曦未露,是連魯迅、曹禺和老舍也看不到光明的,只隱隱約約覺察到日出之前混沌里的一絲希望,而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一個生來有些憂郁而暗澀的青年,孤獨,苦惱,茫然,左沖右突,找不到光明和出路,因為跟繼母看過許許多多的戲,京劇,梆子,落子,文明戲,一場場看下來,動起心思,于是寫起戲來,試圖在戲里找到苦悶的出口。不料戲是一個醬壇子,他掉了進去,融了進去,依然找不到出口,就像《日出》里陳白露的話,“太陽會升起來,黑暗也會留在后面,但太陽不是我們的。”曹禺這個人,我以為有點像《雷雨》里的周沖,有點像《日出》里的方達生,有點像《原野》里的仇虎,又有點像《北京人》里的曾霆,然而仔細一想想,又都不是,甚至全然不像,相似的只有痛苦。
曹禺在《日出》的跋文中,引用了《尚書·商書·湯誓》里的一句誓言,“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這誓言是毒誓,是血誓,是痛誓。好文章都是痛出來的,要么痛苦,要么痛快,要么既痛苦又痛快。魯迅寫《狂人日記》是痛苦,王勃寫《滕王閣序》是痛快,張岱寫《陶庵夢憶》是既痛苦又痛快。有人曾經(jīng)問曹禺,《雷雨》和《日出》哪一本比較好些,這自然如同問一個母親大兒子好還是小兒子好,問不出個所以然來,但曹禺為難半天,終于還是說,“比較說,我是喜歡《日出》的,因為它最令我痛苦。”其實他的四部曲無一不是痛苦的,寫的人痛苦,讀的人也覺得十二分壓抑的痛苦,有一團黑漆漆的郁結(jié)在胸臆里翻滾,像孫悟空在鐵扇公主的腸胃里翻滾,像新死的鬼在油鍋里被炸著翻滾,既不會隨一口氣呼出去,也不會隨一個屁放出去。然而即使如此痛苦,還是舍不得釋卷,悲劇有著巨大而可怕的力量,如同山螞蟥的吸盤,何況,四部曲寫得這樣好。好的著作如佳人,眉眼鼻子青絲胸臀都是好的,又像一團氣,渾元真氣,結(jié)構(gòu)章法對白獨白旁白,無一不好,說不出來的好。
見過曹禺出演《雷雨》周樸園的一張劇照,據(jù)說是演員因上火眼睛紅腫無法登臺他臨時披上戲衣替代的。照片上的周樸園,絕望而悲涼。是的,他寫的和演的都是毀滅。舊的毀滅了,新的才會從灰燼中萌芽。是的,他寫的也是萌芽。他寫的還是預(yù)言,原本有些懵懂的周沖、魯大海、方達生、仇虎、袁任敢、袁園、曾瑞貞、愫方他們,如新年的第一線陽光,破舊立新。
很喜歡關(guān)于曹禺的一個故事,說的是他生命最后的日子,病榻上還在認真讀《托爾斯泰評傳》一類的書,讀著讀著,忽然大叫,“我要寫出一個大東西才死,不然我不甘。我越讀托爾斯泰越難受。”他寫的戲是精彩絕倫的,他活到了86歲,歷經(jīng)晚清、民國和新中國,閱人閱事無數(shù),所演的人生的戲也是精彩的。
戲,本來是一種兵器,上古時部落先民祭祀山川鬼神,戴猛獸面具持“戲”而舞,于是有了戲。遠古的戲是圖騰崇拜,是迎神祈福,類似今天的儺戲和跑五猖。戲院,戲樓,戲臺,戲具,戲衣,戲人,戲子,戲法,倉才才才,臺才才才,人到中年迷上戲,人生的戲臺上卻只想清白如蔥蒜,不大愿意演戲了。
幼時縣城有劇團和劇院,少兒心性,不耐煩看戲,京戲、評戲、昆戲、黃梅戲、高腔戲都是上好的搖籃曲。往往隨了大人走好幾里山路進了戲院,先是小老鼠似的嘎吱嘎吱吃瓜子花生糖果,甫一吃完,瞌睡蟲立刻嗡嗡起來,蓋過了臺上的鑼鼓鐃鈸和念唱做打。尤其不樂意看話劇,寥寥幾個人在臺上走來走去白來白去的,直如聽道士念經(jīng)文,沒有小丑插科打諢,又沒有騎馬耍花槍打斗的戲份,枯索無味得很。
如今三十幾年過去了,縣劇團早已解散,劇院成了早點一條街,這幾年卻對戲上起心來。宋元南戲、元雜劇、明清傳奇、清代地方戲、近現(xiàn)代戲劇,莎士比亞、易卜生、契訶夫的劇本都讀過一些,看嚴鳳英和韓再芬演的黃梅戲《小辭店》眼睛會濕,在紹興沈園看越劇《沈園情》心如撕裂的帛,翻來覆去地看經(jīng)典元雜劇、湯顯祖的《臨川四夢》、老舍和曹禺的話劇、本土的青陽腔遺脈岳西高腔,如中魔怔。看戲,品戲,懂戲,修為之外,大概的確也是需要閱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