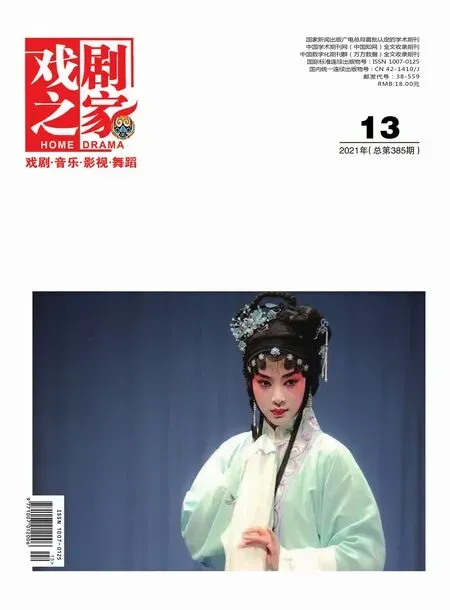淺析音樂劇《醉酒伴娘》上戲版的舞臺美術
曹婉琪
(上海戲劇學院 上海 201102)
音樂劇《醉酒伴娘》(The Drowsy Chaperone),由Bob Martin、Don McKellar編寫,Lisa Lambert、Greg Morrison作曲詞,于2006年上演并獲得2006年Tony獎全部13項提名,最終斬獲最佳編劇、最佳作曲、最佳女配角、最佳舞臺美術、最佳服裝設計5項大獎;以及獲得紐約戲劇委員會包括最佳音樂劇在內的六項大獎,至今仍持續上演。該劇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其“戲中戲”的獨特結構,滑稽的喜劇讓觀眾從頭笑到尾,憑借著旋律優美的音樂、令人叫絕的舞蹈表演、精美的舞臺美術成為音樂劇中尤為成功的作品之一。2019年4月6日,上海戲劇學院2015級的音樂劇畢業大戲即全新的《醉酒伴娘》,學生版的演繹獲得了肯定,也讓觀眾感受到了不一樣的音樂劇魅力。
一、劇本的創作特點

音樂劇《醉酒伴娘》主要講述了一個離異獨居的中年男子,又被稱為“Man in the chair”,即椅子上的人,與觀眾分享他最愛的音樂劇唱片《醉酒伴娘》的故事。隨著唱片的播放,劇中的人物依次登場,演繹了一場婚禮鬧劇——新郎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親吻了假扮成法國女孩的新娘,導致新娘宣布婚禮取消,最終新娘不僅原諒了新郎,還與劇中另外三對男女共同喜結伉儷。《醉酒伴娘》的故事是Happy Ending,但是劇中中年男子的生活卻充滿了憂傷,他在介紹中偶爾會透露他個人生活的一些方面,比如他失敗的婚姻,或許音樂劇創造的幻想世界成為了拯救他的一劑良藥。中年男子播放的唱片所演繹的音樂劇并未真實存在,而是劇作家杜撰的,此劇的背景被設定在1927年,以“富麗秀”為代表的美國音樂劇的萌芽時期。無論是情節設置、音樂曲風,還是表演樣式,都充滿了那個時代的特征。
“戲中戲”是本劇的特點之一,包括了兩個層面:一是中年男子的生活和音樂劇的故事這兩條并行線索;二是每一個扮演劇中人物的“演員”都帶著各自生活中的特點和人物關系在場上演出。椅子上的男人在舞臺上為整個節目提供了一個連續的解說,盡管他對于觀眾席來說處于“第四堵墻”的位置,是看不見的。在整個演出過程中,觀眾都在用一張舊唱片來聽音樂劇。隨著節目的繼續,他更多的個人生活通過他對音樂劇的思考得以展現,直到唱片結束時,他又一個人留在自己的公寓里——但他仍然保留著他長期以來鐘愛的唱片,每當他憂郁的時候,他都可以去聽。有一些重要的場景,比如唱片跳過,導致歌曲的最后一個音符和舞步被重復,直到坐在椅子上的人撞到了轉盤才恢復;臨近尾聲的一次“停電”導致舞臺變暗;以及在幕間休息的時候,男人懶散地坐在舞臺上,補充道:“他們把它拆了,然后建了一家酒店”,這是一個笑話,指的是該劇在馬奎斯劇院上演,這是萬豪馬奎斯建筑群的一部分,就建在摩洛斯科酒店所在地。他在音樂劇中場休息時換了唱片(表面上看是準備唱片,播放音樂劇的第二幕),然后離開舞臺“去洗手間”,這張新唱片實際上是同一位作曲家和作詞家創作的另一部音樂劇的第二幕,由許多相同的演員主演。一只夜鶯的口信令人聯想到中國帝王的服裝表演,表演者展示著陳腐的中國口音和幽默的語調等,無不顯示出“戲中戲”的趣味。
這樣的規定情境,為演員的角色塑造提供了相對自由的空間。為了營造中年男子的幻想世界,舞臺樣式被限定,人物性格單一,舞臺調度單一,但這種單一并非是負面的意義。“戲劇中的個別人物性格,也不像史詩中的那樣把全部民族特性的復合體都展現在我們面前,而是只展現與實現具體目的的動作有關的那一部分主體性格”。戲劇中的人物性格雖然單一,但會將人物這種相對單一的性格描繪得更加突出、更加豐盈。這就是黑格爾所說的,“一出劇詩的完美,在于不同的劇中人的性格的純粹性與規定性得到透徹的描繪,而且在于對人所以要如此行動的不同目的和興趣加以明白確切的表述。”體現人物單一性格的透徹性,以及人物行動目的的明確性,是戲劇塑造人物的一大優勢,也是戲劇作品重要的美學特征。《醉酒伴娘》運用了大量的隱喻手法,劇中的中年男子作為介紹者,在暫停唱片時往往會發表自己的看法,而這其中透露了男人的性格及其過去的生活、家庭關系。同時,劇本對于人在現代生活中的存在價值及家庭關系對人的影響做了深入的解讀與反思,這使得觀眾在走出劇場后對這個男子不是充滿憐憫,而是在他身上發現了自己的影子——發現了與他同樣的困惑與渴望,與角色共同經歷了一場自我探索的旅程。康斯坦布爾曾說“藝術是靠喚起記憶,而不是靠欺騙取悅于人”。當觀眾發現新的舞臺形象與自己平時的經歷形成一致時,就會獲得“辨認的特殊快感”,這正是人們精神活動的最大魅力之一。
二、關于舞臺美術
由于劇本的限定,舞臺在規定情境下呈現了一個逐漸被肢解的世界,即最后男人走進幻想的音樂劇世界。景片的樣式及舞臺整體造型基本參照百老匯版本的設計,在此基礎上有一些創新,加入了破舊的公寓、靈活的冰箱門等等。
《醉酒伴娘》的舞臺基本環境是椅子上的男人的家,假臺口后的假臺框以及后面的兩面景片墻組成了這個男人的家,墻面上到處張貼著老舊的海報,當唱片機開始放映時,男人帶著觀眾一同來觀看這部他最喜愛的音樂劇。男人的“現實生活”與唱片機中的另一時空不停地轉換,在布景上也要快速切換,舞臺在寫實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寫意的風格。布景設計有效地展現了演出的世界,展示了坐在椅子上的人的性格,并為節目設定了時間和地點。舞臺兩側的框架設計有效地使觀眾一踏進劇院,就直接進入了坐在椅子上的人的房間。幕布外的布景,不僅在整個演出過程中,甚至在演出開始之前,觀眾都能看到。茶壺、書等等,這些固定的物件都能顯示出它們是房間的一部分。在表演之前和介紹的時候,部分舞臺已經被暴露了。這樣一來,當幕布升起時,舞臺的主體部分就顯得格外突出,人們就不會疑惑舞臺的每一部分屬于哪個“世界”了。椅子上的男人的世界已經暴露出來了,在演出期間沒有什么新的或獨特的東西可以看。因此,這些景不會分散注意力,觀眾能夠集中觀看戲劇。旁邊的布景上也有許多關于百老匯演出的古色古香的海報。左邊和右邊的布景中都有昏昏欲睡的陪伴者的海報,暗示了這個坐在椅子上的男人對這部虛構的音樂劇的愛。其中有一些很容易辨認的著名音樂劇的海報,如《歌劇魅影》、《悲慘世界》、《西區故事》和《貓》。還有一些不是很有名的音樂劇,比如《俄克拉荷馬》、《屋頂上的小提琴手》和《樂師》,這些不太出名的音樂劇的海報也更加凸顯了坐在椅子上的人的性格。他是一個音樂劇愛好者,張貼各種音樂劇海報來裝飾。大多數海報都是幾十年前在百老匯演出的音樂劇。還有一個留聲機,這可能使這場演出看起來像是在很久以前舉行的,但又有一些較小的裝置表明,這場演出是在更近的時間。

《醉酒伴娘》的舞臺最大的特點是使用了多用途的裝置。在寫實主義的基礎上,追求舞臺美術的逼真,為觀眾營造出極易理解的舞臺空間和氛圍,這一切并不是通過舞臺裝置的頻繁轉換來完成的,而是運用具有靈活性和可變性的舞臺裝置,隨著劇情的變化,在此之上重新加以組合,或者在某些布景上進行增減,從而形成一個多用途的裝置。比如在阿多法出場時,男人從原本是一面墻的景片中拉出了一張床,場景隨之切換到臥室,“西班牙斗牛”情景即將上演。又比如第一場開幕后男人離開椅子,去拿身后燒開的熱水,隨后打開冰箱拿了一瓶冰水,之后演員從原本是冰箱的門里走了出來,依次亮相出場。這就像是劇中的人物進入了男人的“現實生活”,從冰箱里出現的那一刻,觀眾也隨之進入到音樂劇的世界之中。這樣的多用途裝置,能夠快速地在兩個時空中切換,創造夢境般的世界。當兩邊的臺框升高之后,男人的單調小公寓變成了一座巨大的宮殿,隨著景片切換,公寓又變成了一個美麗的花園。在第二幕結束后,幸福的新人結婚,百老匯原版是飛行員開著單引擎螺旋槳飛機從天而降,而在這次演出中,景片全部升上天空,全場是一個深空舞臺,飛機從后面隨著煙霧出現,給觀眾一種錯覺,仿佛真的在天空中飛行。舞美創新更加凸顯了百老匯的主題特色,突破了原本的舞臺設計。
在單調的舞臺調度上為角色塑造行動空間。燈光注重突出戲劇的表現力,在舞臺上把握空間的快速轉換,即男人的生活與唱片中的人物故事,引導觀眾鎖定舞臺焦點。因劇中人物臺詞與歌舞轉換較快,燈光也起到了烘托情境與氣氛的作用。
三、結語
音樂劇《醉酒伴娘》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為它符合當下的時代精神,那就是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呼喚與渴望。劇本雖講述了西方環境下的故事,卻與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并不相違,我們每個人都可能像坐在椅子上的男人一樣受困在自己的陰影之中無法自拔,我們都誠實地面對渴望,我們都需要愛與支持,就像椅子上的男人最終進入了自己期待的音樂劇世界一樣。但這是悲劇還是喜劇呢?我想《醉酒伴娘》的魅力就在于它把最后這個問題留給觀眾去思考。
注釋:
①黑格爾,《美學》3卷下,246頁。
②黑格爾,《小邏輯》,176頁。
③居其宏.音樂劇,我為你瘋狂:從百老匯到全世界[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