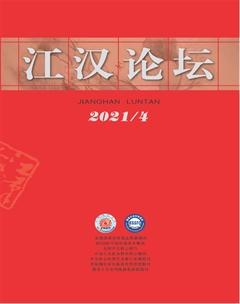治術、治體、道體
摘要:北宋儒家治理學說有一由治術、治體向道體深化的演進過程。宋初的國家治理偏向使用禮、法等治之“術”,但術的經驗性無法確保其普遍與正當。故而,在正當性方面,儒者以仁義道德作為治之“體”,引導治術。在普遍性方面,儒者將道德性之“體”上達于“道”,展開儒家治理理論的“道體”建構,以因應佛、道對治之術、治之體的挑戰。王安石、張載、二程是儒家“道體”理論肇端、深化與奠立過程中的標志性人物。
關鍵詞:禮;法;理;治術;治體;道體
中圖分類號:B244?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854X(2021)04-0055-06
傳統儒家政治理論是以道德介入治理的理論形態。在先秦時期,儒者多以具體情景論析倫理政治之合理性①。秦漢至宋以前,儒者仍秉承倫理型政治之傳統,然于佛道對儒家禮樂的消解,缺乏有效回應。至宋代,在因應佛道對儒家倫常的消解中,儒者將倫理型政治理論的道德內容融于對“道”的闡發之中,以奠定道德的形上地位,建立起“道學”關乎“政術”的新“范式”②,以道學之興廢,“乃天下安危、國家降替之所關系”③,建構以哲學的抽象理論關懷現實秩序的理論模式。然近百年的宋明儒學研究偏于哲學式的書寫,經過“首先是將道學從儒學中抽離出來,其次再將‘道體從道學中抽離出來”的兩度抽離④,儒學經世之旨掩于其中。故從宋儒對儒家倫理政治的道德內容之形上立法角度,重揭其以道學建構“道體”的治理之旨,是理解道學關乎政事的重要途徑。宋儒倫理政治理論形上化之建立過程,包含三個不斷演進的層次:第一,宋初諸儒重視治理之“術”的使用。治術主要是指經驗中的形下制度與儀節等,包括禮、法之制以及儒經所載治理方案、圣王治跡等內容。第二,在政治實踐中,宋初諸儒逐漸認識到“術”作為零散的、個別性的經驗匯整,須以善的引導來賦予其政治實踐中的合法性,這是治理理論第二層次的“治體”建構。治體是以“正心以正身”為起點的道德修養內容,主要為“治術”的推行賦予正當性⑤。第三,要回應佛道對道德性的治之體的消解,須向溝通天道性命的“道體”轉進,對作為“治體”的道德倫理冠以形上的立法,從而為儒教道德綱常確立至上的尊嚴。此為宋儒治理之學的第三個內容。本文旨在對北宋儒者的治理理論作一由治術、治體向道體演進的概觀,以還原被兩度“抽離”后的儒學旨趣。
一、治術肇端:北宋初期儒者的致治之方
北宋儒家治理思想與彼時政治長期失序的社會形勢聯系緊密,故能迅速廓除時亂、實現治績的治術為統治者優先看重。執政集團“講求治術”之切,甚至于“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⑥。在理論闡釋層面,宋初諸儒雖仍依循肇端于中唐古文經世之路徑,但逐漸轉向“重儒宗經”的宋學格局:針對宋初秩序狀況,宋初儒者更加聚焦于將治理之“術”與儒家經義結合。概言之,宋初諸儒的秩序學說,大致是回歸儒經,以重建社會、國家秩序的政治憲綱之“術”為要務。
中唐、五代以來,社會治理層面法制不興、“禮之失久”⑦,鑒于此,宋初治理尤重刑罰律令和禮樂制度兩方面之建設。一是對法治的重視,史載:“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此風行久,以至“士初試官,皆習律令。”(《宋史·刑法志》)二是儒家禮治亦參與到國家治理之中。晚唐至五代國家禮法喪亂,治理層面的典章制度多所散逸。至五代晚期,后周世宗始詔學官考證《三禮圖》,留意于禮樂之治,然彼時禮文儀注尚多“草創”,故“不能備一代之典”(《宋史·禮志》)。至宋立國,宋太祖制禮作樂,《新定三禮圖》得以頒行,成為扭轉禮失之后“名數法式,上下差違”⑧ 之保證。宋初治理所重在經驗性的、具備操作性的治之術主要表現于三個方面。
其一,法以及律令等成為宋初政治治理的重要內容。法律刑賞是高效的制度機制,相比柔性的禮樂教化,法令律條表現出強制性與確定性的特征。“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漢書·賈誼傳》)因而,“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⑨。在經邦治國的治效考量下,眾多儒士以習律學法為出仕之備。宋代儒家知識群體往往以“兼通律令之學”⑩ 為參政前提,其中熟稔律法者,甚至有“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及”{11}之情形。
其二,制度性的“禮”逐漸參與到社會治理之中。儒家政治觀念對刑、律、法、令等治之術的審慎傳統,促使在宋初“頗用重典”的法治氛圍中,習禮、重禮之呼聲也逐漸強烈。禮治的功能在于調和法治之嚴苛,使政治活動入情入理,所謂“立法之制嚴”,必以禮相調融,以使“用法之情恕”(《宋史·刑法志》)。在禮制建設方面,宋初頒行的《新定三禮圖》雖涉及到禮,但該書大致為考訂繪制禮經各式禮器、服飾之圖樣與圖說,非嚴格意義上闡釋禮學、記錄禮制的文本{12}。故重編禮書以施禮教的重任,就成為儒者參與治理的題中之義。北宋開寶年間,“四方漸平,民稍休息”(《宋史·禮志》),皇帝乃命執政詳訂禮書、以究禮制,以儒家的禮引導法治。在儒家治理理論中,政治治理中的道德動機,是使治術不淪為暴虐之政的保證。故儒家治術以禮治為第一義,律令刑法為第二義,以此規避執政者“無所畏憚,妄構刑獄”{13} 的政治風險。故至開寶時,太祖注意創制宋代禮樂之制,命儒臣“撰《開寶通禮》二百卷”,嗣后又修《通禮義纂》一百卷,且“自《通禮》之后,其制度儀注傳于有司者,殆數百篇”(《宋史·禮志》),由此確立了北宋社會治理中的禮治依據。
第三,宋初諸儒還將儒經中圣王致治之方與為政準則總結為治理策略。宋初,儒者對記載“先王治跡”的五經系統闡發最多,五經系統所載具體內容,大致為圣王為政的具體內容。在重建秩序的訴求下,宋初統治者汲汲以“學”求“治”,其“學”多為《五經》中的治之術。如《尚書》記錄圣王治跡和為政之方,多為策略的呈現{14},三禮中《周禮》、《儀禮》本就側重治理制度、修養規矩之闡述;《禮記》雖多為闡釋禮節儀式的內涵和義理,但亦不乏《曲禮》、《內則》、《冠義》、《昏義》等闡述制度之“術”的篇章。
總之,宋初執政者基于現實治效考量,以法、禮為治理首選。然而,從治之術運作過程的起點而言,社會的道德倫理狀況其實決定著制度機制,“是制度功能得以發生、制度有效性得以保證、制度本身的狀態可以調整的依據”{15}。因此,治術的制定和實施還面臨兩個問題:一是所制治術如何獲得普遍接受,以保障穩定性與可持續性,避免“人存政舉,人亡政熄”的窘境;二是在制定和實施治術時,是否合乎并貫徹儒家精神和價值,即宋初立法制禮,是否符合共同認可的“善”,同時實施法、禮之治的行為主體,是否基于這一“善”的精神來推行治術。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從學術上、理論上將治理之術向更優先的“治體”推進。
二、治體追尋:治術轉入治體的內在動力
承前所述,治術能否取得預期治效,首先面臨“術”在施行中是否具備正當性之考驗。宋初,儒家知識群體已經注意到治“術”背后需要有正當性的依據作為支撐,并開始有意識地探索建立更為根本的、關乎價值的道德形上之治“體”。如宋初胡瑗所倡“明體達用之學”,強調以“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體”引導“用”{16}。
宋初儒學治理理論中的體用之學,是以道德性的仁義為“體”,統攝技能性的治術之“用”。以胡瑗的“體用之學”為例。胡瑗的體用思想可由其“湖學”的治事齋、經義齋的分設體現出來。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所學為儒家仁義忠孝等知識,屬于作為治國理政之根本的“體”;治事齋則“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17},側重傳授經驗層面的治理技藝,屬于治術范圍之“用”。胡瑗的體用之分雖然凸顯了道德性的治之“體”之于技能性的治之“術”在政治實踐層面的優先地位,但該治“體”尚不具備超越之意,此言“體用”等同言事物之“本末”,尚屬于形下層面的分別,即未對所揭義理作抽象的闡釋,未將治理“人事”之“術”的正當性、合法性根據上達于天道。胡瑗主要是借天人相似之理發明人倫之序,模擬天道以論人事。他認為:“天地卑高既定,則人事萬物之情皆在其中”,如此人道“皆有貴賤高卑之位”,故人間社會綱常在法象天地的過程,實現“其分位”的秩序。若“卑不處卑,高不處高,上下錯亂”,則人倫貴賤尊卑、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就“不得其序”{18}。顯然,胡氏“全以天氣明其義”,通過天人比附論證人間秩序之合理性的闡釋方式,仍然停留在外部論證層面。
但不可否認,宋儒對治之體的闡明,不僅為作為用的治之術提供了道德理性與價值支撐,也開啟了北宋儒學由治理之“術”的形下設計向治理之“體”和治平之“理”的形上建構的推進。這一理論生發的內在動力大致基于以下兩點原因。
其一,作為經驗性的治之術,要從現實中經營一隅的成功,拓展至適用于廣闊疆域的治理,必須完成其理論上的普遍性證明。宋初諸儒正是在對治術合理性的反思中,意識到其理論上的不足,進而返回經典,力圖通過揭舉儒經中的思想內容引導治術之合理設計與有效推行。如胡瑗注意將內之“德”與外之“事”連接,他說:“以人事言之,則是圣賢、君子有中庸之德,發見于世之時也。夫君子之道,積于內則為中庸之德,施于外則為皇極之化。”{19} 劉彝謂其師說乃發明“圣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即強調作為內圣的道德性治之“體”,是成就外王之功勞的根據。孫覺重揭安定之旨言:“為道而不至于三王者,皆茍道也;為學而不至于圣人者,皆茍學也。”{20} 由此可見,北宋初期的儒家知識群體和政治家們,在申明秩序構建之合理性的過程中,無外乎于三代圣王(人)之“治”中稽求圣人治理之“學”,以其作為治“體”為政治實踐中的治“術”賦予正當性與普遍性。
其二,治“體”的建立亦有現實政治實踐之考量。術的推行須以體用、本末之條理,來避免彼此抵牾、掣肘,確保其治效。眾所周知,傳統儒學中禮優先于法、刑、律等治術,但宋初禮、法相提并重,法條律令與禮樂制度并行,形成禮法交織、不分伯仲的治理結構。當禮法治術在處理同一事件上產生分歧時,往往因雙方支持者聚訟不休、難以決斷而延誤政事。如在仁宗朝,“每朝廷有大事,議論紛然,累日而不決。司馬君實與范景仁號為至相得者,鐘律一事,亦論難數十而不厭”{21}。再如神宗時期的“登州阿云案”,從定案到減刑,再到朝議至再定罪,前后延宕十來年,成為影響政治集團斗爭的重要事件。原因即在于這一事件既關乎禮治上夫婦地位之原則,也關乎法治上對婚姻關系確立與否的規定。同一案件中的人、事,投射于持不同觀念之執政者,往往導向極為相反的判決。所以,為避免治理的低效,一要規定禮、法先后順序,二要在制定、頒行中達成普遍的共識。基于此,從經驗性的治之“術”進展為較為普遍認可的道德性的治之“體”,成為現實的治理需要。
總之,雖宋初治理策略偏于治之“術”,但“術”之有效性又必然需要理念上的支撐,因此建構治之“體”的理論訴求就產生了。宋初諸儒已開建構“治體”之端緒,其“雖未能深于圣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是得圣人個意思”{22}。此語雖有專指,然實可以之勾勒宋初諸儒尋求治“體”的基本情狀。
三、道體確立:儒家道德形上學的建立
治“體”作為引導治“術”的德性規定,體現著儒學的價值層面對制度實踐層面的調控。因此,價值層面本身的正當與否不僅關系著制度的有效性,更關系到以“學”求“治”的目的能否實現。而從理論合法性意義上看,作為治之體的儒家道德切入現實政治,要確立穩固的觀念統治地位,必須積極回應漢末以降佛、道二教大熾造成的思想層面的嚴峻挑戰。
(一)道體建構的動力
第一,佛、道空無、寂滅觀念,對士大夫維持積極昂揚的精神面貌構成極大消解。佛道之說興于漢唐,至宋,其盛尤勝前代,特別是佛教“人人談之,彌漫滔天,其害無涯”{23}。神宗曾質言其害:“使釋、老之說行,則人不務為功名,一切偷惰,則天下何由治?”{24} 一旦佛道空、無之說泛濫于庶眾的觀念世界,世間的一切積極努力都被視為虛幻而無意義,那么國家社會各項事業都無法推進。故宋儒深切意識到必須旗幟鮮明地抵斥佛老,昌明儒者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此一時代之學人,基本要求非作‘逃遁,而是作‘承擔。”{25}
第二,佛、道之說對儒家名教綱常的價值具有消解作用。從教義看,佛教之止、觀法門,道教之心齋、齊物我諸說,強調個體在精神上的超越和自足。這種超越表現為對經驗世界的疏遠甚至否定,所謂“絕仁棄義”“絕圣棄智”(《老子》第十九章)。佛家認為,人間社會的“相”“皆由妄念而起”,“若離念,化念歸心,則一切法本質上即是空如平等,只是一真心常在,不生不滅”{26}。其以佛性為唯一的真實,而以人生為虛幻和亟待解脫的苦海,采取背離社會生活以求生命根本的覺解方式。而道教的長生久視之說,同樣容易導向拋棄人道之追求。為此,儒者即以佛、老理論割裂形上與形下兩個層面、致使“體用殊絕”之弊流行作為標靶,提出嚴厲批評。
第三,晚唐、五代亂世導致社會治理嚴重失序,政治集團迫切需要有利于秩序建構的思想理論作為指導。而傳統儒學理論思辨不足,未能給予政治統治秩序之合法性更為深入、更高層次的保障。正是在被迫回應佛、老之學的過程中,宋儒開始反思儒家現有關于治之術和治之體理論的形下性,進而尋求為其建構一個更為根本、可靠的形上根基,以便為秩序的實現奠立至上的道義根據,即關于“天道性命”之“道體”建設。
(二)道體建構的過程
王安石首倡“道德性命之學”,以闡釋道德性命的形上地位。他說:“萬物待是而后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27} 天作為萬物生化的根本,道作為萬物運化的機制,二者所具備的至上地位,足以確保道德的尊嚴。王安石引莊子“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論證作為治之“體”的道德、仁義引導作為治之“術”的“分守、形名、因任、賞罰”,并由之構成層次清晰的治理體系。
王安石指出,“天”是道德仁義之“體”至上地位的保證,“天”的至上性支撐著道德的尊嚴。然而后世學人卻懸置“天”的道德義,將“天”降格為“不知其幾千萬里”的“彼蒼蒼而大者”。在他看來,必須使國家之治的扎實根基落實于將道德上達于“天”的觀念建構。他說:“古之言道德所自出而不屬之天者,未之有也。”{28} 他正是通過追溯道德“所自出”于天,來確立其至上性,以此作為解決道德形上立法之課題,從而避免道德與人倫為異教所敗壞。
對于當時思想界言道德則“窈冥而不可考”、言形名則“守物誦數”,至體用二分之流弊,王安石以“道之體”統攝“道之用”和“道之用”呈現“道之體”來解決。他說:“道有體有用。體者,元氣之不動;用者,沖氣運行于天地之間”{29},此體用即有無、本末,有無之道,皆出于道,而“道之本,出于沖虛杳眇之際,而其末也,散于形名度數之間”{30}。意思就是,道的“不動”之體與“形名度數”之用,分別涉及總括萬物與觀照現實之治的內容,二者統一于道。
然而王安石闡釋道德心性摻雜佛、道觀念,其性說經歷由“性善”、“性可善可惡”,到以佛教之“空”釋性,謂“性無善惡”,最終被視為“出于私意之鑿”,“特竊取釋氏之近似者”{31}。同時,王安石對“形名度數”的治術偏重實用考量,“以適用為本”,若“不適用,非所以為器也”{32},強調“非有則無以見無,非無則無以出有”{33},即要通過“用”來展現“體”,使“體”具有現實針對性,以避免“體”流于空泛無實。這實際上將“用”的重要性等同于“體”,導致體用“二本”,因而并未真正完成天道與性命、內圣與外王的貫通。其學主要是為其變法奠立合理的知識體系,故偏重闡發治之術,于天道性命之學僅開了端緒。
王安石新學因其作為推行政治改革的理論依據而招致諸多批評。然而就其對儒學道德形上學發展的推動來看,由于其學被納入學官,在當時產生了廣泛影響。與此同時,在推動儒學道德形上體系建構方面,也展開了另一路向。張載以氣闡發“天道”,溯性命之源;二程將“天道”與人道的“性命”學說貫通,把人道的道德內容上達天道本體,從理論上實現了治理學說由“治術”“治體”向“道體”的轉進,最終完成“道體”建構{34}。可以說,王安石、張載、二程是儒家“道體”理論肇端、深化與奠立過程中的標桿。
天道論建構主要是由張載闡釋的氣化宇宙論來實現的。在橫渠之前,周敦頤、邵雍也都進行了宇宙論的闡釋,但周敦頤言之過簡、闡釋未豐;邵雍則純以數的規律性變化,闡發宇宙的演變奧秘,偏離了儒學心性之傳統。而橫渠則通過其氣化宇宙論,使理學煥然一新{35},豐富了儒家治理之學的“道體”內涵。張載反對將“道學”與“政術”裂為“二事”,注意將具體經驗性治術關聯于自然天道,思考如何為道德立法,以給“治術”“治體”奠定形上根基。其宇宙學說旨在呈現人間秩序所以可能的“天道”根據。他以“氣”立本,通過解釋“氣”的聚散變化,建立起宇宙生成和宇宙本體的哲學體系,以此論證人間秩序及其合理性。二程指出:“橫渠言氣,自是橫渠作用,立標以明道。”{36}此即標示了“氣”在張載哲學體系中的獨特作用。
一方面,張載以“太虛”之“氣”的聚散解釋整個世界的生成和消逝,以此否定佛、道虛無之說,為儒家名教留下地盤。他指出:“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在他看來,通過對“虛”氣的特性規定,“推本”萬物“所從來”,便能使佛之以實為空、以空為真,道之以無為體、無能生有的“蔽于诐而陷于淫”的理論性質暴露出來{37}。由“虛空即氣”知太虛作為氣之本初狀態,是無形無狀的,而萬物則是處在聚散變化中的氣之“客形”,故“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38}。氣 “往來”于有形與無形之間,但無論如何變化,萬物生滅無非是氣的聚散,故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即是說,整個世間萬象均為氣的聚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39}。通過討論介于隱顯之間的氣,張載解釋了萬物的存在情形,抵斥了佛、道異端的空無論,維護了儒家倫理及其禮樂秩序的現實合理性。
另一方面,通過氣化宇宙生成論的建構,張載將儒家倫理上達于天,確立了人道的至上地位。以“氣”論事的思想傳統,可遠溯西周伯陽父以氣釋地震,但此氣屬形氣,非論性之氣。由春秋戰國至漢代,“氣”仍多指“形氣”,時兼及“精氣”,亦偏于物質性的涵義。魏晉以“有無”言氣,受到佛、道影響,其涵義逐漸向生命本原、道德修養境界等發展,氣的道德性得以凸顯{40}。而宋代理學之氣區別于境界之氣,亦非單言形氣或性氣。其中,張載將“形氣”與“性氣”合于一氣,指出“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41}。太虛之氣具有“湛一”“無形”之特性,“氣本之虛則湛[一]無形”{42},此特性為構成“性”的依據,所謂“言湛然純一而不雜者,氣之本體也,即所謂性也”{43}。由虛聚而氣,由氣聚而為人,人稟受虛的“湛一”純粹之性,此即儒家所言良善之“性”{44}。將氣與性連接是張載的發明,他解決了“性”的根源問題與道德賦義,從而奠定了倫理政治中的道德仁義之至上性。
從氣稟來論證人性的根基,不僅是橫渠對性善論的價值認可,而且還透過論證人性的平等,暗示在社會治理上,可以由儒家溫和的禮樂之治,來實現整個社群的教化與秩序。可見,張載以氣發明天道來闡釋心性根源,為天道與性命貫通奠定了基礎。但氣化宇宙論僅完成了天道下貫人道的準備,天道與人道之間的溝通,“形”與“性”的相輔相成,則尚待詳析。其理論中的核心概念“虛”,仍有未明之處。二程否定橫渠“以清虛一大為天道”,批評“虛”氣“乃以器言而非道”,認為“虛”猶未切實于“道體”{45}。二程將“虛”僅作形下之“形氣”理解,固然是對其“性氣”內涵之忽視。但對“清虛一大”形下性的批評,的確點出橫渠在“道體”建構中雜性、形為一體的二本傾向。在二程看來,某一對象不可能兼為本體和構成萬物的質料,不能同時既為“形而上者”又為“形而下者”。透過否定“虛”的形下性和物質性,二程將“虛”的“性氣”特質剝離出來作為“理”,指出“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于理者”{46},將“太虛”的“神體”性質和物質性質剖分為“理”與“氣”,從而由張載之“虛”進展至二程之“理”。
在繼承、批判前儒時彥的基礎上,二程進一步完善其“理”學思想,建構北宋儒家治理之學的道體內容。正統的理學,直到二程才基本奠定學術規模。正是通過將心性與禮上達于天,二程奠定了形下制度之禮與道德心性之理的至上性,將治理理論中制度性的治術、道德仁義性的治體提升至天道層面的道體,從而確立道德的本體性,恢復倫理政治之道德的尊嚴。這主要由三個層面來完成:第一,二程奠定“理”的形上本體地位,指出“理,當然者,天也”;第二,二程還將“理”與“心”、“性”互詮,視“人倫者,天理也”{47};第三,二程將“理”與“禮”予以互釋,對儒經中“禮者,理也”的舊說加以發明。二程以“天理”作為儒家治理理論的“道體”內容,從而完成了儒家倫理政治的道德內容的形上立法。
四、余論
宋儒治世理論是在治術、治體而逐漸深入至道體這一過程中完成的。宋初諸儒雖已展開對治之“理”的討論,但側重于術,朱子謂此時雖已知崇禮義、尊經術,然諸儒“說未透在”{48}。此即言宋初諸儒雖于經義有所發明,然未闡明治理之“道”。至北宋中期王安石首倡“道德性命之學”后,始切入倫理政治中道德立法之課題,經張載完成“天道”理論的建構、二程將“心性”與“天道”融貫,才真正實現北宋治理理論的歷史書寫。不過,作為“道體”的“天理”論,如何處理好形下之“禮”與形上之“理”間的平衡,是值得進一步省思的:既然“天理”至高無上,且構成對形下世界的統攝,理論上學人只須循天理,即可成形用。但是事實上,可能由于將天理定調過高,忽視世俗世界的禮治與習俗,導致學人苦心極力以求天理,卻學愈深而用愈薄,反而又墮入空疏寂滅的境地{49}。故從儒學經世傳統審視“天理”,此“理”若無形下之“禮”“法”等充實,則易流于概念分析,與其所批評的空疏無用無別。這樣一來,又須回到王安石強調的以“用”充實“體”,否則只言體而疏于用,終至體用兩失之。
注釋:
① 先秦儒家道德倫理之論證,多采取某一具體情景來論證道德的合理性與普遍性,如《孟子·梁惠王上》“以羊易牛”、《告子上》言“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等,這些論析均基于某種特殊“情景”,儒家倫理政治的道德普遍性之論證尚未建立。
②{37}{38}{39}{41}{42} 張載:《張載集》,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349、8、8、7、9、10頁。
③ 李心傳:《道命錄·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頁。
④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8頁。
⑤ 可參任鋒:《中國政學傳統中的治體論:基于歷史脈絡的考察》,《學海》,2007年第5期。另參考《立國思想家與治體代興·導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
⑥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15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903頁。
⑦《歐陽修全集》第1冊,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378頁。
⑧ 聶崇義:《新定三禮圖》卷20,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12頁。
⑨{13} 《包拯集校注》,黃山書社1999年版,第98、214頁。
⑩{27}{28} 《王安石全集》第6冊,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935、1210、1211頁。
{11} 《曾鞏集·行狀》,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792頁。
{12} 張文昌:《制禮以教天下——唐宋禮書與國家社會》,臺大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138—139頁。
{14} 宋太祖讀《堯典》時言:“堯舜之世,四兇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在于執政“有意于刑措”,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第2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37頁。
{15} 任劍濤:《道德理想主義與倫理中心主義》,東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2頁。
{16} 黃宗羲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第1冊,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5頁。
{17}{36}《朱子全書》第1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319頁。
{18}{19} 胡瑗:《周易口義》,《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51、176頁。
{20} 孫覺:《孫氏春秋經解》,《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頁。
{21} 陳傅良:《永嘉先生八面鋒》卷6,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42頁。
{22}《朱子全書》第1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69頁。
{23}{45}{46}{47} 《二程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118、66、394頁。
{24} 《楊時集》,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124頁。
{25}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3卷(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頁。
{26}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99頁。
{29}{30}{33} 《王安石全集》第4冊,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65、155、155頁。
{31} 《張栻集》,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1053頁。
{32}《王安石全集》第7冊,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369頁。
{34} 黃震指出:“本朝之治,遠追唐虞,以理學為之根柢也。義理之學,獨盛本朝,以程先生(即二程)為之宗師也”,即言北宋治理理論的治體追尋直至二程而精微。見《黃震全集》第7冊,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0頁。
{35} 陳榮捷:《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歷史》,“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印行2004年版,第45頁。
{40} 參考葛榮晉:《中國哲學范疇導論》,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47—52頁。
{43} 轉引自林樂昌:《正蒙合校集釋》,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323頁。
{44} 陳來:《宋明理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73—74頁。
{48}《朱子全書》第1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020頁。
{49} 如蘇軾批評言:“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于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見《蘇軾文集》第4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392頁。
作者簡介:張子峻,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博士后研究人員,湖南長沙,410006。
(責任編輯? 胡?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