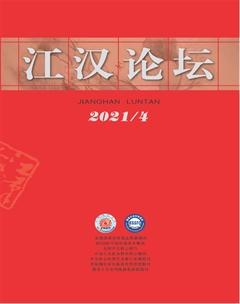“感傷的詩”和“素樸的詩”
摘要:“白話詩”之后,“抒情”成為新詩的核心問題。“主情論者”大都認為詩歌來自“迫切的人的情感”,然而,他們對“情”的理解卻存在著差異,由此也引發了對于抒情與理性、道德、技藝等關系的論爭,這些問題都直接與抒情中的感傷主義相關。正是由于認識到詩歌的情感來自“迫切的”生理沖動,容易引發精神上的熱病,周作人選擇將“并不迫切”的日常事物納入寫作的視野,通過客觀的方式傳遞一種寧靜的人生哲學。雖然周作人的“素樸的詩”祛除了感傷主義的濫情和自我傷害,但因其“返古”卻不能代表新詩的發展方向。早期新詩或躁動或冷靜,都還不具備將情感和情緒轉化為具有現代性的詩歌藝術的能力。
關鍵詞:早期新詩;抒情;感傷;身體;周作人
中圖分類號:I206.6?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854X(2021)04-0066-07
按通常的看法,詩歌和抒情幾乎是同義詞,沒有抒情,詩不成其為詩。在新詩中,這種看法仍然被大多數人所贊同。“白話詩”作為新詩的開端,它的偏于寫實、說理是對僵化的古典抒情模式的反叛,然而它的弊端卻為郭沫若、周作人、朱自清等人所詬病。中國詩歌有著深厚悠久的抒情傳統,所謂“言志緣情”,同時,18世紀末到19世紀上半葉的西方浪漫主義詩歌也在新詩中發生著影響,新詩回歸抒情勢所必然。新詩的抒情是逐步確立并成型的,朱自清在回顧早期新詩的發展時說,“民國十四年以來,詩才專向抒情方面發展”①,朱自清在這里指的是到了新月派詩歌才真正有了“理想的抒情”②,這樣看來,1920年代初期是抒情逐漸成形的階段,在這一過程當中,新詩的抒情特質是如何確立的?早期新詩的寫作暴露出哪些問題?相對于古典詩歌,它是如何認知“現代的抒情”的?這些問題都需要到歷史中去尋找答案。王德威指出:“在革命、啟蒙之外,‘抒情代表中國文學現代性——尤其是現代主體建構——的又一面向。”③ 如果說現代的主體通過抒情得以呈現是考察新詩現代性的重要標準,那么,在新詩抒情問題上,這一現代的主體又應該具有怎樣的品質?本文主要以白話詩以后的新詩(1920年代初期)在抒情問題上呈現出來的兩種不同思路為對象進行考察,嘗試對上述問題進行回答。
一、“感傷的詩”與“生理的沖動”
作為一種新的文體形式,新詩的性質和文體規范在1920年代初尚未成形,因而理論的建設就顯得尤為重要。在白話詩的寫實說理傾向之后,周作人、郭沫若、康白情等都發表了“主情論”,并逐步確立了新詩的抒情性質。“主情論”并非鐵板一塊,以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兒》、汪靜之的《蕙的風》以及湖畔詩社的四人合集《湖畔》等早期新詩集為對象,關于新詩抒情問題的討論非常熱烈,并且當時的探討已初步覆蓋了新詩在其后發展中所遭遇的與抒情相關的各種問題,而其核心就是對感傷主義的批評和反思,圍繞“抒情”的討論以及對寫作中所暴露的“感傷”的批評在1920年代初期主要體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在確立新詩的抒情性質的過程中,大多數“主情論者”都認為情感具有自發性,詩歌所抒之“情”是一種不吐不快的感性的“沖動”,這就與理性劃出了涇渭分明的界限,這樣的認知是與“五四”個性解放的時代語境相呼應的,但早期抒情詩的情感的淺薄和泛濫,以及感傷主義的流行也正是由這種抒情認知所導致的。
作為新詩早期的實踐者,俞平伯說,詩應以“主觀的情緒想象做骨子”,“凡做詩底動機大都是一種情感或是一種情緒,智慧思想似乎不重要。我們從心理學上,曉得這種心靈過程是強烈的,沖動的,一瞬的。若加以清切的注意或反省,或雜以外來的欲望,便把動機底本身消滅了。所以要做詩,只須順著動機,很熱速自然的把它寫出來,萬不可使從知識或習慣上得來的‘主義‘成見,占據我們底認識中心”。④ 1922年俞平伯的詩集《冬夜》和康白情的《草兒》由亞東圖書館出版,這是在《嘗試集》《女神》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兩本新詩集。俞平伯在“自序”中稱“詩底心正是人底心,詩底聲音正是人底聲音”,朱自清給俞平伯所作的“序”也稱贊其有“迫切的人的情感”,而康白情在“自序”中則同樣說他的詩是“自由吐出心里的東西”,“我不過剪裁時代的東西,表個人的沖動罷了”。
以這樣的認知為標準,理性在早期抒情詩中被排斥。創造社的成仿吾在《詩之防御戰》一文中批評包括胡適在內的白話新詩“中了理智的毒”⑤。白話詩之后,胡適就拋棄了說理,他甚至批評俞平伯的《冬夜》并非如詩人自己所倡導的那樣是主情的,而是偏于智性和說理:“平伯最長于描寫,但他偏喜歡說理;他本可以作詩,但他偏要想兼作哲學家。”⑥ 如果說俞平伯、胡適在當時都是“主情論”的提倡者,那么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認知上的差距,其原因要么是“情”的標準對于胡適、俞平伯而言并不相同,要么如胡適所說,俞平伯的理論與實踐之間確實存在差距。
早期新詩普遍認為抒情詩之“情”是一種感性的、自發的情感,情感的沖動來自于人的本性,這是詩歌原始的發生機制,它在西方浪漫主義詩歌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查爾斯·泰勒認為相對于古代人將本性具體化為秩序,“現代觀點贊同把本性作為正確沖動或情感的根源。所以,不是在秩序觀中,而是在體驗健全的內部沖動中,我們遇到了作為典范和核心的本性”⑦。西方浪漫主義詩歌以自我為主體的情感表達來自于對人的“本性”的認同,而這種“本性”即是身體性的。同樣,與“情”作為早期新詩的寫作倫理相呼應,“沖動”一詞在當時常被用來描述情感或情緒的狀態,它不僅是心理的,同時也是生理的,具有即發性、瞬時性、直接性的特征,這樣的詩歌很容易感染讀者,引起讀者在情感、情緒上的共鳴,但這種“感染”也具有瞬時性的特點。
聞一多對《冬夜》《草兒》的批評,同樣基于對感性情感的肯定、對理性情感的排斥,他明確批評俞平伯的一些詩作缺乏情感和想象:“大部分的情感是用理智底方法強造的,所以是第二流底情感。”在聞一多看來,由觀念和思想發生的情感是第二流的情感,所謂“觀念和思想”主要是指“五四”以來的人本主義思潮,而第一流的情感是“與熱情比較為直接地倚賴于感覺的情感”⑧。正是第一流的情感才能產生詩歌的藝術,第二流的情感實際上并非詩歌所需要的“情感”,聞一多敏銳地區分出不同情感的差異,感性的情感是具體的、身體性的情感,而非抽象的、精神性的情感。按現代觀念來看,雖然聞一多反對理性并不可取,但他認識到“情”也可能出自理性,這一洞見在當時超越了很多人。
隨著時代語境和寫作觀念的變化,理性、思想在后來逐漸被重視。“湖畔”詩人汪靜之后來就認識到了“思想”對于抒情的意義:“我們知道有許多詩僅以情感為目的,僅以情感為主旨,也可以成為佳作,但大多數的好詩卻都是含有思想的,而高深偉大的作品則非含有高深的思想不可。”⑨ 汪靜之認為“思想”一詞可以以“真理”代之,并稱之為“情感的真理”,而抒情與智性的結合也正是40年代現代主義詩歌的重要特征。
第二,早期抒情詩及一些相關批評注重的是“情”的內容,并沒有在意如何抒情,沒有認識到抒情的問題最終是一個語言問題。感傷的抒情往往缺乏高明的技藝,同時由于這種情感來自“生理的沖動”,如果在語言上任其傾瀉、缺乏升華,就易將讀者的注意力引向道德問題上,因而偏離詩歌作為一門語言藝術應該具有的指向。
早期新詩集所表現出來的技藝缺失的問題,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當時胡適等人更看重的是其內容、風格所具有的時代價值。在新舊文學之爭中,胡適特別強調經驗、情感之“新鮮”“真實”的重要意義,他批評了俞平伯詩歌的理性,卻對康白情的《草兒》、汪靜之的《蕙的風》所表現出來的感性予以積極支持。胡適稱康白情的詩“富于創作力,富于新鮮味兒,很可愛的”⑩。汪靜之的《蕙的風》出版時,胡適寫序對其進行贊譽,認為其新鮮的氣息更甚于早期白話詩人的代表俞平伯和康白情:“他的詩有時未免有些稚氣,然而稚氣究竟遠勝于暮氣;他的詩有時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遠勝于晦澀。況且稚氣總是充滿著一種新鮮風味,往往有我們自命‘老氣的人萬想不到的新鮮風味。”{11} 在胡適看來,新題材、新經驗對于新詩而言才是最重要的,真誠坦率正是新詩區別于舊詩的重要特征。
在西方浪漫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情感的作用不僅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自然主義的情感可以與公民道德相結合,并通過這一情感的紐帶將社會聯結在一起,“情感被認為是自然的,它們團結人,而不是孤立人的;它們作為一種公共資源而被所有人享用。公開表達強烈的情感,不但不會引發尷尬,還是慷慨真誠的象征,也是社會聯系的象征”{12}。與此相似,在對待早期新詩的情感表達上,一些詩人和詩歌批評家常常從時代的角度認識新詩的情感價值。汪靜之《蕙的風》的出版引發了有關文藝與道德關系問題的論爭,以胡夢華《讀了〈蕙的風〉以后》一文為代表,指責汪靜之的詩做得“多么輕薄,多么墮落”{13}。針對此種言論,周作人發表《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學》、魯迅發表《反對“含淚”的批評家》對胡夢華等的攻擊予以反擊,肯定《蕙的風》的反封建性質,它的自然、清新正體現了新文學的風貌,周氏兄弟的支持立足于時代變革的語境,而并非基于對新詩藝術的考量,這也間接說明了感傷的抒情在特定時期的積極意義之所在。
雖說新詩的本職在抒情,但并非“有情”就是好詩。有高明的詩藝,才有美好的情感。《蕙的風》在技藝上的殘缺就引發了有關文藝與道德關系的論爭。與胡適、周作人、魯迅不同,聞一多、梁實秋不是基于思想的立場而是基于詩歌藝術的立場支持胡夢華對《蕙的風》的批評:“這本詩不是詩。描寫戀愛是合法的,只看藝術手腕如何。”{14}? 在給梁實秋的信中聞一多激烈地鄙薄道:“《蕙的風》只可以掛在‘一師校第二廁所底墻上給沒帶草紙的人救急。實秋!便是我也要罵他誨淫。與其作有情感的這樣的詩,不如作沒情感的《未來之花園》。但我并不是罵他誨淫,我罵他只誨淫而無詩。淫不是不可誨的,淫不是必待誨而后有的。作詩是作詩,沒有詩而只有淫,自然是批評家所不許的。”{15}在聞一多看來,情愛的題材沒有詩藝的保障就會變成道德的問題,愛情不是不能寫,但是其情感的表達需要從藝術出發。聞一多一語洞穿,感情的淺薄不僅是內容問題也是技藝問題,語言缺乏表現力和情感輕浮互為表里,聞一多的批評“注意的是詩的藝術,詩的想象,詩的情感”{16},而感傷的抒情存在的問題就在于不注重詩藝對情感的規約,導致“情感太薄弱,想象太膚淺”{17}。
第三,1920年代的抒情詩很多都囿于個人的情感,缺乏時代精神和深厚的現實基礎。《湖畔》作為《蕙的風》的姊妹篇,其無病呻吟的問題在文學研究會的刊物《文學旬刊》上被批評,其參照對象是徐玉諾具有現實感的詩歌。文研會的鄭振鐸等人提倡“血和淚的文學”,也就意味著新詩需要對個人化的狹小詩意進行反叛,而現實的人生如何進入詩歌,“為人生”與“為藝術”是否能獲得一種平衡也成為新詩發展中受到關注的問題。
雖然出于對新生事物的支持,朱自清在給《蕙的風》作的“序”中認為汪靜之的詩勝在“清新”、“質直”、“多是性靈的流露”,同樣因其經驗之新,他也贊譽“湖畔詩派”的四人合集《湖畔》“帶著清新和纏綿底風格”,不過,朱自清也意識到其中存在的問題,他稱其“只有感傷而無憤激”{18},這意味著“感傷主義”作為一個抒情問題被提了出來。朱自清在他同年寫作的《毀滅》一詩中描述了感傷主義飄渺虛幻、柔弱無力的特征:
這好看的呀!
那好聽的呀!
聞著的是濃濃的香,
嘗著的是膩膩的味;
況手所觸的,
身所依的,
都是滑澤的,
都是松軟的!
靡靡然!
朱自清直接表達了他對“感傷”的抵制態度,在這首詩的最后,朱自清說要“擺脫掉糾纏,/還原了一個平平常常的我!/從此我不再仰望看青天,/不再低頭看白水,/只謹慎著我雙雙的腳步;/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腳印!”“我寧愿回我的故鄉”——詩人的“故鄉”便是“現實”,新詩不能只制造詩意的幻覺。
因此,早期新詩有關抒情與理性、抒情與技藝、抒情與道德等的討論都與感傷主義有關。感傷的抒情是一種語言現象,也是一種身體現象,“由疾病引發的不安的、熱烈的主體形象,遍布于1920年代普遍感傷、浪漫的新詩寫作中,焦灼的、羸弱的乃至瘋狂的身體感受,也成為現代文學經驗發生的前提之一”{19}。尤其是在情感的初始形態中,“情”往往是身體性的,它帶有即時性、突發性的特征,直接而未經沉淀的情感會包含不受理性控制的夸大、虛飾的成分。進而言之,來自于身體的沖動在轉換為情感的過程中,會因“沖動”的熱力讓情感無限膨脹,也會因在現實中的挫敗而使情感變得柔弱,后者往往表現為感傷主義的抒情,“感傷性是一種情感過剩的形式,因此是一種倫理和修辭的缺陷,它在讀者和詩人身上均可發現,顯示的是自我憐憫,缺乏成熟的情感控制”{20}。從語言的角度來看,“感傷與非感傷之間的一個有用區分在于,人們不依賴于情感表達或激發的強度與類型來判斷感傷與否,而是把那些在再現的細節中未能進行鮮明的語言表達和有力的實現、只是以平凡方式和陳詞濫調來呈現情感才稱之為‘感傷性”{21}。情感的過剩、語言的貧乏都是感傷性的標配,即便是它從真實的情感出發,但卻被它的夸飾及其導致的無力所稀釋。雖然感傷主義來自身體的沖動,但其所表達的情感卻由于最終離開了身體而趨于夸張和抽象,現代的主體只有在具體的表達中才能獲得一種真實性。
對感傷主義的抵制和清除伴隨著新詩的發展過程,隨著意識上的警惕,并借助于理性的精神、詩藝的發展和現實的力量,新詩中的感傷主義情緒得到了有效遏制。1936年金克木在《論中國新詩的新途徑》{22} 一文中反對抒情詩的“賦得”和“即興偶成”,“不虛發,不輕發,不妄發,不發而不可收”,情感要“真”和“深”。他還指出,中國古詩以抒情為主,但新詩需要表達新的感情,“若情并不新,只足證明作詩者是生錯了時代的古人,于詩無干”。隨著現代主義詩歌的興起,對抒情中的感傷主義無論在觀念上還是在技藝上都有了更有效的抵制方式,卞之琳的《讀詩與寫詩》、朱光潛的《文學上的低級趣味》、袁可嘉的《漫談感傷》、李廣田的《論傷感》等文都對感傷主義進行了清理和反思,在西方現代詩歌的影響下,尋求客觀對應物、戲劇化也成為遏制感傷的現代思路。
感傷主義不僅存在于個人化的詩歌寫作中,也存在于政治化的詩歌寫作中。在《論現代詩中的政治感傷性》一文中,袁可嘉認為不僅存在情緒的感傷,還存在著觀念的感傷,他批評的對象是40年代的“文藝大眾化”運動。袁可嘉的觀點并不意味著現代主義詩歌對現實的排斥,恰恰相反,對現實的深入、歷史意識的強化正是以奧登為代表的西方現代詩歌的追求方向,這樣的現實精神也影響了新詩,40年代的現代主義詩人并沒有將藝術和現實對立起來,而是“追求一個現實、象征、玄學的綜合傳統”{23}。李廣田也認為要避免感傷,除了技藝,“最重要的當然是要從生活改造起來才行。使生活的領域擴大,使生活的經驗豐富,使生活勇敢而有力”,一個“潑辣堅實的生命”,“自可免于狹小的,片面的,或過火的反應”。{24} 這意味著具有現代性的新詩需要詩人主體對于現實的在場,以這樣的標準回頭看,早期新詩“感傷”的根源更是一目了然,雖然它強調真誠,“美德是真誠的,真誠是高尚的”{25},但卻缺乏牢固的現實根基,主觀情感的真誠只是一種詩學倫理標準,在詩學效果上卻很可能包含“不真”的成分。
與上述感傷的抒情詩相比,同時期郭沫若的浪漫主義詩歌影響更大。從情感機制來說,這樣的抒情詩都是因生理沖動而發生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古典的、靜態的、柔弱的,后者是現代的、動態的、有力的。相對于感傷的抒情詩,郭沫若的詩歌更具有時代特征,也就是更現代,它具有更突出的社會政治涵義,然而這種“現代”準確地說應該是前現代,因為它在表達方式上與西方浪漫主義詩歌具有同質性,郭沫若的詩歌是激情的,但這種激情一旦受挫,就容易落入感傷。
二、“素樸的詩”——離棄“生理的沖動”
席勒在18世紀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之爭中,曾將詩歌分為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詩人或則就是自然,或則尋求自然。在前一種情況下,他是一 個素樸的詩人,在后一種情況下,他是一個感傷的詩人。”素樸的詩人是和諧統一的,感傷的詩人是活躍緊張的,“素樸詩人把我們安排在一種心境當中,從那里我們愉快地走向現實生活和現實事物。可是,另一方面,感傷詩人除少數時刻外,卻經常會使我們討厭現實生活。這就是因為無限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把我們的心靈擴大到它的自然限度之外,以致它在感官世界中找不到任何事物可以充分發揮它的能力。我們寧可回到對于自身的冥想中,在這里,我們會給這個覺醒了的、向往理想世界的沖動,找到營養。至于在素樸詩人那里,我們則要努力從我們自身向外流露,去找尋感性的客觀事物”{26}。兩種詩歌各有特點,感傷的詩是主觀的、厭世的,它向外擴張;素樸的詩則是客觀的、平和的,它內收于己。席勒肯定的是“素樸的詩”,而如果存在一種理想的詩歌,席勒認為是將二者結合起來,席勒的這一分類恰好在1920年代的早期新詩中呈現出來。
如果說1920年代初“感傷的詩”盛行一時,那么與此相對,周作人的詩則屬于沒有太多情緒渲染的“素樸的詩”,這一評價來自沈從文:“使詩樸素單一僅存一種詩的精神,抽去一切略涉夸張的詞藻,排除一切煩冗的字句,使讀者以纖細的心,去接近玩味,這成就處實則也就是失敗處。因這個結果,文字雖由手中而大眾化,形式平凡而且自然,但那種單純,卻使讀者的情感奢侈,一個讀者,若缺少人生的體念,無想象,無生活,對于這樸素的詩,反而失去認識的方便了。”{27} 沈從文的評價道出了周作人詩歌樸素又耐人尋味的特點。
對于新詩的抒情性質,周作人的《論小詩》具有總結性:“本來詩是‘言志的東西,雖然也可用以敘事或說理,但其本質以抒情為主。”{28} 四年后,他在《〈揚鞭集〉序》中又言:“新詩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歡嘮叨的敘事,不必說嘮叨的說理,我只認抒情是詩的本分”,“凡詩差不多無不是浪漫主義”。{29} 然而,周作人的詩卻非青春浪漫型的詩,而是一種中年,甚或老年的詩,它看似淺白樸質,細細體味卻有一種禪意,這樣的“樸素”實際上是他寫作的一貫風格,而尤以他的新詩集《過去的生命》為突出。周作人并不像廢名酷愛冥想和聯覺,他只是直接地呈現即時即刻的觀感,至于其中的人生況味,得仔細咀嚼才能體察。需要注意的是,這部詩集與1920年底周作人的一場病有關:發熱,醫生診斷為肋膜炎,第二年九月才治愈。
經過“五四”的各種思想、主義的沖撞以及理想主義的“熱病”之后,一場真實的病倒是讓周作人的精神冷靜并抽離出來,收入《過去的生命》的詩歌如《愛與憎》《夢想者的悲哀》《歧路》《小孩》《飲酒》等詩,留下了周作人逐步在意識上拒絕“主義”的紛擾并回到“自己的園地”的痕跡,其中有懷疑也有醒悟。1927年他在《談虎集》的“后記”中說道:“凡過火的事物我都不以為好”,“民國十年以前我還很是幼稚,頗多理想的,樂觀的話,但是后來逐漸明白,卻也用了不少的代價。”{30} 他自稱散文《尋路的人》是他自己內心真實的表白,“我卻只想緩緩的走著,看沿路的景色,聽人家的議論,盡量享受這些應得的苦和樂,至于路線如何,那有什么關系?”{31} 從中可以看到周作人對現實明確的疏離感。
然而,“樸素”也并非周作人的天性,1922年2月26日他在《晨報副刊》上發表《詩的效用》一文持“主情”的觀點,且將“情”歸之于生理的沖動:“詩的創造是一種非意識的沖動,幾乎是生理上的需要,仿佛是性欲一般”,“文藝本是著者感情生活的表現,感人乃其自然的效用”。{32} 數月之后,他又發表《論小詩》一文:“小詩的第一條件是須表現實感,便是將切迫地感到的對于平凡的事物之特殊的感興,迸躍地傾吐出來,幾乎是迫于生理的沖動,在那時候這事物無論如何平凡,但已由作者分與新的生命,成為活的詩歌了。”{33} 可以看到,周作人在描述寫詩的沖動時,明確地將它看作是生理性的,這也符合浪漫主義以及中國傳統詩學的觀點,這樣的生理沖動會帶來精神上的“熱病”,而精神的“熱病”包括“思想的動搖和混亂”,極易導致“神經衰弱”等身體的疾病,因而周作人更愿意撇開讓人躁動的詩歌去讀佛經、寫散文,他說:“做詩使心發熱,寫散文稍為保養精神。”{34} 為了修養身心,周作人即使是寫詩,也是散文化的,不過其古樸、清淡的風格中卻又蘊涵著幽深,這與傳統文化包括佛教文化有內在的聯系。
即使個人的寫作趨向客觀的寫實,周作人也仍然認為新詩的本職在于抒情,只是抒情的方式可以進行調整,他將“生理的沖動”轉換為一種當下的體驗,或曰“剎那間的感興”,書寫的是平凡的事物:“我們日常的生活里,充滿著沒有這樣迫切而也一樣的真實的感情;他們忽然而起,忽然而滅,不能長久持續,結成一塊文藝的精華,然而足以代表我們這剎那內生活的變遷,在這一意義上這倒是我們的真的生活。”{35} 來自于日本俳句的“小詩”感情疏淡,語言素樸,同時還有清悠淡遠的意境,相對于那些激烈跳蕩、哀怨滿腹的抒情詩,這樣的寫法使過火的情緒得到了遏制。
波德萊爾提出的現代感性即審美現代性是從“過渡的、短暫的、其變化如此頻繁的成分”中“提取它可能包含著的在歷史中富于詩意的東西”,“從過渡中抽出永恒”{36}。相對于波德萊爾詩歌中那些碎片化的瞬間及其對世俗欲望的沉淪,周作人以古典的心態對待這樣的“瞬間”,即希望在每一個瞬間獲得生命的自足和安寧。在《老年的書》中他借用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的看法,說自己需要的文學是“心的故鄉”的文學{37},與朱自清在《毀滅》中表達的希望回到的“故鄉”是“現實”不同,周作人希望回到的“故鄉”則是生命永恒的歸宿。
姜濤認為:“周作人對于‘平凡實感的偏愛,對于‘過火的事物之憂懼,便不僅僅是個人趣味的表達了,其中包含了他對整個‘現代的疏遠及再思考。在日常生活的基礎上培育一種新的倫理感受,通過對‘人情物理的發現來重建現代中國人理性調和的生活世界,本身就是周作人后來嘗試的一種‘另類的現代性方案。”{38} 然而,與其說這是“現代性方案”,不如說它是返回古典的方案,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說:“我恐怕我的頭腦不是現代的,不知是儒家氣呢還是古典氣太重了一點。”{39} 這里包含了他清醒的自我定位。當時的小詩作者除了周作人,還有冰心、宗白華等,雖然有散文化的傾向,但他們的詩并不像周作人的詩那般樸素客觀,而更多淺近的抒情和說理。
1926年周作人在回顧新詩時說:“一切作品都像是一個玻璃球,晶瑩剔透得太厲害了,沒有一點兒朦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種余香與回味。”{40} 他因而提倡浪漫主義的創作原則和象征的手法。雖然提倡“具體的寫法”的早期白話詩與提倡“剎那間的感興”的“小詩”在寫法上有一脈相承之處,如周作人的《兩個掃雪的人》《微明》《路上所見》《北風》等詩歌就有類似于早期白話詩的寫實風格,但同樣是寫實,周作人的這些小詩在意境和美學層次上與早期白話詩顯示出了差異。如果說早期白話詩的“寫實主義”過于平淡直白,那么周作人的“小詩”則顯得有“余香與回味”,這來自客觀的寫物中所容納的禪意,即“言近而旨遠”。更需要看到的是,由于其與早期白話詩在新詩發展中的位置各不相同,周作人的寫法具有的意義也就格外不同:在經歷了早期新詩的感傷主義情緒之后,周作人寫法上的“往后退”甚至“返回古典”確實起到了警惕“過火的情感”的作用。
然而,與其說這是周作人為新詩提供的方案,不如說是為他個人提供的方案,從構建現代的主體來說,它也存在缺陷,正如他為自己的詩集《過去的生命》所作的序言所言:“這些‘詩的文句都是散文的,內中的意思也很平凡,所以拿去當真正的詩看當然要很失望”,在當時,周作人也“不知道中國的新詩應該怎么樣才是”{41},只能從個人的處境和性情出發,構造一種首先讓自己能接受的新詩。廢名在《談新詩》中認為新詩的形式是散文化的,內容是詩的,而周作人的詩歌從內容到形式都是散文化的,雖然廢名對周作人的方案多有贊同,但兩人的創作還是有差別的。同樣是寧靜的美學,與周作人筆下具體的日常不同,廢名卻非常注重詩歌的想象力,通過冥想他將天地萬物收納于一體。相對于廢名,周作人的詩非常散文化,缺乏“詩性”,并非一種現代意義上的詩。另外,對于日常事物入詩的問題,聞一多也有和周作人不一樣的看法,他說:“尋常的情操不是不能入詩,但那是點石成金的大手筆的事,尋常人萬試不得。”{42} 周作人和聞一多的出發點完全不同,前者出于一種個體生命哲學的考慮,而后者則出于對新詩現代性的追求。
站在時代精神和抒情主義的立場,周作人這種“素樸的詩”也曾被詬病。成仿吾就對周作人引進的日本小詩予以否定,認為“俳諧不足模仿”,一是“俳句僅一單句,沒有反復的音律,他實在沒有抒情的可能”;二是安于靜寂,“與時代精神背道而馳”,它為做詩而做詩,而非處處“真摯的熱情做根底”,是一種“游戲的態度”。{43} 對此,周作人顯然并不認同,《〈知堂雜詩抄〉舊序》說:“我哪里有這種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材料,要來那末苦心孤詣的來做成詩呢?也就只有一點散文的資料,偶爾想要發表罷了。”{44} 周作人抵制過火的熱情的方式,是回到“自己的園地”,雖然他的小詩表達了具體的實感,然而,卻隔絕了時代、社會的經驗,這也決定了他的詩是“小”而“舊”的。
三、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感傷的詩”和“素樸的詩”代表了早期新詩兩種不同的抒情路向,也反映了早期新詩在抒情性上暴露的問題。實際上,浪漫的詩歌也并非如周作人認為的那樣一概會導致熱病。在西方詩歌中,浪漫主義的熱情一方面可能是熱病,另一方面也可能走向精神的寧靜和永恒。肯尼斯·勃克在《濟慈一首詩中的象征行動》中認為,對于濟慈來說,肺結核的高燒和寒冷等疾病癥狀與其詩歌創作有著緊密的聯系,由于身體的激情短暫易逝,需要將其轉換為積極的、永恒的精神,“身體的欲求是高燒惡性的一面,而精神的行動是良性的一面。在接下來的發展中,惡性的欲求被超越,而良性的行動的另一半,也就是智性歡樂占據了首要位置”。{45} 也就是說,詩人水準的高低要看他的激情和狂熱是否在詩歌中能化為寧靜和永恒,這是西方批評家的標準,中國的新詩在當時還只能往兩個方向走,或躁動,或冷靜,并不具備這樣升華和超越的能力。
新詩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說就是抒情性的發展變化過程,而抒情性并不是一個可以單獨抽離出來的問題,在技藝層面它與感覺、想象聯結,在情感的層次和深度上它與經驗、思想聯結。從早期白話詩到新月派、現代派以及七月派、西南聯大詩人群的發展中可以看到,新詩逐漸從抽象、浮泛的感傷抒情走向真實、具有深度的抒情,早期新詩的躁動和泛濫之“情”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和轉換,這也正是新詩從脫離于現實的感傷的“個人”走向個人與現實相結合的過程,它同時說明,“身體”作為構成現代主體的重要前提和基本內容,它可以在新詩的抒情中扮演積極和消極兩種不同的角色,積極是指“身體”在寫作中體現為具體性和現實感,消極是指它僅僅體現為一種本能的沖動。
注釋:
① 朱自清:《詩與哲理》,《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34頁。
② 朱自清:《抗戰與詩》,《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頁。
③ 王德威:《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3頁。
④ 俞平伯:《做詩的一點經驗》,《新青年》1920年第4期。
⑤{43} 成仿吾:《詩之防御戰》,《創造周報》1923年第1期。
⑥ 胡適:《俞平伯的〈冬夜〉》,《讀書雜志·努力增刊》1922年第2期。
⑦ 查爾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韓震等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35頁。
⑧{17} 聞一多、梁實秋:《〈冬夜〉〈草兒〉評論》,清華文學社1922年版,第61、63頁。
⑨ 汪靜之:《詩歌與真理》,《文學周報》1928年第6期。
⑩ 胡適:《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412頁。
{11} 胡適:《〈蕙的風〉序》,《胡適文集》第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24頁。
{12}{25} 威廉·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周娜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17、222頁。
{13} 胡夢華:《讀了〈蕙的風〉以后》,《時事新報·學燈》1922年10月24日。
{14}{15} 聞一多:《聞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127頁。
{16} 梁實秋:《談聞一多》,《梁實秋散文》第1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版,第367頁。
{18} 朱自清:《讀〈湖畔〉詩集》,《時事新報·文學旬刊》1922年第30期。
{19}{38} 姜濤:《公寓里的塔》,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96、110—111頁。
{20}{21} 張松建:《抒情主義和中國現代詩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102頁。
{22} 金克木:《論中國新詩的新途徑》,《新詩》1936年第4期。
{23} 袁可嘉:《新詩戲劇化》,《詩創造》1948年第12期。
{24} 李廣田:《論感傷》,《文訊》1948年第4期。
{26} 席勒:《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蔣孔陽譯,《西方文論選》(上),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93頁。
{27} 沈從文:《論劉半農〈揚鞭集〉》,《沈從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頁。
{28}{33}{35} 周作人:《論小詩》,《周作人自編文集·自己的園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8、43頁。
{29}{40} 周作人:《〈揚鞭集〉序》,《周作人自編文集·談龍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1頁。
{30}{39} 周作人:《后記》,《周作人自編文集·談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93、393頁。
{31} 周作人:《尋路的人》,《周作人自編文集·過去的生命》,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頁。
{32} 周作人:《詩的效用》,《周作人自編文集·自己的園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頁。
{34} 周作人:《與廢名君書十七通》,《周作人自編文集·周作人書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108頁。
{36} 波德萊爾:《現代生活的畫家》,《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郭宏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484—485頁。
{37} 周作人:《老年的書》,《周作人自編文集·秉燭后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頁。
{41} 周作人:《序》,《周作人自編文集·過去的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頁。
{42} 聞一多:《評本學年〈周刊〉里的新詩》,《清華周刊》1921年第7期。
{44} 周作人:《〈知堂雜詩抄〉舊序》,《周作人文類編·夜讀的境界》,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639頁。
{45} 肯尼斯·勃克:《濟慈一首詩中的象征行動》,《讀詩的藝術》,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72頁。
作者簡介:李蓉,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金華,321004。
(責任編輯? 劉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