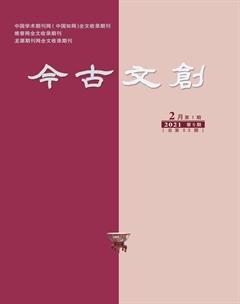周秦《書》學中的“明德慎罰”
張建會 王云鵬
【摘要】 上古“以《書》為訓”的《書》學發(fā)展基調(diào)奠定了周秦諸子“以《書》議政”的政治傳統(tǒng);先秦諸子紛紛在滿足自身學說的基礎上,以建立《書》學、繼承《書》學為己任,積極探索周秦時期《書》學之傳統(tǒng)。“明德慎罰”作為《書》學傳統(tǒng)中卓有成效且具有代表性的施政方針,成為周秦《書》學新變后的一支新秀。
【關(guān)鍵詞】 《書》學;《書》學傳統(tǒng);“明德慎罰”
【中圖分類號】K221?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05-0048-02
基金項目:江蘇省教育廳哲學社會科學項目:“天醫(yī)星”文化視域下古代醫(yī)德文獻整理與研究(編號2020SJA1862)。
“明德慎罰”一詞最早見于《尚書 · 周書》的《多方》《康誥》兩篇,研究“明德慎罰”思想最好從周秦時期開始,且離不開周秦時期的《尚書》學研究。周秦《尚書》學為解析“明德慎罰”思想提供了學術(shù)背景,是解決周秦“明德慎罰”問題的先決條件。近代有關(guān)“明德慎罰”的研究多集中于“明德慎罰”的思想內(nèi)容,鮮有文章將“明德慎罰”放入特定的《尚書》學史中,從社會背景的視域進行探討。
一、周秦《尚書》學概貌
《尚書》對周秦諸子的作用和影響集中表現(xiàn)在諸子紛紛稱引《尚書》并以之為風尚,形成了《書》學熱潮。周秦諸子“引《書》議政”不僅是上古《書》學傳統(tǒng)在周秦時期的發(fā)展,還是非官方的《書》學新變。周秦時期,諸子征引《尚書》的現(xiàn)象比較普遍。茲取儒、墨、道、法四家,分別舉例析之,從中探求周秦諸子的《書》學要論,管窺周秦《書》學概貌。
《尚書》作為儒家學派開科授徒的必修科目是因為其資政的功用滿足了儒家學派的需求;孟子肯定《尚書》對治政的積極意義的實質(zhì)是促進其實現(xiàn)資政的宿命。孟子認為《書》學中很多治國理政之觀點,符合儒家治世理想,尤其是對治國理政的看法與理解,故而在探索治國理政之良策時,孟子時常引用《書》中的觀點。據(jù)《孟子》載: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1]115-117
周秦典籍中,《墨子》引《書》頻次極高。鑒于《尚書》的權(quán)威性,墨子論辯時多稱引《尚書》以佐證墨家學派之主張的合理性。[2]87墨子引《書》、論《書》的《書》學方式和表現(xiàn)形式表達了其學說傾向和《書》學見解,據(jù)《墨子 · 尚同中》載:
昔者圣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為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為五殺。[3]83-85
莊子一派對《尚書》的積極闡釋使道家作為顯學積極活躍在社會政治舞臺。雖然莊子從道家立場出發(fā),間或貶低儒學,與之爭鳴非難,但《莊子》引《書》論事,積極推進了《書》學演進的歷程,豐富了周秦的《書》學學脈。據(jù)《盜跖》載:
“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zhàn)于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莊子 · 盜跖》)[4]1003
周秦法家學派的《書》學方式可以以《韓非子》為代表。韓非子承繼荀子《書》學主張并發(fā)展、闡揚,形成了隸屬于法家學派的《書》學體系。韓非子對《尚書》的解釋和引申是法家學派的學說主張的外在體現(xiàn)。據(jù)《韓非子》載:
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5]175-176
周秦時期對《書》學的學習、繼承與研究,主要表現(xiàn)在諸子們對《書》的引用與注釋。但是,諸子學說由于在政治理想上主張不同,因此,諸子們在自己不同的理解下,對《書》進行了不同的理解與應用。這種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實質(zhì)是《書》學詮釋內(nèi)涵因諸子學說需要而分化、割裂。客觀地研究周秦《書》學面貌[3]45,看待周秦《書》學及《書》學傳統(tǒng),必須依據(jù)不同學派加以甄別。無論是積極的應用或激烈的否定,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書》學體系的發(fā)展。
二、周秦《書》學傳統(tǒng)下的“明德慎罰”
儒家文獻中,《尚書 · 周書》中最早出現(xiàn)“明德慎罰”一詞,對“明德慎罰”思想的研究也最早從周秦時期開始。周秦典籍引“明德慎罰”,其中,《尚書》引“明德慎罰”兩次;《左傳》引《書》“明德慎罰”一次;《荀子》引“明德慎罰”一次;《孔叢子》引《書》“明德慎罰”一次。[2]80《尚書》中的《康誥》 《多方》兩篇是最早出現(xiàn)“明德慎罰”的篇章,故而此處“明德慎罰”的記載被后世認為是“明德慎罰”思想的肇端。“明德慎罰”思想的產(chǎn)生是建立在以鑒戒為目的的古圣先賢的哲思智慧的基礎上的,從一定程度上的確取得了成功,保障了政權(quán)的長久,據(jù)《尚書 · 康誥》載:
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qū)夏,越我一、二邦以修。[6]532
應該說,“明德慎罰”作為周秦時期最高的治政方針,被普遍應用于古代法律體制中,并逐步成為當時的治國策略。這種現(xiàn)象不僅明顯地提高了當時治國理政之效率,更是成為后世檢驗治國理政方式是否合理的標準之一。[2]87據(jù)《尚書 · 多方》載: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7]669-670
由上可見,周秦時期《書》學作為一種治國理政的標準一直存在著,一方面極大地保障了施政措施的有效落實,另一方面也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引起了后世當權(quán)者的足夠重視[2]83。《左傳》成公二年,楚莊王伐陳,申公巫臣引用《周書》“明德慎罰”之義勸諫莊王: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8]803
“明德慎罰”思想和上古政治自有淵源,經(jīng)歷史檢視和擇選,表現(xiàn)出了資政功用的本質(zhì),成為我國古代獨具特色的政治理念。《書》學是構(gòu)成百家學術(shù)的重要基礎,周秦《書》學新變也體現(xiàn)在諸子的“明德慎罰”觀中。荀子將“明德慎罰”視為治理國家、安頓百姓、平定天下的不二法門:
治之經(jīng),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9]461
由上可以得出,周秦時期,作為施政綱領(lǐng)“明德慎罰”,同時也是執(zhí)政者治國理政追求的最高境界。“明德慎罰”通過指導治國理政的方式成為治政綱領(lǐng),由政治層面進入到普通社會,彰顯出當權(quán)者施政意識具有了法律的特征[3]P67。雖諸子學說各具特色,但引《書》的核心旨意是相同的。周秦時期的《書》成了文化統(tǒng)治權(quán)力和統(tǒng)治權(quán)威的證詞[2]78,鑒于此,諸子學派也必須援引《書》。據(jù)《孔叢子》載,孔子借《周書》“明德慎罰”勸諫齊景公并取得了成效: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jù)自外而至……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wèi),統(tǒng)三監(jiān)之地,命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勑誡之文。”[10]21
作為三代之政史,《尚書》承繼了上古政治意念,深度總結(jié)、把握了歷史上的王朝興衰規(guī)律;“明德慎罰”思想作為《尚書》宣揚的指導性的施政方針,跨越了多個復雜的歷史時期,在《書》學發(fā)展史及以治《書》、用《書》為主要目的而形成的《書》學傳統(tǒng)中表現(xiàn)出了符合時代課題的《書》學發(fā)展特點。“明德慎罰”表現(xiàn)出的突出的治政功用是歷史上的《書》學經(jīng)過否定、承繼后,融入于政治范疇的結(jié)果。
三、結(jié)語
周秦時期的《書》學作為正統(tǒng)的學說理念深入發(fā)展,形成了早期的“《書》教”傳統(tǒng),其實質(zhì)是對上古不朽意識形態(tài)之價值的肯定和承繼。周秦“ 《書》學”傳統(tǒng)是對上古《書》中蘊蓄的哲思智慧的理性思考后的周秦《書》學集成。“明德慎罰”作為治政理論,經(jīng)周秦《書》學文化主導下的實用精神的闡揚,形成了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哲學內(nèi)涵。“明德慎罰”的周秦接受史是周秦《書》學傳統(tǒng)下的一個代表性分支,從中可以管窺周秦時期的《書》學面貌,對系統(tǒng)研究周秦《書學》系統(tǒng)、諸子《書》學式樣同樣具有積極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清 ) 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7.
[2]王云鵬.《尚書》“明德慎罰”思想研究[D].曲阜師范大學,2018.
[3]王云鵬.《康誥》“明德慎罰”思想研究[J].昭通學院學報,2017:(4).
[4]( 清 ) 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間詁[M].北京:中華書局,2001.
[5]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61.
[6]( 清 ) 王先慎撰,鐘哲點校.韓非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98.
[7]( 漢 ) 孔安國傳,( 唐 ) 孔穎達正義,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8]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0.
[9]( 清 )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8.
[10]傅亞庶撰.孔從子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2011.
作者簡介:
張建會,男,山東臨沂人,江蘇護理職業(yè)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歷史文獻與整理。
王云鵬,男,黑龍江牡丹江人,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2018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歷史文獻整理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