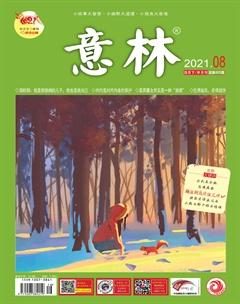你終將會吃不起一碗麻辣燙
溫血動物
上大學時,學校里路邊的麻辣燙是我最愛的食物。
想吃什么就拿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這是自由;沒錢就多拿兩把菠菜,有錢就多拿兩盒肉卷再加三個鵪鶉蛋,反正都在一個湯底里煮,絕不差別對待,這是平等;按重量計費,絕不亂收一分錢,這是公正;食材都擺在眼前,新不新鮮都看得到,這是誠信。如此正能量的食物,身為社會主義接班人的我們,又怎能不愛呢?

大學時,我和狐朋狗友間有一個習俗,月底兜里沒錢了,就去麻辣燙吃“海鮮”,一塊錢一串,再加一大把青菜,十塊錢就能吃飽,還覺得綠油油的特別健康,一點都不丟面子。在一碗牛肉面起步價十八的北京,麻辣燙絕對是我們這幫窮學生的救星了。
麻辣燙界有一個重要的規律:看上去門臉干凈的店,基本沒什么人去;看起來臟不拉幾,自帶20瓦小燈泡的麻辣燙攤子,反而門庭若市,高峰期甚至半天等不到座。
如果真有人對麻辣燙和路邊攤有什么情懷的話,我想這幫人一定都有某些共同特征:沒什么積蓄、年輕、沒有階層觀念。并且他們對未來總是無條件抱有熱情和希望。
2016年畢業,我留在了北京工作。本來我已經和一起開黑打游戲的幾個朋友計劃好了,一起找工作,畢業了一起合租。合租房間的室內設計圖我們都規劃好了,但由于大學期間打游戲的時間過多,找工作比我們想象中也要難得多。最終我的兩個朋友,一個回家去當了公務員,一個準備考研,合租的計劃自然是流產了。
只有我堅持不懈,每天把頭發梳成大人模樣,穿上一身帥氣西裝去找工作。那時候在地鐵站問路,還沒開口別人都揮手說:“不需要,謝謝。”
最終我找到了工作,公司在東四環,我很開心,因為我知道,銀河系中心三里屯就在東三環,一環之隔,應該差距不大,畢竟北京可是有六環呢。
公司樓下不遠處就是大排檔,走馬燈音響放著《走在冷風中》,人們三五一桌聚在一起,酒桌上肚子大的個個看起來都像老總,那些剛畢業的學生端著酒杯,一個個笑得比哭還難看。
我一直覺得,中國唯一配得上“深夜食堂”稱號的,就是麻辣燙了。有著不同故事的人們圍坐在一桌,想吃什么,老板就給你煮什么。路邊三蹦子揚起的灰塵和一鍋可能從改革開放以來就沒有換過的鍋底,共同給你烹出一碗人間煙火,你還別說,還真有那么點緩解當代人孤獨的功效。
掐指一算,我在北京居然生活整整六年了。
一開始大學朋友一周一聚,勉強還能喝一杯;后來一個月見一次,有人說“我上次去醫院檢查,醫生說我有脂肪肝”,有人說“我今天開車,喝不了酒”。有人說“身體不行啦,現在一吃烤串就拉肚子”。于是一群大男人圍著烤串喝酸梅湯。
沒錢的時候,我們擼不起串,有錢了,更擼不起了,因為我們付不起背后的時間成本:我們沒有時間宿醉,沒有時間鬧肚子,也沒有時間翻山越嶺,從朝陽跑到海淀來看你了。
最后我們差不多半年一聚了。約在學校門口,一伙人走在校園里,居然有點做賊心虛的感覺。為了緩解這種心虛,有人提議說要去吃麻辣燙懷個舊,走到靜園,幸好攤子還在,只是老板換了新面孔。 吃了兩串魚豆腐,遺憾地發現自己已經吃膩了,以前覺得魚豆腐就是麻辣燙界的鵝肝啊,現在含在嘴里像是塊橡皮。吃完之后回去,五個人有四個拉了兩天肚子。
我也沒有再吃過麻辣燙,因為不衛生,因為不健康,因為沒人一起去,因為懶得出門,因為路邊攤越來越少了。可我想了想,真正的原因其實只有一個,因為我不再年輕了。但我還是想祝福你,能遇到一群跟你一起快樂地吃麻辣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