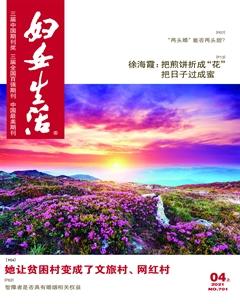媽媽,我一直陪著您
復林
32年前,她被養母從垃圾箱旁撿回。從她記事起,養母每隔兩年就要住一次精神病院。12歲之前,她只知道有養父,卻從來沒見過。12歲時,她與養父第一次見面,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從此對養母心存感恩。長大后,她將患了老年癡呆的養母接到身邊細心照料。孰料,長期失聯的養父突然出現,打起了養母房子的主意,還提出解除與她的收養關系。而她,不愿與養母解除母女關系——
得知自己的身世,吳怡幾乎在一夜之間長大,她開始懂得感恩,不再因為媽媽的“瘋”病而覺得羞恥
家住江蘇省鎮江市的吳怡,12歲時才知道自己的身世。那是2000年1月,小學六年級寒假的第一天,媽媽吳文煜帶著吳怡到市區的城中村,要她與父親張勇相認。一路上,吳文煜反復叮囑她:“進了門要叫爸爸。”誰知,見到張勇后,她還沒出聲,張勇就冷冷地說:“瘋婆子,這就是你撿來的丫頭?”
返回的路上,吳怡邊哭邊問媽媽:“我真是你撿來的嗎?”吳文煜斷斷續續說起了往事。1988年10月的一天早上,她出門就聽到清亮的啼哭聲,循聲找尋,在垃圾箱旁發現了襁褓中的吳怡,她身邊還有一張字條,上面寫著她的生日。
得知自己的身世,吳怡幾乎在一夜之間長大,她開始懂得感恩,不再因為媽媽的“瘋”病而覺得羞恥。從吳怡記事起,媽媽每隔兩年就要住一次精神病院。媽媽住院期間,姥爺、姥姥負責照顧她的生活。她只知道有父親,還有一個哥哥,卻從沒見過面。精神狀態穩定的時候,吳文煜對吳怡十分疼愛。
1999年,媽媽又犯病了,嘴里不停說:“兒啊,你怎么不帶媽媽一起走?”吳怡問姥姥,媽媽的話是什么意思,姥姥這才告訴她,吳文煜與張勇結婚后生過一個孩子張揚。張揚1歲多時,吳文煜間歇性精神分裂癥發作,張勇帶著兒子離開了家。幾年后,張揚也被診斷出患有精神疾病。那年3月,張揚去世。吳文煜受到刺激,又發病了。
半年多后,吳文煜出院了,她看起來和常人并無二樣。趁著吳怡放寒假,吳文煜想讓她和張勇相認,不承想暴露了吳怡的身世。
2001年5月,吳怡的姥姥病故。張勇在城中村的房子要拆遷,他便搬回家與吳文煜母女同住。這是吳怡記事起父母第一次團聚。然而,一家三口只共同生活了四五年,張勇就去了外地,從此再無音信。
吳怡大學畢業那年,本來有機會留在南京就業,可為了照顧母親,她回到了鎮江。熱心人看她一直單身,便給她介紹對象,她有言在先,婚后要與養母生活在一起。這個要求嚇退了不少男孩,直到2015年,一個叫趙剛的小伙子接受了吳怡的要求,和她結了婚。
吳文煜被女兒女婿接到新買的房子里照料,她原來的住宅空置了下來。
養父:“我們沒有到民政部門辦理收養手續,也就意味著收養關系不成立,你哪里來的監護資格?”
2017年,吳文煜的病情越來越嚴重,漸漸失去了記憶,大小便不能自理,連女兒都不認識了。4月,吳怡帶母親去醫院檢查,醫生說她長期服用抗精神病藥物,導致認知功能完全喪失,已經發展成了老年癡呆癥。
2017年6月,吳怡懷孕了,想著夫妻倆收入都不高,還得繳月供,還得照顧吳文煜,她便做通了趙剛的工作,決定暫時不生育,到醫院做了流產手術。
2018年春節,長期失聯的張勇突然找上門,說他年齡大了,想住進條件好一些的老年公寓,無奈退休金比較低,基本沒什么積蓄,提出賣掉吳文煜的住房:“賣房的錢,我只拿一半,另一半你保管,將來由你繼承,可以辦個公證手續。”
吳怡知道,養父說的房子原是姥姥單位分的公房,住房改革那年,姥姥出資買斷,產權直接登記在吳文煜名下。姥姥在臨終前曾囑托,這房子要吳文煜居住終老。吳怡將母親接到身邊后,房子一直保持原樣。
因此對于養父的提議,吳怡直接拒絕了。她說房子不能賣,但愿意接納養父共同生活:“這樣既節約了花銷,你也可以在我們身邊頤養天年。”張勇卻皺起了眉頭:“你姥姥家害了我一輩子,我婚后才發現你媽有這病,這么多年也沒有離成婚,從來沒有過上像樣的日子。年輕時就因為不愿意面對你媽,我才幾度出走。現在我老了,更不想每天對著她心里添堵。”見養父這樣說,吳怡表示,她可以每月給養父贍養費,如果他生病住院,她可以分攤醫療費,但房子在母親生前絕不可能處理。
經過數次交涉,吳怡都沒有松口。張勇咨詢律師后,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宣告吳文煜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并指定他為監護人。
法院通過醫學鑒定,確定吳文煜已經喪失意識,確實不具有民事行為能力。吳怡對此沒有異議,但提出,張勇雖系吳文煜的丈夫,但雙方已經分居10余年,在此期間,她與母親相依為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吳文煜的監護權應當由她這個正在進行貼身照顧的女兒行使。張勇卻說:“我們沒有到民政部門辦理收養手續,也就意味著收養關系不成立,你哪里來的監護資格?”
2019年7月,法院判決,宣告吳文煜沒有民事行為能力,指定張勇為其監護人。
之后,張勇并沒有到吳怡家中探望妻子。兩個月后,他告知吳怡已經為那套房子找好了買家,讓吳怡清空室內物品并交出鑰匙。
法院審理認為:吳怡年幼時即被吳文煜領養是客觀事實;張勇知道妻子的收養行為后,曾在經濟上幫助妻子撫育養女;兩原告和被告之間也以父女、母女相稱,因此可以確認兩原告與吳怡存在事實上的收養關系
為阻止張勇賣房,吳怡索性帶著母親住進了那套房子里。此后,幾撥看房的人都被吳怡勸了回去。張勇對此又氣又急,干脆作為原告,同時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將吳文煜也列為原告,起訴到法院,請求確認吳文煜與吳怡的收養關系無效。
張勇訴稱,我國于1982年就實行了計劃生育政策,他和吳文煜于1983年生育了兒子,同年領取了獨生子女證。因此,吳文煜在1988年領養吳怡的行為,違反了計劃生育政策,而且也沒有辦理收養登記。另外,吳文煜于1980年被確診為精神分裂癥,并住院治療。她生下兒子后病情有所發展,不具備收養子女的相應民事行為能力。
吳怡據理力爭:“張勇沒有證據證明吳文煜當時不具備民事行為能力,而且他的訴求也不能代表吳文煜本人的真實意愿。張勇更沒有證據證明吳文煜在收養我時違反了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因此,即使存在沒有辦理收養登記的瑕疵,但我從被收養到現在已將近30年,收養早已既成事實。這些年,吳文煜對我視如親生,我也把吳文煜當作親生母親,我們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均未提出解除收養關系。因此,張勇存在濫用監護人代理權的行為。”
法院審理認為,吳怡年幼時即被吳文煜領養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張勇知道妻子的收養行為后,也曾在經濟上幫助妻子撫育養女;兩原告和被告之間以父女、母女相稱,因此可以確認兩原告與吳怡存在事實上的收養關系。案涉收養事實發生于1988年,即為199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實施之前,當時,辦理收養登記并非確認收養關系合法性的必要條件,原、被告之間存在事實收養關系。
法官還指出,張勇認為收養無效的理由有兩點:其一,兩原告曾生育一子,故收養行為違反了計劃生育相關的政策法規;其二,吳文煜系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不具備收養子女的能力。
對此,合議庭認為,雖然吳文煜患有精神疾病時間較長,但精神疾病系醫學概念,民事行為能力系法律概念,兩者不能混同。吳文煜在2019年才經司法鑒定確認無民事行為能力,但并不能就此推定其在1988年收養吳怡時就無民事行為能力。即使吳文煜有多年精神疾病史,也并不必然可以認定她一直處于無民事行為能力狀態,更無法確認她無收養被告的行為能力。
而且,原、被告間的事實收養關系發生在《收養法》和《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頒布、實施之前。在此前不同歷史時期,計劃生育作為國家的基本國策,也有相應的規章,國家推行和鼓勵一對夫妻只生育一個孩子,嚴格控制生育第二個孩子,但也有可生育二胎的例外,如《江蘇省計劃生育條例》在推行和鼓勵只生一胎的原則性規定下,同時規定了可按計劃再生一個孩子的情形。本案中,張勇、吳文煜的婚生子自幼患有精神疾病,并不當然排除收養的合法性。
2020年12月23日,江蘇省鎮江市潤州區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駁回兩原告確認收養關系無效的訴訟請求。宣判后,張勇沒有提出上訴。吳怡將判決書念給吳文煜聽時,吳文煜似乎明白了什么,臉上露出了笑意。吳怡捋了捋養母的白發,貼在她耳邊輕輕說:“媽媽,我一直陪著您!”
點評:
收養制度是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合法的收養關系應予以保護,穩定合理的收養關系應予以尊重。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設立了三個條款,對解除收養關系的條件做出了明確具體的規定。第1114條:當事人協議解除及因違法行為而解除。收養人在被收養人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養關系,但是收養人、送養人雙方協議解除的除外。養子女8周歲以上的,應當征得本人同意。收養人不履行撫養義務,有虐待、遺棄等侵害未成年養子女合法權益行為的,送養人有權要求解除養父母與養子女間的收養關系。送養人、收養人不能達成解除收養關系協議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第1115條:關系惡化而協議解除。養父母與成年養子女關系惡化、無法共同生活的,可以協議解除收養關系。不能達成協議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第1116條:解除收養關系登記。當事人協議解除收養關系的,應當到民政部門辦理解除收養關系登記。
本案中,張勇援引的收養無效的法律規定,皆是著重保護被收養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以防出現不利于被收養人健康成長的情形。事實上,吳怡早已成年,并且參加工作、成立家庭,不存在阻礙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情形。
依據傳統倫理,收養關系的目的是為了組成一個完整的家庭,是為了幼有所育、老有所養。現在,不論是張勇還是吳文煜,都已年老體弱,急需吳怡履行贍養義務。若認定收養關系無效,就可能會出現吳文煜無人贍養和照顧的情況,更會出現事實上吳怡愿意贍養吳文煜和張勇,而法律還要否認其父女、母女關系的悖論,不利于保護收養人的合法權益。另外,依據公序良俗原則,法院也不應對吳文煜收養吳怡的行為作無效認定。
【編輯:潘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