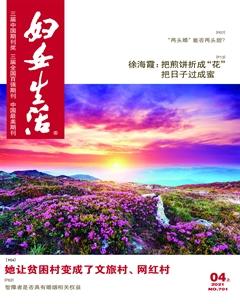智障者是否具有婚姻相關權益
祁雪瑞 崔凌云
編者按:
2月28日,一段“河南駐馬店55歲男子娶智力殘障女孩為妻”的視頻在網上熱傳,引發網友熱議,當地官方也對此進行了調查、通報,河南省婦聯還為此事專門組織了研討會。鑒于這個事例牽涉一個群體的權益是否被國家法律認可和保護,我們覺得很有必要對此進行深入的剖析和探討。
“55歲男子娶智力殘障女孩為妻”的視頻在網上熱傳,引發網友熱議
根據《新京報》《楚天都市報》等多家媒體的報道以及官方的調查,我們梳理了事情的大致情況:2021年2月27日,駐馬店市泌陽縣一張姓村民在家中舉辦婚禮,新娘智力殘障,看上去未成年,一直哭泣,新郎明顯比她大不少,時不時用衛生紙替她擦拭淚水。有人拍了這段視頻,發到網上后引發網友熱議:這名女子是不是未成年人?她是不是被脅迫結婚?智障女該不該結婚?他們能否領取結婚證?
3月1日,泌陽縣公安、民政、法院、婦聯和當地政府組成了調查組對此事進行調查核實,之后官方發布通報:智障女子姚某瑞,生于2001年2月,是二級智力殘疾人,持有殘疾證,但是沒有做過民事行為能力認定。她不能說話,不能走路,不會自己吃飯,但能認識親人,有一定的肢體表達能力,可以表達簡單意愿。比如,不想讓“丈夫”離開,她就會拉著他的衣服。男方55歲,為人忠厚,愿意娶姚某瑞,也愿意照顧她。女孩的父親姚某書,母親安某紅,都同意這樁婚事。他們按當地習俗舉辦婚禮,不存在脅迫行為,未發現有違法情況。街坊鄰居對他們的婚禮也都認可。但根據法律規定,民政部門不能給這對新人頒發結婚證。他們可以同居,生育的孩子可以上戶口。
現實中,我國不少地方都存在結婚登記不了,但也辦了婚禮的情況。如果清楚知道對方有智障,雙方出于滿足生活、生理需要同居,在法律上沒有明確規定不允許
官方通報稱,這對男女同居不違法,但不能給他們頒發結婚證。有法學研究者認為,這是現行法律的疏漏造成的。《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一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無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結婚的親屬關系;(三)未到法定婚齡。本事件中均不存在上述情形。根據《殘疾人保障法》第四條規定:“國家采取輔助方法和扶持措施,對殘疾人給予特別扶助,減輕或者消除殘疾影響和外界障礙,保障殘疾人權利的實現。”這里所說的權利,應該包括殘疾人結婚和離婚以及性生活的權利。
根據我國法律規定的代理人制度,本事件中女方不能正確表達或明確表達自己的意愿,其合法的代理人(包括但不限于法定代理人)可以為了其利益代為表達。那么,怎么判斷其代理人的代理行為符合女方的利益呢?我們認為,應該采用一般人公認的標準和公序良俗標準,也就是說,在不違反法律的情況下,一般人認為可以,就應當推定為可以。視頻中女方在婚禮現場的哭泣,不能認為是對結婚的拒絕,可以采信男方的解釋,女孩哭是因為“認生”。這也說明女孩對結婚沒有認知,對自己的處境卻有所感知,也能表達一定的情感。有人說,不能認知,就不能結婚。但這種觀點剝奪了智力殘疾者的婚姻權益,也侵害了其監護人的監護權。現行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都承認無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監護人可以代為起訴離婚和進行離婚答辯,但對結婚并沒有詳細的規定。離婚和結婚都是婚姻權的內容,法律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在這兩件事上沒有區別對待的理由,只能說,法律沒有明晰智障人士的結婚權是一立法缺陷。這一立法缺陷傳導到《婚姻登記條例》,就使得婚姻登記機關處于尷尬境地。
現實中,我國不少地方都存在結婚登記不了,但也辦了婚禮的情況。如果清楚知道對方有智障,雙方出于滿足生活、生理需要同居,在法律上沒有明確規定不允許。
站在女方現實生活的角度考慮,有人不主張女方結婚,認為男方家庭條件不好,可能不如自己父母照顧得周到。張先生有八旬老父親長年臥床,還要照顧這個女孩,將來可能還要照顧孩子,生活壓力太大。男方已經55歲,不能照顧女方的時候怎么辦?如果他們的孩子也是智障,更是雪上加霜。最好是一直由父母照顧,父母照顧不了的時候,再由政府照顧。但是,女孩的父母認為女大當嫁,智障女兒也應該像正常女孩一樣享受家庭生活,也有做妻子做母親的權利,并無不妥。根據《楚天都市報》2021年3月4日的報道,女方父親說,女兒是大約5歲時生病致殘的,并不是先天性智障。男方希望以后能生育孩子,這對他們來說,可能是個好消息。
對于生不生孩子,有沒有結婚證有重大區別。根據《民法典》第二十八條的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監護人的順序是配偶、父母及子女、其他近親屬。本事件中,如果男女雙方沒有結婚證,僅僅是同居關系,那么女方的監護人仍然是她的父母;如果有了結婚證,女方的監護人就自然變更為她的配偶。對于女方的生育意愿,應該由其監護人根據其利益代為表達。如此,在沒有結婚證的情況下,女方的生育權由其父母決定;而有了結婚證,她的生育權就可以由其丈夫決定。
關于性生活意愿表達問題,以及是否牽涉到婚內強奸問題,表面看是一個難題,實際上用法學理論結合生活常識來分析,并不是特別復雜。性生活是婚姻的重要內涵,是推定雙方自愿的行為,只要沒有明顯的、事后能夠被證明的不自愿的行為和事實,比如分居、受傷等,就應該認為是正常的。對于本事件中的女方來說,只要沒有發現她的身體和生活明顯異常,就應該認為她的婚姻生活、性生活是正常的,性權利是得到了尊重的。網友對她的關愛和擔心可以理解,但是要維護她的合法權益,她的監護人才是第一責任人。如果領了結婚證,她的監護人就是丈夫,而根據生活經驗,最可能侵害她的人也是丈夫。那么,誰來監督這個新的監護人,就牽涉到監督監護人制度的完善問題。
有人指責女方父母嫁女兒是在“甩鍋”。說實話,這樣一個女兒對于大多數家庭而言,都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女方父母養育呵護了她20年,其中付出的艱辛可想而知。如今,他們日漸年邁,想為女兒找個歸宿難道有錯嗎?更何況,他們在女兒“結婚”之前,考慮了兩家的距離遠近,考慮到了對女兒生活狀況了解和幫助的便利性,也考察了男方的人品。
我們衷心希望,這件事能夠推動智障群體婚姻相關權益的保障和實現。
姚某瑞是否具有承諾婚姻的行為能力是他們能否領結婚證的關鍵
針對這起事件中的法律問題,我們采訪了河南針石律師事務所的趙衛萍律師。
趙律師認為,該事件中法律問題的焦點是婚姻的合法性。本事件中男女雙方都符合結婚年齡的要求,也不具有禁止結婚的近親屬關系。因此,姚某瑞是否具有承諾婚姻的行為能力是他們能否領到結婚證的關鍵。
所謂民事行為能力,是指民事主體以自己獨立的行為去取得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的能力。分為完全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無行為能力三種。據媒體報道,姚某瑞父親稱姚某瑞曾被鑒定為“智力殘疾二級”。依據《殘疾人殘疾分類和分級》國家標準,對精神殘疾二級的鑒定標準為:適應行為重度障礙;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基本不與人交往,只與照顧者簡單交往,能理解照顧者的簡單指令,有一定學習能力。監護下能從事簡單勞動。能表達自己的基本需求,偶爾被動參與社交活動。需要環境提供廣泛的支持,大部分生活仍需他人照料。”對精神一級的鑒定標準為:適應行為極重度障礙;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忽視自己的生理、心理的基本要求。不與人交往,無法從事工作,不能學習新事物。需要環境提供全面、廣泛的支持,生活長期、全部需他人監護。”
依據媒體報道的張某某及姚某瑞父母的描述,姚某瑞更符合精神一級殘疾的標準,也更符合《民法典》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特征。如果姚某瑞經鑒定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本事件中可能涉及以下法律問題:
1.二人“婚姻”的法律性質?依據《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四條的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又依據《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六條規定,結婚應當男女雙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對另一方加以強迫,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加以干涉。在婚姻登記環節,民事行為能力體現在能否準確表達其自愿成婚領證。而“自愿”的一個前提是有意識,如果無意識,就不存在自愿與否的問題。本事件中,姚某瑞明顯無法準確表達其意愿,所以民政部門聲稱無法為其辦理結婚登記。而確定婚姻關系,必須以登記為前提。姚某瑞沒有結婚的意識和意愿,所以無法通過結婚登記得到國家法律認可。
2.張某某是否涉嫌強奸罪?我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規定,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奸婦女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若違背婦女意志,強行與之發生性關系,即構成強奸罪的構成要件。根據媒體報道,張某某自述其與姚某瑞“已經同房,但姚某瑞不懂是怎么回事。”從中可以看出,姚某瑞欠缺發生性關系的承諾能力。如果經鑒定姚某瑞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張某某與之發生性關系,就可能構成強奸罪。但官方稱二人的同居并不違法,那么,二人在不違法的前提下同居,怎么可能避免發生性關系?這似乎是一個難解的命題。
3.姚某瑞父母是否構成遺棄罪?根據《民法典》第二十八條、第三十四條的規定,姚某瑞的父母是其監護人,對其有扶養義務。而張某某因不是姚某瑞的合法配偶不能成為她的監護人。雖然《民法典》第二十八條規定了“其他愿意擔任監護人的個人或者組織”,“經被監護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或者民政部門同意”,也可以擔任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的監護人,但是未見媒體報道中提及姚某瑞父母與張某某進行過姚某瑞監護權的變更。故而,姚某瑞的監護人依然是其父母。他們將女兒交與他人扶養,缺少監護人變更的法定手續。此種情形下,姚某瑞父母是否構成遺棄罪也有待討論。
【編輯:潘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