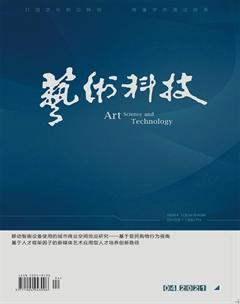《果醬拌水》與《暴風(fēng)雨》互文研究
摘要:?jiǎn)讨巍だ魇亲钤绯俗暗蹏?guó)風(fēng)馳號(hào)”移民英國(guó)的加勒比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主要書寫加勒比黑人被殖民的歷史以及后殖民時(shí)代殖民地人民在本土和宗主國(guó)的生活現(xiàn)狀,表達(dá)殖民主義、民族主義的政治主題。在《果醬拌水》中,作者從書名、人名、故事情節(jié)及人物命運(yùn)等幾個(gè)方面互文重構(gòu)莎翁名劇《暴風(fēng)雨》,在表現(xiàn)殖民主義題材的創(chuàng)作中有其獨(dú)特的藝術(shù)魅力。
關(guān)鍵詞:加勒比文學(xué);《果醬拌水》;《暴風(fēng)雨》;互文
中圖分類號(hào):I106.4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4-9436(2021)04-0-02
互文性即文本間性,是20世紀(jì)60年代克里斯蒂娃在《符號(hào)學(xué)》(1969)里闡釋的一個(gè)重要概念,是在其研究巴赫金的對(duì)話理論和狂歡化現(xiàn)象時(shí)提出的[1]。其基本含義是文本、話語(yǔ)與其他文本、話語(yǔ)的關(guān)系,或者兩個(gè)或兩個(gè)以上文本間發(fā)生的互文關(guān)系。從廣義上講,互文不僅包含參與最終文本的一切文本,還包括形成這一切文本的其他文本與話語(yǔ)[2];從狹義上講,互文主要指文學(xué)作品的起源、作用與互動(dòng),人們借此探討文本中通過(guò)引用、默示、諧仿等方法與已有文本建立的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互文研究強(qiáng)調(diào)多學(xué)科話語(yǔ)分析,主導(dǎo)以符號(hào)系統(tǒng)的共時(shí)結(jié)構(gòu)取代文學(xué)史的進(jìn)化模式,從而把文學(xué)文本從心理、社會(huì)或歷史決定論中解放出來(lái),以投入一種與各類文本自由對(duì)話的批評(píng)語(yǔ)境中。可以說(shuō),每一部作品的誕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各種經(jīng)典的影響,加勒比作家喬治·拉明(1927—)的小說(shuō)《果醬拌水》(1971)也不例外。
《果醬拌水》是喬治·拉明的第5部小說(shuō),與其第2部作品《移民》相似,描寫了幾位生活在倫敦的加勒比藝術(shù)家的遭遇及認(rèn)同危機(jī)[3]。無(wú)論是書名、人名、故事情節(jié)還是人物命運(yùn),《果醬拌水》都與莎翁名劇《暴風(fēng)雨》有互文的成分,只是殖民發(fā)生的空間有所改變,由邊緣轉(zhuǎn)向中心,《果醬拌水》也因此被學(xué)界稱為“生活在英國(guó)的凱列班們的故事”。本文擬從互文角度淺析《果醬拌水》與《暴風(fēng)雨》的關(guān)系。
1 “果醬拌水”的由來(lái)
拉明生于前英屬殖民地巴巴多斯,從小接受殖民教育,深受英國(guó)文學(xué)經(jīng)典的影響[4],拉明對(duì)《暴風(fēng)雨》爛熟于心并有意將其中的人物、故事情節(jié)等運(yùn)用到了小說(shuō)《果醬拌水》中。該書1971年在倫敦首發(fā),主要探討殖民、移民、流放等主題,講述了3位西印度藝術(shù)家的移民動(dòng)機(jī)以及在英國(guó)遭受的毀滅性影響。小說(shuō)在架構(gòu)上參考了《暴風(fēng)雨》,呈現(xiàn)出主要人物與大英帝國(guó)和本土島嶼之間的關(guān)系[5]。換言之,《暴風(fēng)雨》是《果醬拌水》故事情節(jié)及人物塑造的靈感源泉。首先,書名“果醬拌水”取自《暴風(fēng)雨》的第一幕第二場(chǎng):“你剛來(lái)的時(shí)候,用手撫摸我,疼愛(ài)我,給我里頭放了莓果的水喝,還教我怎么稱呼白天和夜晚發(fā)亮的大光和小光。那時(shí)候我愛(ài)你,帶你看島上的風(fēng)貌,淡水泉、咸水坑、荒地和沃土。我該死,竟那樣做!愿西考拉克斯一切蠱物——蛤蟆、甲蟲、蝙蝠——都降到你們身上。”[6]普洛斯彼羅初來(lái)乍到,像慈父一般關(guān)愛(ài)孤苦無(wú)依的小凱列班,給其“放了莓果的水”喝,并用自己的語(yǔ)言教育馴化凱列班,旨在使其成為一名忠實(shí)的奴仆,這杯莓果水是維系二者關(guān)系的情感紐帶,在普洛斯彼羅的荒島殖民統(tǒng)治中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7]。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成年后的凱列班為擺脫普洛斯彼羅的奴役和束縛,竟然用后者教給他的語(yǔ)言詛咒以普洛斯彼羅為首的殖民者,這時(shí),殖民語(yǔ)言扮演了負(fù)面角色,已然成為去殖民化的有力武器。凱列班的這一幕詞同時(shí)預(yù)示他欲與普洛斯彼羅決裂的決心[8]。拉明以“放了莓果的水”(果醬拌水)作為書名也暗示著小說(shuō)中3位藝術(shù)家所處的困境與《暴風(fēng)雨》中的凱列班并無(wú)二致,作者把這種處境描述為“最可怕的殖民方式:利用情感約束的殖民手段”。
從某種程度上來(lái)說(shuō),拉明是在逆寫旅程。在《暴風(fēng)雨》中,是普洛斯彼羅造訪了凱列班的荒島,在《果醬拌水》中卻恰恰相反。在《果醬拌水》中,他將莎士比亞這位出生于16世紀(jì)的劇作家的政治主題和那些出生于20世紀(jì)的后殖民藝術(shù)家的困境有力地聯(lián)系了起來(lái)[9]。
2 人名的互文及象征意義
褆頓理想破滅,孤獨(dú)難耐之際在荒原上偶遇作為米蘭達(dá)化身之一的米亞(Myra),試圖重新了解自己的過(guò)去[10]。在《流放的喜悅》中,拉明把米蘭達(dá)描述為“天真無(wú)邪的凱列班的另一半”,將凱列班形容成“米蘭達(dá)少女時(shí)代可能成為的殘缺部分”。在《果醬拌水》中,褆頓和米亞經(jīng)歷相似:他們失去純真、錯(cuò)位、疏離、被強(qiáng)取豪奪[11]。米亞是莎士比亞筆下那個(gè)天真無(wú)邪的米蘭達(dá)遭受性虐后幸存的化身,作為一名克里奧爾人,她首先跟隨父親被流放到圣克里斯托布爾,繼而在家園遭受同樣的命運(yùn)。她跟小說(shuō)中的凱列班們一樣顛沛流離、居無(wú)定所、地位卑微,是普洛斯彼羅殖民歷史的受害者[12]。她與褆頓的邂逅加深了后者對(duì)個(gè)人及其島國(guó)歷史的了解。小說(shuō)中米蘭達(dá)的另一半化身是褆頓的妻子蘭達(dá)(Randa),這可以從米蘭達(dá)(Miranda)一分為二的名字看出。為換取褆頓的人身自由,蘭達(dá)不惜委身于駐圣克里斯托布爾的美國(guó)大使,結(jié)果卻遭到褆頓的唾棄[13],她絕望之極,最終在圣克里斯托布爾自殺身亡,這與米亞在倫敦過(guò)著自暴自棄的娼妓生活異曲同工。
作為凱列班和普洛斯彼羅的翻版,拉明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無(wú)論在西印度還是在英國(guó)本土都表現(xiàn)出了殖民經(jīng)歷的方方面面[14]。普洛斯彼羅象征正在失去殖民勢(shì)力的大英帝國(guó):他是給島上帶來(lái)光明和知識(shí)的殖民者,是前種植園主,遭廢黜的暴君。凱列班代表整個(gè)加勒比,代表他繼承的島嶼,土生土長(zhǎng)的凱列班在殖民體系中被視為怪物、孩子和奴隸,但凱列班正是革命力量的源泉[15]。《果醬拌水》中燒毀高爾·布賴頓莊園并蹂躪普洛斯彼羅女兒米亞的動(dòng)亂就是凱列班反抗普洛斯彼羅獨(dú)裁統(tǒng)治的一種表現(xiàn)。
褆頓在荒原上向米亞描述的具有和解意義的靈魂儀式在《暴風(fēng)雨》中也能找到相似的事件:當(dāng)普洛斯彼羅呼風(fēng)喚雨將他的敵人同船一起沉入海底時(shí),無(wú)論是無(wú)辜的還是有罪的,都從水里復(fù)活了,與海地的靈魂儀式驚人地相似[16]。普洛斯彼羅是被殖民者無(wú)法回避的痛苦現(xiàn)實(shí)。拉明喜歡用海地靈魂儀式推進(jìn)生者與死者、現(xiàn)在與過(guò)去的對(duì)話,認(rèn)為這是一種從困擾和制約人意識(shí)的死者手里解放生者的途徑,為當(dāng)代新殖民勢(shì)力和尚未終結(jié)的舊殖民殘余提供了一次和解的機(jī)會(huì)[17]。
3 凱列班們的命運(yùn)
然而,靈魂儀式暗含的和解在小說(shuō)中并未實(shí)現(xiàn)。7年來(lái),獨(dú)立后的圣克里斯托布爾依然承受著英國(guó)的殖民統(tǒng)治,褆頓決心歸國(guó)奮戰(zhàn)[18]。他與房東高爾·布賴頓夫人多年的曖昧關(guān)系成為他看似容易跨越的障礙。從情感層面上講,對(duì)褆頓與高爾·布賴頓夫人關(guān)系的描寫,一方面展示出他對(duì)這個(gè)照顧自己的老婦人心存感激,另一方面也體現(xiàn)了褆頓為擺脫后者的過(guò)度束縛而努力抗?fàn)幍倪^(guò)程[19]。從象征層面來(lái)看,這映射出殖民地與母國(guó)的關(guān)系,暗示殖民國(guó)需要作出決斷才能脫離母國(guó)的控制,必要時(shí)還需付諸武力。費(fèi)爾南多的介入加速了二人關(guān)系的破裂,也導(dǎo)致了悲劇的發(fā)生。作者略去了謀殺的細(xì)節(jié),但顯然,褆頓為獲取自由不得已勒死了老夫人[19]。
相比之下,音樂(lè)家羅杰的自我毀滅則不盡相同。他討厭祖國(guó),移民英國(guó)是為了與自己的過(guò)去劃清界限[20]。他閉門造車,行為怪異——白天在自己的住處創(chuàng)作,夜晚到妻子的寓所歇息。他與妻子的關(guān)系在后者的容忍下勉強(qiáng)維持,直到妻子懷孕,危機(jī)才真正爆發(fā)[21]。妻子是白人,自己是黑人/混血兒,出于對(duì)血統(tǒng)不純的恐懼,羅杰否認(rèn)孩子是自己的。這是羅杰極度排斥自己與生俱來(lái)的種族文化混雜性特質(zhì)的有力象征,體現(xiàn)了其對(duì)自我的否定[22],這也從側(cè)面反映了他痛恨自己出生地的原因,因?yàn)槟鞘且粋€(gè)雜居成性的島國(guó)。他對(duì)尼科爾的依戀不足以說(shuō)服自己接受一個(gè)血統(tǒng)不正的孩子。在歐洲文化霸權(quán)面前,美國(guó)白人妻子對(duì)羅杰心理創(chuàng)傷的慰藉是暫時(shí)的[23],雖然她也來(lái)自前英屬殖民地,有著同樣的殖民經(jīng)歷。放棄自我的羅杰不能融入英國(guó)文化使其痛苦不堪,妻子懷孕更是加重了他的精神壓力。于是,在尼科爾失蹤自殺后,羅杰也終于精神崩潰,成為縱火狂。
演員德里克在各大劇院跑龍?zhí)祝┯驳氖w是他扮演的唯一角色,他沒(méi)有臺(tái)詞,只需聽(tīng)從指示擺出相應(yīng)的死姿[24]。七年如一日的僵尸演繹沒(méi)能讓德里克出人頭地,更不用說(shuō)一炮走紅,實(shí)現(xiàn)自己的明星夢(mèng),他在燈紅酒綠的倫敦只是一個(gè)無(wú)名小卒,得不到認(rèn)可,甚至被別人瞧不起,最終因強(qiáng)奸女主角未遂斷送了自己的前途[25]。
這3位好友最終因被指控謀殺、縱火、強(qiáng)奸等罪行鋃鐺入獄,這與《暴風(fēng)雨》中的凱列班企圖犯下的三宗罪及受到的懲罰極其相似[26]。
4 結(jié)語(yǔ)
《果醬拌水》對(duì)《暴風(fēng)雨》的互文明顯,在殖民主義霸權(quán)的影響下,拉明筆下的人物命運(yùn)是悲慘的,全然沒(méi)有莎翁戲劇里主要人物的美好結(jié)局。
凱列班作為一個(gè)無(wú)知懵懂的兒童登場(chǎng),此時(shí)他代表的是被殖民的初始狀態(tài),之后被流放異化成“他者”,最終覺(jué)醒,強(qiáng)烈反抗普羅斯彼羅,展示了其去殖民化的成長(zhǎng)過(guò)程。拉明對(duì)凱列班經(jīng)歷的描述,實(shí)則是對(duì)西印度人民慢慢覺(jué)醒、逐漸擺脫殖民歷程的間接反映,也是作者自身經(jīng)歷的呈現(xiàn)。
參考文獻(xiàn):
[1] 陸劍萍.顯性互文的象征表達(dá)——以《推銷員之死》和《拜金一族》為例[J].海外英語(yǔ),2019(16):208-209.
[2] 王富銀.莎士比亞戲劇兩譯本的翻譯倫理研究[J].英語(yǔ)廣場(chǎng),2019(10):13-15.
[3] 宋偉,成玉峰.從生態(tài)整體主義視角看人與自然關(guān)系——以電影作品《夢(mèng)》為例[J].英語(yǔ)廣場(chǎng),2020(15):42-45.
[4] 王旭霞.《海上無(wú)路標(biāo)》的藝術(shù)特色剖析[J].英語(yǔ)廣場(chǎng),2019(01):05-07.
[5] 劉婷婷,張弛.淺析《面紗》中的雙重東方形象[J].英語(yǔ)廣場(chǎng),2020(23):3-7.
[6] 莎士比亞.暴風(fēng)雨[M].彭鏡禧,譯.北京:外語(yǔ)教學(xué)與研究出版社,2016:17-18.
[7] 鮑志坤.《寵兒》象征主義分析[J].英語(yǔ)廣場(chǎng),2019(12):6-8.
[8] 陳桂霞.以深層生態(tài)學(xué)的價(jià)值觀論舍伍德·安德森筆下的“胡髭老人”[J].南京林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9(06):73-79.
[9] 呂鵬,張弛.庫(kù)切《恥》中的后殖民空間想象:帝國(guó)風(fēng)景、性別與動(dòng)物權(quán)利[J].考試與評(píng)價(jià)(大學(xué)英語(yǔ)教研版),2020(02):39-44.
[10] 欒雨菡,張弛.走出創(chuàng)傷的陰霾:《寵兒》中黑人女性主體性的構(gòu)建[J].英語(yǔ)廣場(chǎng),2020(25):3-6.
[11] 張柯瑋,張弛.《喜福會(huì)》中身份建構(gòu)的生態(tài)女性主義意義[J].英語(yǔ)廣場(chǎng),2020(12):3-7.
[12] 趙一霏,張弛.從存在主義女性主義看《秀拉》中女性主體意識(shí)的重建[J].英語(yǔ)廣場(chǎng),2020(08):3-8.
[13] 朱穎,張弛.“帝國(guó)的管家”:后殖民視閾下“史蒂文斯”的他者形象[J].英語(yǔ)廣場(chǎng),2020(05):8-11.
[14] 陳麗屏.《伊甸之東》的敘事空間解讀[J].名作欣賞,2018(9):66-69,139.
[15] 袁喜歡,胡斐.淺析《摩爾·弗蘭德斯》體現(xiàn)的女性主義[J].英語(yǔ)廣場(chǎng),2020(22):3-6.
[16] 潘鶯.基于榮格心理學(xué)理論淺析小紅帽蛻變之旅[J].英語(yǔ)廣場(chǎng),2020(01):9-10.
[17] 袁家麗.“權(quán)力的游戲”:《誰(shuí)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中的性別政治與文化協(xié)商[J].戲劇藝術(shù),2019(2):123-132.
[18] 奚昕.回歸與重塑——“人格發(fā)展理論”在英美文學(xué)通識(shí)課程中的實(shí)踐研究[J].江蘇外語(yǔ)教學(xué)研究,2019(1):49-51.
[19] 李思炎,戴雪芳.《黑貓》中主人公的畸形心理探究[J].英語(yǔ)廣場(chǎng),2020(22):10-13.
[20] 唐思怡,周莉.生態(tài)批評(píng)視角下對(duì)《走進(jìn)帕米爾高原》的研究[J].英語(yǔ)廣場(chǎng),2020(26):10-12.
[21] 朱蕾,王旭霞.覺(jué)醒的女性——論《蒔蘿泡菜》中薇拉的人物塑造[J].英語(yǔ)廣場(chǎng),2020(17):14-16.
[22] 陳紅梅.混沌的閾限:自我探尋·藝術(shù)抉擇·審美人生——以《他們眼望上蒼》為例[J].三峽論壇,2019(5):60-65.
[23] 田海榮,葛紀(jì)紅.淺析小說(shuō)《我彌留之際》中的創(chuàng)傷隱喻[J].英語(yǔ)廣場(chǎng),2020(5):8-11.
[24] 莊筱鈺,王旭霞.艾米莉·狄金森自然詩(shī)的生態(tài)女性主義解讀[J].英語(yǔ)廣場(chǎng),2020(26):29-32.
[25] 李芳.從合作原則看跨文化交際中的語(yǔ)用失誤[J].英語(yǔ)廣場(chǎng),2020(32):56-59.
[26] 鄭長(zhǎng)明.邊塞詩(shī)的認(rèn)知心理空間構(gòu)建[J].漢字文化,2020(21):210-212.
作者簡(jiǎn)介:王濤(1977—),女,重慶人,碩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語(yǔ)語(yǔ)言文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