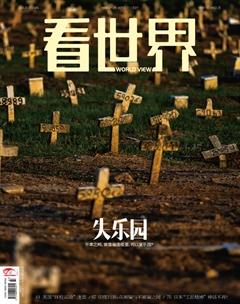印度行旅:在被騙與不被騙之間
索那瑜

加爾各答街頭市集
我在印度旅居近十年,始終抓不準被騙與不被騙之間那條隱微的界線。這條界線不僅關乎荷包,更關乎為人處世:沒能及早發現被騙,覺得自己笨;然而發現人家本心純正,從頭到尾都是自己多疑,覺得自己可恥。前后兩相比較,我還真不知道哪個自我感覺更加不良好。
行乞不是騙錢
每位計劃到印度旅行的人,都會做好被騙的心理防備:殺價至少先砍一半、不與路人說話、不讓陌生人幫忙拿東西、計程車一定要在政府的預付窗口叫……更有人叮嚀,印度嘟嘟車司機為了做生意會緊追不舍,走路時記得與車流反方向,如此一來他們就無法得逞。

舊德里城擁擠的街頭
記得第一次到印度旅游時,我緊張得像頭刺猬,草木皆兵,杯弓蛇影,好似與人說上兩句就會被騙似的,行走也必與車流逆向。過度緊張加上水土不服,我整日窩在麥當勞里一面吃漢堡一面跑廁所,在美麗的古城齋浦爾,我對那間麥當勞最有感情。
在當地生活好幾年后,我才逐漸卸下武裝,稍微放松,接受即使是當地人也偶爾會被騙的現實,也逐漸放開享受當地的風情與美景。
在被騙與不被騙之間,有件事是肯定的:要錢不是騙錢。印度行旅總免不了遇見乞丐,我時常在路口看見抱著嬰兒的婦女,或是穿著破爛的小孩。每逢紅燈車輛停下時,他們穿梭其間,一面拍著車窗,一面手指并成一個圈指著嘴巴,要你給他們吃飯錢。我也時常見到在路邊乞討的老人家,像是約好似的,每天在差不多的時間出現在同樣的地點。
關于施舍,我有自己的原則:不給小孩,不給年輕人,給老人。有段時間遭遇變動,心情不安,我莫名地鎖定了橋上一位非常老的奶奶,每次路過都給她10盧比。她又瘦又小,總是低頭蹲坐,披件咖啡色毛毯,瘦弱的右手掌向上垂攤著。我把10盧比鈔票放到她手中,她有時會抬頭看我一眼,有時只緩緩地將錢收進懷里。
我逐漸將老奶奶當成土地婆,給錢時心中默許愿望,竟也因而獲得平靜,隱隱感到靈驗,錢越給越多,從10盧比、20盧比到50盧比。老奶奶成了我的迷信對象。有次眼見快下雨卻沒帶傘,我跟朋友戲稱,我的老奶奶很靈,給錢許愿就不會下雨。結果,那次我真沒淋到雨。
還有一種乞討者,遇到她們我非常樂意打開荷包。她們叫海吉拉(Hijra),是印度當地的跨性別群體。她們多是裝扮成女人的男人,少數人有變性,類似賤民,不能從事任何體面職業,多數靠乞討為生。
海吉拉時常在大路口或火車車廂間穿梭,濃妝艷抹的她們乞討像討債,氣勢凌人,扭著蠻腰頂著大胸部趴在車窗前,一面拋媚眼,一面伸手要錢。如果錢的數目太少不滿意,她們會繼續糾纏;滿意時,則會用手摸你的頭,表演賜祝的儀式。
我第一次經歷整個頭頂被陌生人大手掌覆蓋抓住,身心受到極大的沖擊。此后,我倒是懂得享受那祝福的時刻,一掌下來,有人下手輕,有人下手重,都是實實在在的肉體接觸。她們喜歡糾纏有錢的男人,通常不會為難外國人,你給錢、她賜福,也是緣分一場。
騙與不騙,眾生平等
騙與不騙,也在對方的一念之間。
我第一次到德里旅游是在2007年,當時沒智慧型手機,沒有Google Maps與Uber,抵達機場已是半夜。我和旅伴依照旅游忠告,在政府的預付計程車窗口排隊,請司機帶我們到預訂好的旅館。半夜兩點多,街道空無一人。我們當時并不知道印度道路與門牌混亂,地圖不在司機心里,而是長在嘴上,若無人可供問路,大部分的司機是找不到確切地點的。

跨性別人士海吉拉
司機鎮定地在一間大房子前停下來,轉頭告訴我們說:“就是這兒了。”我和旅伴跟司機道謝,還特別給他豐厚的小費,下車后拖著行李走到大門,看了一下門牌,咦?門牌不對。回頭一望,司機還在原地,我們又回到車上,花了頗長一段時間才找到正確的地點。如今回想,當初若司機轉頭就走,路上空蕩蕩,天氣又非常寒冷,帶著大包小包行李的兩個女生真的有辦法平安度過那一夜嗎?到底當初司機是要騙我們還是沒有要騙我們?
而有次我在穆斯林小城Bijapur旅游,在路上找嘟嘟車帶我們參觀旅游景點,司機開價是書上寫的兩倍。我們一怒之下轉身要走,他將我們強攔下來,價錢談妥后,司機載著我們到處游玩,一面熱心幫忙拍照、建議地點、指導姿勢,一下午他自己也玩得挺開心。隔天清晨,我們步行前往一座清真寺。見著我們,他熱情地前來打招呼,還免費載我們一程,省下走路的時間。從騙我們到送我們禮物,中間的一線是時間與友誼。
有段時間我住在加爾各答,秉持著時時提防的態度,甚至到達被害妄想的地步,總覺得市場里沒有一家小販靠得住。走進傳統市場,我總是神經緊繃,覺得身上外國人的標記會使我成為小販欺騙的焦點。若細心偵查,我發現確實無時無刻不被騙。
例如,在質量不一的蒜頭叢中,挑選出自己滿意的一小把蒜頭,付錢時眼角卻瞥見老板將已放在秤上的蒜頭偷換幾個。那時我心中大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該為了幾顆蒜頭喊抓賊,還是自認倒霉呢?冷靜一想,畢竟只是幾塊盧比的小事,還是算了,大不了換一家。
海吉拉時常在大路口或火車車廂間穿梭,濃妝艷抹的她們乞討像討債,氣勢凌人。
幾個月下來,竟是每一家都在我心中打了叉叉。在魚市買魚蝦,我總是在旁觀察別人買了多少、付了多少,跟在當地人后頭買一樣的東西,或至少貨比三家,花時間講價。有次買蝦,看品質頗好,也談了好價錢,我買了一公斤,回家心里有打勝仗的喜悅,誰知道下回再去,跟另一攤買時竟發現,上回根本只拿了半公斤,價錢雖好,分量卻只有一半!
那日起,我總覺得自己的愚蠢早已在市場傳開,每次走進市場都會聽到不同的小販喊我:“小姐,小姐,來買蝦吧。”
與朋友討論買菜之難,朋友說:“我從不買菜,老是被騙,太困難了。”原來,當地小販也并沒有歧視外國人,文化如此,價錢即關系,誰都說不準。關系好、了解行情的獲得好價錢,關系差、看起來一頭霧水的就差一些,這是當地的潛規則。
我在印度遇到過真正的欺騙,如今回想起來還像是場夢。
每個家庭都有負責采買的成員,由該人負責了解價格波動與建立關系。在我朋友家,父親負責采買,他喜歡在市場里交朋友,也頗得意自己砍價的能力。但有次,我親眼看他買回一大袋蘋果,打開里頭都是爛的,心底竟偷偷浮起大大的笑意,感到相當釋懷,原來關系再好也難免會被騙。不分在地外來、男人女人、資深資淺,人人都生活在被騙與不被騙之間,也不能說不是種眾生平等。
一次背脊發涼的欺騙
嚴格上來說,喊價并不算欺騙。我在印度遇到過真正的欺騙,如今回想起來還像是場夢。
一位師長來印度授課,我建議走訪“金三角”:德里、泰姬瑪哈陵與齋浦爾;從德里到齋浦爾5小時的旅程別包車,體驗火車,速度快、平穩,沿路送茶、送點心,可享受殖民時期印度的英式服務。

印度古爾岡,街頭求助警察的婦女

印度古爾岡,抱著嬰兒的流浪婦女

穆斯林小城B i j a p u r 的古爾·岡巴茲陵墓
火車清晨出發,我們到達火車站時天還沒亮。在我們找月臺時,一位穿著白衣的站務人員操著一口好英文將我們攔下,問我們車號多少,幾點的車,到哪里。聽畢,他說:“你們的火車已經被取消了。”我一臉驚慌,問他怎么會這樣,怎么辦?他鎮定地說:“你們快去月臺換票,半小時后有另一班火車從另一個火車站出發,你們現在趕去還來得及。”
我心里非常惶恐,但為了表現“在地”,回頭跟老師說:“也不是沒可能,最近有些大型抗議行動,可能受到影響。”我們匆忙到了售票窗口,發現時間太早,售票窗口還沒開。這位站務人員恰好前來,見我們買不到票,就在紙上寫了個地址說:“你們到這個辦公室,那里的人可以幫你們換票。要趕快不然會來不及!”他還熱心地幫忙叫計程車,幫我們用印地語和司機溝通。
我們手忙腳亂地上了車,上車坐定后,問計程車司機價錢。他說了一個不合理的價格,同行的朋友心生警覺,說:“也太貴了吧,不是很近嗎?太奇怪,為什么火車取消沒有收到簡訊通知呢?不對勁!”
我們馬上跟司機喊停,下車回到車站,發現火車并沒被取消,一切如常,那位貌似站務先生的人也已消失了。如果我們當時跟著計程車走,他會帶我們去哪里?一走,鐵定錯過火車,他們會得到什么好處?回想起來,真是背脊發涼。
2015年德里地方選舉,反貪腐運動起家、以平等與窮人利益為宗旨的小黨AAP大勝右派BJP(印度人民黨)。AAP市長候選人Arvind Kejriwal宣傳說自己是“誠實主義者”,不像對手BJP是“投機主義者”。
開票當天,AAP首次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我記得當時的街道空氣中彌漫著奇異的愉悅與歡喜。一整天搭嘟嘟車,司機都主動跳表,無須喊價,仿佛就在那一瞬間,全城上下都決定跟著新市長當個誠實主義者了。
在被騙與不被騙之間,存在的是文化、是生活、是社會、也是政治。當代科技的電子監控與搜尋系統,使得今日印度旅游更加安全方便,但也似乎使得存在于被騙與不被騙之間的那塊曖昧又奇妙的空間,從旅游地圖中消失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