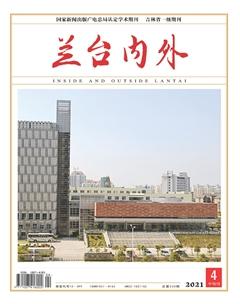1930年廢兩改元在重慶的實施
付毓澤
摘 要:1930年駐重慶的二十一軍軍部下令廢兩改元,此次廢兩改元由于軍閥割據和重慶特殊的貨幣金融環境對重慶經濟社會的影響并不大,但卻是重慶幣制走向規范化的重要一步,符合近代以來經濟社會發展對統一市場、統一國家的內在訴求。而廢兩改元在重慶的實施是民國以來軍閥割據地區的突出代表,是割據軍閥在統一地方過程中控制金融、鞏固統治的重要措施。
關鍵詞:重慶;廢兩改元;軍閥割據
1933年南京國民政府明令全國實施廢兩改元,這是中國金融近代化進程中一個重要事件,對當時經濟、社會、政治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學界在探究其原因、過程、影響等的同時也注意到廢兩改元在地方的實施,但關注多焦距于國民政府控制區域,未曾深究軍閥割據地區廢兩改元的實施情況。民國以來,四川軍閥割據混戰冠絕全國。重慶作為西南地區最重要的商埠,在西南地區金融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但由于軍閥混戰,金融動亂頻繁,經濟發展極為緩慢。雖然1926年劉湘入駐重慶,并將重慶作為“根據地”加以經營,重慶的經濟得以恢復并有一定的發展,但當時劉湘在重慶的統治并不穩固,直到1930年劉湘成為四川軍閥勢力最大者之一。此種背景下,1930年二十一軍軍部的金融改革看似是應對金融動蕩的一次“救市”行為,實際上卻是以劉湘為首的軍閥集團統一四川過程中加強對重慶金融業控制的重要措施。
一、1930年以前重慶的金融狀況
1.紊亂的幣制環境
重慶作為西南地區最重要的商埠,在西南地區金融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自民國以來,四川政出多門,金融管理體制極為混亂,金融業成為軍閥籌措軍費聚斂財物的工具,鑄造金屬貨幣和發行紙幣則是主要手段,由此導致四川幣制紊亂達十幾年之久。四川經濟考察團在《四川內地金融考察報告》中就言到:“在法幣推行以前,四川的幣制最為復雜,軍人可任意設廠鑄造銀幣銅幣,各縣商會亦可隨意發行流通券,或鑄造鉛類之硬輔幣,銀行、錢莊不經政府許可發行鈔票或類似鈔票的兌換券,幣制之紊亂,幾不可究詰”。
重慶幣制雖然紊亂,卻有自己的特點。銀兩在重慶的使用,民國以來全四川的銀平差不多已經統一于成都的九七平,重慶也不例外。并且由于“歐戰以后,各國積極進行其傾銷政策,川省洋貨進口激增,出口貨物減少。川省貿易以上海為樞紐。故申渝匯兌上之價格,因進口之不平衡,常處于不利地位。于是川省銀錠因申匯高昂,源源流出。而九七平之于川省,遂漸成為會計上之虛本位”。
銀元在重慶的使用,早在光緒十八年(1892)川東道就曾飭令巴縣知縣,流通重慶市場上的各省銀元均統一按照七錢一分折算使用,并成為定律。民國以來,重慶市面上流通的銀元種類逐漸增多,但“因川省政治不能統一,劉湘統治下之重慶,仍保持每洋一元合銀七錢一分之定價”。劣質銀元如赤水大洋和合川大洋等在重慶的流通則受到一定規范,“流通市面,惟重慶市面商人,自來拒絕行使成色不足之銀幣。及一切半元兩角雙毫等幣,官方亦未加以勉強,故獨得免幣制紊亂之害”,所以重慶不同于上海等地存在洋厘行市情況。另一方面,重慶對外省的貿易以上海為大宗,對于其他各地的匯價均以申匯為標準折算,省內貿易則多以九七平為折算標準。所以“兩元并用”的存在對重慶經濟社會的影響并不大。
2.不發達的銀行業
近代以來“兩元并用”的存在,給中國幣制帶來了極大的混亂,嚴重影響國內財政金融的運行和國內外貿易的結算,不利于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所以國內關于廢兩改元,統一幣制的呼聲一直存在。據估算,1925年,外商銀行、本國銀行和錢莊的資力比重(包括實收資本、公積金、盈利滾存、存款和發行兌換券等五項)占比分別為36.7 %、40.8%、22.5%。本國銀行業雖發展迅速,但在“兩元并用”貨幣制度下卻受限于掌握洋厘、銀拆和票據交換的錢莊行業。而且幣制的紊亂和貨幣價格的漲落導致銀行結算業務的復雜化和對會計的依賴進而影響銀行業務的發展。1921年,劉子健在《銀行周報》就發文言到:“然者欲謀會計上整理之最便利者,非劃一幣制不可;欲劃一幣制,非先自廢兩改元實行起不可”。而貨幣不統一不僅不利于商貿往來,也加大了交易成本,所以商界早就對銀兩制度反感,并一直努力請求幣制改革。故而廢兩改元尤以上海、天津等新式銀行發達,貿易遍及國內外的金融貿易城市最為積極。
1899年中國通商銀行在重慶設立分行,重慶才有了第一家銀行,之后各式銀行相繼在重慶成立或設立分行,銀行業在重慶逐漸興起。辛亥革命后,由于軍閥割據混戰,無論是官辦或是商辦銀行都面臨軍閥的攤派勒索,銀行業務幾度陷入停滯狀態。而且,“各銀行雖組織大致模擬外國方式,而經營銀行業務則類似本地錢莊,即:對各錢莊及個人皆按其信用及聲譽便貸與款項,不需任何擔保品。銀行與錢莊的唯一差別似乎就是銀行放款所取利息低于錢莊所取利息的0.2%”。據1934年中國銀行年鑒顯示,當時重慶有銀行總行8家,分行11家(9家為本地銀行分行),共19家;天津則有總行10家,分行39家(19家為本地分行);上海有總行59家,占全國總行百分之四十,分行111家(71家為本地銀行分行),占全國分行總數百分之十以上,共計170家。重慶銀行業在當時無論是規模還是業務發展都不算發達,更無法和上海、天津等地相比。
二、1930年重慶廢兩改元的實施
雖然1926年劉湘占據重慶,重慶的局勢漸趨穩定,地方經濟得以恢復并有一定的發展,但當時軍閥混戰的大環境并不能給予劉湘安穩發展的機會。1927年到1929年,劉湘打敗了羅澤洲、楊森、賴心輝等軍閥,占據重慶、萬縣、奉節等二十余縣,總兵力約十萬人,成為四川軍閥勢力最大者之一,而且還獲得了國民政府的支持,劉湘在重慶的統治才算真正穩定,由此更加注重對重慶的經營,就有了1930年的金融改革。
此次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以本票取代劃條。重慶“劃條”制度發端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其初原因用現不便,始以書面劃撥替代。其后因現金缺乏,遂引架空之幣。竟將劃條與現金判而為一,演出補水問題”。民國十九年,重慶市面現金枯竭,現洋貼水每千元達五十元之巨,不僅影響商貿往來,而且對二十一軍每月所需數十萬軍餉也造成極大影響。所以軍部不得不對重慶金融進行整頓,將廢兩改元列于第一步則是因為錢莊劃條以銀兩為單位,廢兩改元實則是避免錢莊有所借口。而此次廢兩改元相對當時重慶的幣制環境而言影響并不大,正如成緒所言“于市面固屬無礙”“僅廢一轉賬手續”。從1932年重慶市商會致上海市商會的復函中也可看出廢兩改元對當時的重慶商貿往來影響并不大。
1.從本年(1930)十月一日起,凡渝埠各商所立各種票據,上面金額,一律改兩為元。
2.改兩為元時,每銀一元,仍照向例以九七平生銀七錢一分合算。
3.各商號所立賬簿,其登記金額,從十月起,即陸續改兩為元。限至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一律改完,以便二十年一月一日實行查驗。
4.由渝匯至各地交付之款,查照各該地通用貨幣立票,渝埠登賬,仍記成元數。
5.其由各地匯至渝者,無論票面如何記載,仍以元數登賬。渝埠向有各種折扣規例,一律照常辦理,毫不變更。但不得與改兩為元之案,發生妨礙。所有票據賬摺,登記數目,均須改兩為元。
6.議決各項,即由商會轉呈川東南工商業整理委員會核定,通知各幫照辦。
1930年二十一軍軍部的金融改革既是一次“救市”行為,也是以劉湘為首的軍閥集團加強對重慶金融業控制的開始。據統計,劉湘獨占重慶的近10年間,逐步把持了重慶的金融業,重慶的商業銀行被劉湘搜刮的資金,已占銀行業全部資產的56%和錢莊業的60%。1930年開始他們通過創辦或入股銀行、錢莊等方式逐漸控制重慶金融,重慶銀錢業“而其有軍政人物之資本關系者,約在十分之八以上”。此后,又試圖通過“糧契稅券”統一重慶幣制,并設立金融匯兌管理處對匯兌進行控制。也正是因為他們控制了重慶金融,又為他們濫發紙幣、恣意搜刮提供了條件。實際上,劉湘對重慶金融業的整頓是為避免金融崩潰基礎上的更好掠奪。此次廢兩改元雖然對重慶經濟社會的影響并不大,但卻是重慶幣制走向規范化的重要一步,在法律層面結束了重慶金融市場上紋銀的使用。
三、廢兩改元與軍閥割據
各地廢兩改元實質上是國民黨在建構統一的國家權力過程中與地方勢力之爭,廢兩改元的成功與否取決于國民政府政治控制力與財政實力。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統一經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1928年,國民政府在上海召開全國經濟會議,財政部長宋子文在開幕詞中言到:“(甲)金融,以我國枯竭紛亂之金融如何整理,各省參差幣制如何統一,濫幣如何整理,以鞏固金融之根本”,會議審核通過的《國幣條例草案》第一條就規定:“國幣之鑄發權專屬國民政府”。1929年,國民政府邀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美國財政專家甘末爾等來華為中國幣制改革設計方案,進行所謂的“甘末爾計劃”。這些廢兩改元整理幣制的嘗試最終因各種原因未曾實施或以失敗告終,但無不顯示出國民政府統一幣制、整頓金融的決心。
1927年和1928年,國民政府曾試圖干涉四川軍政,但卻引起四川軍閥的聯合反對,《國民政府整理川政令》中所謂“全省幣制,應即整理劃一,各處造幣機關一律撤除,不得再鑄惡幣,致紊金融”也就成為一紙空文。1933年國民政府下令廢兩改元,此次廢兩改元雖然在地方的實施并不徹底,但卻加強了中央對全國經濟、金融的控制力。1934年,國民政府就以擾亂幣制為由飭令劉湘控制下的重慶銅元局停鑄漢字銀元,并將模具上繳毀廢,表明軍閥在地方的統治被削弱。
民國以來,中央權力不張,地方軍閥割據,廢兩改元的實行既有中央主導,也有地方自主實行,廢兩改元實際上也成為割據軍閥統一地方過程中控制金融、鞏固統治的重要措施。1919年閻錫山掌握山西軍政大權以后,就先后頒布多項劃一幣制的政令對山西幣制進行整理,進而逐漸壟斷山西的金融業。1930年廢兩改元在重慶實施實際上也是以劉湘為首的軍閥集團在統一重慶過程中加強對重慶金融控制的重要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28年控制成都造幣廠的鄧錫侯就曾下令恢復以“大洋”為一切營業交易的法償,下令停滯鑄造減成色和減重量的錢幣,并將劣幣鑄镕改造良幣。其他軍閥見鑄造劣幣無利可圖便也陸續將造幣廠關閉。廢兩改元的實質:“是近代經濟發展導致錢莊掌握的銀兩體系限制了銀行的金融業務空間,從而引發了銀行與錢莊業務上的矛盾或競爭;同時政府稅收使用銀元并通過銀行利用公債(標的物也是銀元)籌資(而錢莊卻無此功能)。故而政府和銀行合力消滅銀兩的勢力是當時經濟環境下政府、銀行、錢莊三方博弈的結果”。重慶廢兩改元的實施實際上也是因為鑄造金屬貨幣已經無利可圖,以劉湘為首的軍閥集團對重慶金融的掠奪開始轉變為以創辦或入股各類銀行,通過發行紙幣、債券等方式為主。
四、結語
民國以來,四川軍閥混戰冠絕各省,重慶作為四川金融中心,1930年廢兩改元成為軍閥割據地區的突出代表,是割據軍閥在統一地方過程中控制金融的重要措施。而軍閥對金融業的整頓是為避免金融崩潰基礎上的更好掠奪;是軍閥對金融業的掠奪轉變為以創辦或入股各類銀行,通過發行紙幣、債券等方式為主;也是近代經濟社會的發展對統一國家和統一市場的內在訴求。
參考文獻:
[1]西南經濟調查合作委員會編.四川內地金融考察報告[M].獨立出版社,1939年
[2]黎 文.重慶金融市場考略[N].銀行周報,第十卷第九期,1926
[3]重慶中國銀行編.四川金融風潮史略[M].重慶中國銀行,1933
[4]重慶金融編寫組編.重慶金融上[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
[5]四川金融極紊亂[N].銀行周報,1933
[6]洪葭管.廢兩改元[J].中國金融,1988
[7]吳景平.評上海銀錢業之間關于廢兩改元的爭辯[J].近代史研究,2001
[8]劉子健.對于廢兩改元后銀行會計改組之商榷上[N].銀行周報,1921
[9]周 勇,劉景修譯編.近代重慶經濟與社會發展1876-1949[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1987
[10]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經濟研究室.全國銀行年鑒[Z].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經濟研究室,1934
[11]成 緒.重慶市之廢兩改元[N].銀行周報,第十四卷第五十期,1930
[12]廢兩改元問題之討論:四川省早已實行廢兩[N].銀行周報,第十六卷第三十六期,1932
[13]周 勇主編.重慶通史[M].第二冊第二版.重慶:重慶出版社,2014
[14]張禹九.四川之金融恐怖與劉湘東下[N].銀行周報,1934
[15]金融:貨幣:二十一軍謀統一戍區幣制[N].四川月報,1933
[16]金融:二十一軍部設立重慶金融匯兌管理處[N].四川月報,1934
[17]陳海忠.從汕頭到上海:國民政府的“廢兩改元”之路(1925—1933)[J].近代史學刊,2019
[18]1928年全國經濟會議史料(一)[J].檔案與史學,1995
[19]一九二八年全國經濟會議史料(四)[J].檔案與史學,1996
[20]四川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川省志附錄.[M].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3
[21]孔祥毅主編.民國山西金融史料[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3
[22]戴建兵.白銀與近代中國經濟(1890-1935)[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作者單位:重慶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