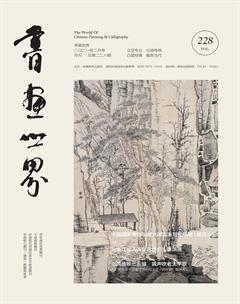古意新韻 古法新知
馮健



王云舒
王云舒,號虛谷子,云溪草堂主人,江蘇沛縣人。1998年畢業于南京師范大學美術系,曾作為訪問學者赴臺北文化大學交流學習。現任天津詩詞學會副會長、天津畫院特聘畫家、榮寶齋畫院特聘畫家、江蘇省青年美術家協會理事、江蘇書畫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天津美術家協會理事、榮寶齋(天津)總經理。在臺北、山東滕州、江蘇徐州和四川成都等地舉辦聯展和個展數次。曾出版《林泉高致——王云舒中國畫邀請展作品集》(臺北百香里出版社,2014.)、《當代中青年書畫名家——王云舒書畫作品集》(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作品被人民大會堂、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臺北中華全球文創協會、徐州市博物館等多家機構收藏。
畫家王云舒先生是我的同鄉,又是好友,因而我經常有機會拜讀他的一些大作。他囑我寫篇短文,談談對他繪畫作品的看法。我本人雖閑來畫些大寫意花鳥,山水也偏好野逸豪放一路,實際上在云舒兄所擅長的工細一路山水畫方面了解得并不多。但藝術都是相通的,我愿意結合自己對中國畫的理解和對云舒兄創作狀態的了解,談談對他近期作品的一些感受和認知,也許能為讀者們解讀他的作品提供別樣的視角,算是拋磚引玉吧。
北京大學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北京大學燕園印社社長
中國山水畫肇于魏晉,發展于隋唐,盛于宋元。明清以降,山水畫總體上已開始走下坡路,尤其是清代“四王”及其追捧者陳陳相因,完全在古人范本里討生活,山水畫所應該具有的生氣、生機幾乎被掩埋了。“四僧”的崛起,似乎讓人們看到了山水畫的希望,尤其是石濤提出“搜盡奇峰打草稿”,山水畫似乎又逐漸恢復生機。近現代以來,又出現了黃賓虹、李可染、陸儼少、黃秋園、陳子莊等一批有影響力的山水畫大家,尤其是黃賓虹,既集古人之大成,又把自然山河儲于胸中、現于筆下,將山水畫的用筆、用墨技術及內涵圖式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對后世影響深遠。今天的山水畫家有壓力,也有機遇。壓力在于,前人已經把創新之路幾乎都走盡了,如何再出新、如何有效地處理繼承傳統與創新的關系,是一個艱巨的課題,需要畫家窮其一生精力艱苦磨煉甚至慘淡經營;機遇在于,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步伐加快,城鄉面貌日新月異,時代賦予畫家謳歌大自然、反映社會進步的激情,這些激情轉化為繪畫創作的動力,使得創新仍然存在機遇。
和眾多畫家一樣,在新時代的快速發展節奏下,王云舒也要面臨繼承傳統和有效創新這一畫家們都需要面對、無法回避和竭力尋求突破的永恒主題。王云舒在擔任榮寶齋天津分店總經理之前,曾經數度北上,通過集中式學習以提高繪畫水平。他先在榮寶齋畫院郭石夫先生的高研班上學習寫意花鳥,后來又在國家畫院程大利先生的高研班上學習寫意山水。程大利先生的教學思想非常明確,要求先要深入傳統,系統地鉆研和掌握古法,與此同時,注重寫生和“行萬里路”,也就是說“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王云舒受到程大利先生治學及教學思想的影響,在學習傳統尤其是宋元山水畫傳統方面投入了極大的精力。他經常通宵達旦地臨摹古畫,有時一幅畫能臨上兩三個月。僅是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他就臨摹過多遍,不僅按原大小來臨,還放大臨,通過這種方式,對古人的用筆、用墨方法有更深刻的認識和體會。他學習宋人的山水畫一度進入癡迷狀態。他說越臨摹越感覺到宋畫的精妙,宋畫里有很多微妙的內容,只有深入進去才有切身體會。他及時地把對宋元繪畫學習的心得用于自己的創作實踐中,取得了顯著效果。
在五代及宋元山水畫這一系統里,他學習較多的是董源、巨然、李成、范寬、黃公望、吳鎮和倪云林等。明清以后的山水畫家中,他吸收過文徵明、龔賢、弘仁、查士標等畫家的一些畫法。按照董其昌繪畫南北宗的劃分,他取法的對象都是南宗畫家,也就是文人畫家。值得一提的是,他對清代的龔賢尤其偏愛。我曾欣賞過他收藏的龔賢八尺條幅真跡,其作品中的靜穆之氣和渾然天成的氣息令人震撼。真跡在側,他常常焚香靜品,細細研讀前輩大師的用筆、用墨之法,無疑這是他學習龔賢的得力之處,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他在很多山水畫里都有意無意地用了龔賢的筆法。我個人也非常欣賞他借鑒龔賢筆法的一系列山水作品。這些作品有筆有墨,以墨本為主,縱然用色也設色淡雅,古意盎然,頗有韻味,令人生出撫今追昔的情懷。
《莊子·知北游》中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五代荊浩《筆法記》中說:“畫者,畫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真者,氣質俱盛……”天地不會說話,更不會畫畫,故天地不能自言其美,必欲人為之代言其美、為之代畫其美。那么人又如何代言天地之美呢?既要“取其真”,還要“知其術”。荊浩告訴我們:“物之華,取其華;物之實,取其實。不可執華為實。若不知術,茍似,可也;圖真,不可及也。”也就是說,“取其真”是古人山水畫的目標,那就是要真實地再現自然之美;“知其術”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不學習古人,不對古代名家畫法做深入鉆研,如何“知其術”?道理不言自明。云舒兄曾經感嘆,北宋人以描摹自然物象為第一目標,對繪畫風格的追求倒在其次,而且風格自然形成;南宋人則過于突出個人繪畫風格,這是北宋和南宋山水畫最顯著的區別。這說明他已經深諳古人“取其真”的道理。只要做到了“真”,便可“氣質俱盛”,古人早已講得明白透徹。云舒兄在學習古人方面下了如此大的功夫,我猜想是為了“知其術”,這些功夫都不會浪費,最終將有助于其實現在繪畫上的抱負。
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世之篤論,謂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為得……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謂此佳處故也。故畫者當以此意造,而鑒者又當以此意窮之,此之謂不失其本意。”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一直是古人評價甚至臥游一幅山水畫的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但是,僅“可行可望”還不行,還得“可游可居”,后者才是山水畫的更高境界,是畫者、鑒者不失其本意的“意造”。觀王云舒的山水畫,可謂四個要素皆備。在他的畫中,可行、可望是必備功能,而可游、可居似乎也早已不是難事。我曾見他為萬柳書院繪制的一幅佳作,畫中寒林蕭瑟,遠山隱約,一老者攜童負琴,臨水遠眺,一條小徑蜿蜒至山后,意境頗為幽遠。畫面雖著墨不多,但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兼備,畫面的大面積空白令觀者生出無限遐想。此時無墨勝有墨,畫家的手段令人拍案叫絕!
郭熙的畫論中有一段論述四季山水評價標準的文字,即“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凈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有趣的是,我在云舒兄的淡墨山水中,似乎找到了郭熙所描繪的四季山水的感覺。不難看出,郭熙畫論中的四季山水有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淡、凈、雅。云舒兄擅長淡墨寫實,除了偶爾用濃墨點苔提神以外,濃墨很少在他的筆下出現,“清淡”和“雅凈”成了他山水畫作品的主旋律,恰恰符合郭熙描繪四季山水的淡、凈、雅的標準。尤其是在他近兩年所創作的山水畫作品中,他更加強調“淡”的特征,畫面處理得干凈整潔,似乎一塵不染。在古詩文中,“淡”是一個不易得的境界,古人對此多有論述。在王云舒的筆下,近山遠岫,溪水寒林,蒼松翠柏,古廟野徑,山居煙霞,無不符合“淡墨云山”的標準,無不聯系著一個“淡”字。正所謂“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荏苒在衣”,云舒兄的淡墨云山正是畫家在繪畫中追求司空圖“沖淡”詩品的典型案例啊!古人說“墨非蒙養不靈,筆非生活不神”,可以肯定的是,云舒兄的淡雅筆墨也是經過多年的苦修蒙養而得。這既需要畫家的天性和天分基礎,又需要多方面的后天修養保證。這真是怎一個“淡”字了得,怎一個“難”字了得!
石濤在《苦瓜和尚畫語錄》中專設了“了法章”,既強調“規矩者方圓之極則也”,又強調“人之役法于蒙,雖攘先天后天之法,終不得其理之所存,所以有是法不能了者,反為法障之也”。大意是說,法雖重要,理也重要。現代畫家張大干主張,畫家要了解物理、物情、物態。陳子莊論畫則強調“機趣”,他說:“繪畫須通‘心靈,須得‘機趣,此四字,論及者寡,能做到者更少。”總而言之,古今畫家對中國畫旨要的概括大致要包括“法”“理”“意”“趣”四字,得此四字,畫事備矣。
云舒兄近年鉆研傳統山水古法,尤其是對于宋元傳統頗有心得,對于明清流派了如指掌,可謂得一“法”字。他用研習古畫所得的傳統用筆方法描繪和表現現實中的山水,并賦予其時代特征和新的認知,已能做到“古法新知”。近年,他組織和帶領榮寶齋(天津)新銳藝術家團隊外出寫生,走遍祖國大江南北、三山五岳,實踐“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治學精神,體察物理、了解物情、把握物態,積累了大量的寫生素材并積極促使寫生向創作的及時、有效轉化,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可謂得一“理”字。
“意”可以通“心”,所以古人講“寫意”即“寫心”。“趣”有不同的類型,陳子莊、齊白石、崔子范有“童趣”,天真爛漫化為生機而生機無限。黃賓虹、潘天壽也有趣,但更多的是理性之趣、成人之趣,此“趣”亦可為嚴肅的法度增添輕松氛圍,“一張一弛”成就文武之道。然而,“趣”可遇而不可求,故石濤說“神遇而跡化”。近年云舒兄畫淡墨云山,強調筆筆寫出,甚有古意新韻,其“意”了然于胸中矣。近年云舒兄著意探討新的構圖方式,以與前人拉開距離,其“趣”不求而自有趣在。總體上,“法”“理”二字,已臻高度;“意”“趣”二字,慘淡經營,料不日可期大成!
約稿、責編:金前文、史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