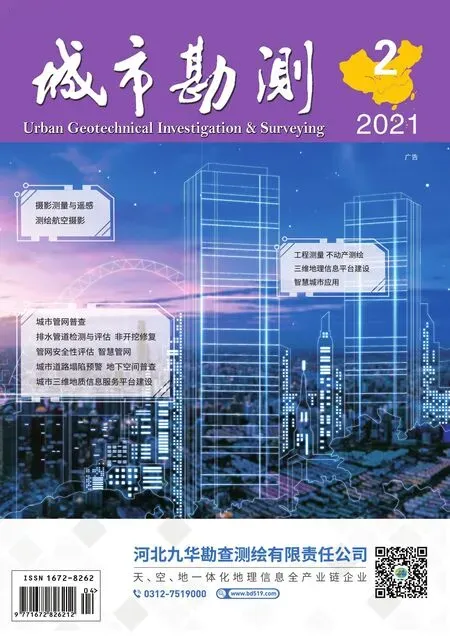基于“三生空間”的昆明市國土空間結構演變特征分析
王菊,趙俊三,林伊琳,龍利秋,李玉龍
(1.昆明理工大學國土資源工程學院,云南 昆明 650093; 2.智慧礦山地理空間信息集成創新重點實驗室,云南 昆明 650093;3.云南省高校自然資源空間信息集成與應用科技創新團隊,云南 昆明 650211)
1 引 言
國土空間是人類生存發展和實施各類生產活動的載體,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快速城鎮化過程,帶來了國土空間格局的劇烈演變[1]。在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同時,人地關系矛盾、土地資源低效利用、環境污染、城鄉發展失衡等問題日益顯現,對我國的國土空間可持續開發帶來巨大挑戰[2]。在此背景下,研究區域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的結構、數量、分布的變化情況與趨勢能為優化區域國土空間格局,實現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提供科學依據。
自十八大召開以來,有大量學者就國土“三生空間”用地的概念與內涵[3]、“三生空間”用地分類[4,5]、“三生空間”綜合承載力[6]、“三生空間”用地的時空格局與演變、優化[7~9]等開展研究,但研究尺度主要集中在流域[10],城市群[11]和省域[12],對市域和縣域的研究甚少。
目前對昆明市國土空間開展的研究主要是以昆明市下轄的區[13,14],縣[15]為研究對象,難以反映全市國土空間結構演變特征。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快速發展,昆明市作為云南省的省會城市和滇中城市群發展的核心地帶,在經濟迅猛發展的同時,其土地利用發生了劇烈變化,所以研究整個昆明市國土空間結構演變特征,能為優化昆明市國土空間提供重要參考。
2 研究區概況及研究方法
2.1 研究區概況
昆明市是云南省的省會城市,地處云貴高原中部,位于東經102°10′~103°40′、北緯24°23′~26°22′,市域土地總面積 21 012.53 km2,下轄7個區、3個縣、3個自治縣,代管1個縣級市,即五華區、盤龍區、官渡區、西山區、呈貢區、東川區、晉寧區、富民縣、宜良縣、嵩明縣、石林彝族自治縣、祿勸彝族苗族自治縣、尋甸回族彝族自治縣、安寧市(圖1)。

圖1 云南省,昆明市行政區劃圖
2.2 研究方法
(1)數據源與預處理
本文研究的數據是來源于土地利用現狀年度更新數據庫的2009年和2015年土地利用現狀數據,借鑒最優樣方尺寸計算方法[16],根據昆明市市域面積,將研究區劃分為 500 m×500 m的柵格單元,并運用ArcGIS 10.2軟件將這兩期土地利用數據統一到該柵格尺寸下,再根據中國土地利用/土地覆蓋變化遙感監測數據分類,結合昆明市土地利用實際情況,并借鑒已有研究成果[11,17]中“三生空間”的分類方法和思想,自下而上識別昆明市國土“三生空間”格局,以建立研究區國土“三生空間”分類體系(表1)。

昆明市國土“三生空間”分類與土地利用類型銜接 表1
(2)研究方法
本文用ArcGIS 10.2和Fragstats 4.2軟件,采用土地利用動態度[18]、重心遷移模型[19]和土地利用轉移矩陣[20]等方法從數量變化、重心遷移和轉移特征等方面分析研究昆明市國土“三生空間”的結構特征,探尋其空間結構變化的過程和差異;采用景觀格局指數法[21]從斑塊類型和景觀水平兩個尺度進一步分析景觀格局與國土空間結構之間的動態變化規律,空間演變異質性及關聯性。
3 昆明市國土空間結構演變分析
3.1 國土空間數量變化分析
依據表1的國土“三生空間”分類體系,利用ArcGIS 10.2軟件對兩個研究時段的土地利用數據進行重分類,得到昆明市國土空間利用格局圖(圖2),提取并統計各類型國土空間面積,測算其所占的比例及其變化,并計算各類國土空間單一動態度和綜合動態度(表2),從國土空間面積變化及變化速率來分析人類活動對其單一類型國土空間和整體國土空間的影響程度。
由表2可知:①昆明市的優勢功能空間是農業生產空間和綠地生態空間,所占面積超過區域總面積的70%,且2015年較2009年增加了約10%,所以昆明的農業產業基礎和生態水平較高;工礦生產空間增加 82.64 km2,說明在“十二五”規劃思想的指導下,昆明市工業化和產業化有了進一步的發展。②兩類生活空間面積均有增長,其中城鎮生活空間面積增長水平顯著,增長 141.16 km2,且單一動態度是5.76%,居第二位,但受城市化的影響,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導致農村生活空間6年內僅增長7.9%。③2015年昆明市生態空間面積共計 13 564.89 km2,占總國土空間面積的64.55%,其中綠地生態空間面積具有較大優勢,水域生態空間的動態度僅為0.15%,面積基本保持著穩定狀態,而其他生態空間的面積顯著減少,較2009年減少了 2 224.78 km2,且單一動態度最大,為13.18%。④從綜合動態度來看,研究期內各類空間用地綜合動態度最大的仍是其他生態空間和綠地生態空間,分別是0.88%和0.85%,變化面積分別是 2 224.78 km2和 2 133.06 km2。水域生態空間的綜合變化度是極小的,僅為 0.002 2%,總的來說各類國土空間面積變化幅度差異較大。

2009-2015昆明市國土空間面積及動態度變化 表2
3.2 國土空間重心遷移分析
根據重心遷移模型計算分析得到昆明市各國土空間重心遷移軌跡圖(圖3),以及重心遷移距離和遷移速率(表3)。

圖3 2009-2015昆明市國土空間重心遷移圖
由圖3和表3可知:①農業生產空間的重心向東北方向遷移 0.994 6 km,遷移速率為 0.165 8 km/a,均處于嵩明縣所轄楊橋街道內;工礦生產空間的重心偏移水平不大,在空間上以 0.058 2 km/a的速率偏移了 0.349 1 km。②生活空間中兩個二級類空間的重心遷移水平較大,尤其是城鎮生活空間的重心遷移特征更為明顯,往東北方向以 0.294 4 km/a的速率向青云街道遷移,共遷移 1.766 3 km,說明昆明市城鎮生活空間變化明顯,東北部空間面積增長幅度最高;農村生活空間的重心遷移變化幅度較城鎮生活空間的小,遷移 1.029 2 km,遷移速率是 0.171 5 km/a,反映出整體上昆明市農村生活空間結構變化相對均衡,彼此之間面積變化的差異性較小。③生態空間中除水域生態空間外,林地生態空間和其他生態空間的重心偏移都較顯著,尤其是其他生態空間變化最劇烈,從2009年到2015年重心共遷移 19.959 6 km,遷移速率為 3.326 69 km/a,從尋甸回族彝族自治縣的雞街鎮遷移到先鋒鎮,說明隨著昆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對土地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從而使得土地利用率提高,這提醒我們在加強土地利用的同時,應該注意土地利用類型的合理分配。

昆明市國土空間重心變化 表3
3.3 國土空間轉移特征分析
利用ArcGIS 10.2空間分析功能得到昆明市2009年~2015年國土空間面積轉移矩陣(表4)。由表可知,研究期內昆明市各空間類型面積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或減少,除了農業生產空間、水域生態空間和其他生態空間外,其余類型空間轉入面積均大于轉出面積。各空間類型面積轉移特征具體表現為:①農業生產空間面積減少,是工礦生產空間和城鎮生活空間的主要來源,說明存在農用地被占用現象;而工礦生產空間主要為建設用地,轉為其他空間的難度較大,且受工業化發展的影響導致工礦生產空間面積增加,凈轉入面積為 82.645 3 km2,主要由農業生產空間轉換而來。②生活空間面積都呈凈增長,主要由農業生產空間和綠地生態空間轉入,其中農業生產空間轉為城鎮生活空間的有97.3871 km2,轉為農村生活空間的有 28.426 2 km2,而綠地生態空間轉為城鎮和農村生活空間的面積分別為 22.049 6 km2和 4.993 8 km2,說明隨著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城鎮生活空間面積較農村生活空間擴張更為迅速,二者向農業生產空間和綠地生態空間要地的趨勢均較為明顯。③生態空間的總轉入和總轉出面積分別為 2 189.313 6 km2和 2 286.470 9 km2,呈現出生態空間面積略微減小的趨勢,其中其他生態空間減幅最大,表現為凈轉出面積為 2 224.782 8 km2,主要轉為綠地生態空間,所以綠地生態空間面積增加顯著,凈轉入 2 133.061 7 km2。

昆明市2009年-2015年國土空間面積轉移矩陣(單位:km2) 表4
3.4 國土空間景觀結構動態演變
采用Fragstats 4.2軟件,分別計算出兩個研究時段上各類國土空間的各個景觀指數值(表5、表6),具體分析研究區在不同斑塊尺度上的景觀特征。

2009年-2015年昆明市國土空間景觀類型指數 表5
(1)斑塊類型尺度上景觀特征
從景觀斑塊類型尺度選擇斑塊數量(NP)、斑塊密度(PD)、景觀百分數指數(PLAND)、平均斑塊面積(AREA_MN)和周長-面積分維數(PAFRAC)分析昆明市國土空間景觀斑塊類型特征及演變規律。由表5可知:
①農業生產景觀斑塊數量和斑塊密度增大,而斑塊百分數指數、斑塊平均面積和周長-面積分維數值都變小,故昆明市農業生產景觀斑塊更加密集,且斑塊形狀趨于簡單,但破碎化程度變大,對農業用地進行規模化利用較難;工礦生產景觀的斑塊數量、斑塊密度、斑塊百分數指數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說明工礦生產景觀面積增加且分布更加集中;平均斑塊面積變小,所以工礦生產空間布局更加連片,細碎化程度變小;而周長-面積分維數值的略微增大,體現其在擴張的過程中,形狀趨于復雜化發展。
②城鎮和農村生活景觀的斑塊數量、斑塊密度和斑塊百分數指數呈現上升趨勢,說明昆明市生活景觀面積增大,且分布更密集,其中城鎮生活景觀的平均斑塊面積急劇減少,周長-面積分維數也降低,故隨著新型城鎮化策略的實施,城鎮生活空間利用更集約、連片,形狀也更為規整。農村生活景觀的平均斑塊面積下降,說明其破碎水平上升,而周長-面積分維數下降,說明實施新農村建設成效顯著,農村居民點更加規則有序。
③綠地生態景觀的斑塊數和斑塊密度下降,原因是綠地生態空間主要由各種林地和草地組成,受退耕還林政策的影響,使得林地與草地集中連片出現,導致斑塊數逐漸減少,所以綠地生態景觀的細碎化程度有所緩和;景觀面積比例明顯上升,平均斑塊面積也明顯增長,說明其分布較為集中,而周長-面積分維數指數有所下降,說明綠地生態景觀的邊界和形狀逐步趨于簡單化。水域生態景觀的總斑塊數、斑塊密度和周長-面積分維數都呈上升趨勢,但增幅均不大,說明其細碎化程度有所提高,且斑塊形狀和邊界趨于不規則和復雜化;景觀所占斑塊面積和斑塊平均面積的值均變小,這與斑塊數量和細碎化水平增高有關,所以今后人們在利用水域生態空間中的湖泊和坑塘時,應合理規劃,盡量改造為簡單規整的形狀。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的快速發展,用地需求不斷增加,所以其他生態景觀中的土地,被有效開發利用轉為其他用地,在研究期內,各景觀指數都急劇減小。
(2)景觀尺度上景觀特征
通過計算香農均勻度指數(SHEI)、香農多樣性指數(SHDI)、集聚度(AI)、蔓延度(CONTAG)和散布與并列指數(IJI)分析昆明市國土空間的空間異質性和相互聯系(表6),由表6可知:
①SHEI和SHDI的值均變小,說明昆明市國土空間景觀類型的異質性程度減小,土地利用均衡度有所下降且多樣性減少,也說明景觀主體類型農業生產空間和綠地生態空間對昆明市景觀整體的控制作用被其他各類景觀削弱。
②昆明市國土空間景觀的AI值和CONTAG均呈現上升的趨勢,說明區域景觀的集聚度在提高,破碎水平在降低且主體景觀農業生產景觀、綠地生態景觀的連通性有所提高,說明在城鎮化和工業化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其他空間對兩類主體優勢空間并無明顯干擾;IJI指數變小,體現昆明市不同類型景觀之間的相鄰概率降低,某一類型與其他類型景觀的鄰接水平下降,表明區域相同景觀類型的斑塊集聚程度在不斷上升。

2009年-2015年昆明市景觀水平指數變化表 表6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本文從國土“三生空間“的數量變化、重心遷移、轉移特征和景觀格局變化等方面分析研究昆明市國土空間的結構演變特征,得出以下結論:
(1)昆明市的優勢功能空間是農業生產空間和綠地生態空間,所占面積超過區域總面積的70%,所以其農業產業基礎和生態水平較高。
(2)各功能空間在研究期內面積變化幅度差異較大,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或減少,除農業生產空間、水域生態空間和其他生態空間減少外,其余類型空間轉入面積均大于轉出面積。
(3)隨著昆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土地的需求日益增加,對后備土地資源開發利用程度增強,致使其他生態空間的重心遷移最劇烈,從尋甸回族彝族自治縣的雞街鎮遷移到先鋒鎮。
(4)昆明市國土空間景觀類型的異質性程度、土地利用均衡度和破碎化水平均降低,而集聚度和景觀間的連通性在提高。
4.2 討論
本文基于昆明市“三生空間”來分析昆明市國土空間結構演變特征,雖能為今后昆明市國土空間開發利用和格局優化提供重要參考,但在“三生空間”的劃分、研究數據的選取以及研究尺度上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
(1)“三生空間”的劃分主要依據國土空間功能,而任一土地都具有多功能性,所以在“三生空間”分類上存在一定的不足,未來需要進一步探討“三生空間”分類與土地利用的銜接,完善“三生空間”分類體系。
(2)受數據收集條件的限制,本文研究數據為間隔6年的兩期土地利用數據,未能在較長時間上反映昆明市國土空間的演變特征,未來需要對其進行長期跟蹤研究。
(3)本文基于昆明市市域尺度展開研究,對各區縣土地利用結構特征分析不夠具體,未來需以縣域尺度作為研究對象,更詳細具體地分析國土空間結構演變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