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象牙塔的學術青年們
張云亭
2020年2月4日,人類學博士候選人曾毓坤在豆瓣上列出了一份《Corona讀書會人類學閱讀清單》,并表示想要組建一個線上讀書會。在當天,有百余位豆友私信加入;次日晚上10點,第一期Corona讀書會在線上展開。
那個節點,新冠疫情正不斷陷入緊急情況和不確定性。讀書會建立的兩天前,國內因為疫情被延長的春節假期剛剛結束;13天前,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宣布“封城”;2天后,李文亮醫生去世。
曾毓坤當時在家中隔離,形容自己的狀態為“崩潰”。“我在武漢上的大學,我無法把疫情當作一個用以在家寫論文的漫長寒假”。他也參Cover Story有故事 青年們與了一些線上組織的志愿者活動,但最終還是決定做自己最熟悉的、從學術知識和能力出發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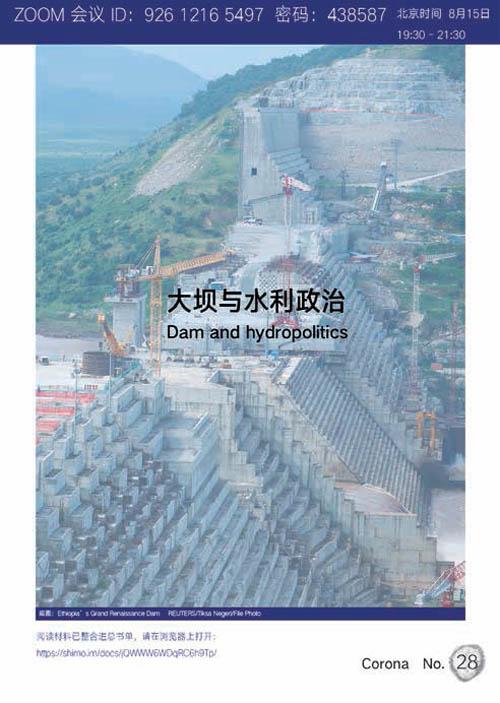
曾毓坤在疫情期間組織的兩次在線讀書會海報。
疫情期間,整個社交網絡興起了一場用線上閱讀來對抗焦慮的運動。曾毓坤關注到一種觀點,有人倡導應該關掉電視和社交媒體,來專心閱讀早就想讀的書、寫早就想寫的論文,他希望自己能做一些有能動性的事。
以疫情為契機,對學術感興趣的年輕人開始行動。相比已成名的學者們,這些知識青年沒有知識權威的光環,一開始就希望打破圈層文化,與擁有不同知識背景的人交流。而微信公眾號、直播平臺、Zoom和飛書等在線交流工具的出現,也讓這個與大眾交流的愿望變得可能。
在海外念哲學本科的劉倫與曾毓坤有類似經歷,他擔心在國內的家人,可除了打電話讓他們買防護用品,“不知道該做什么,不知道能做什么。想抓住什么,但又抓不住什么”。他叫上了幾位學社會科學的同學一起寫了一篇幾萬字的文章,用所學的專業知識分析當時國內在疫情期間的新聞。幾乎在Corona讀書會成立的同時,他們把文章發在了劉倫和朋友一起創建的公眾號上。這篇文章在當天就獲得了幾十萬的閱讀量。
大學生交流平臺“圍爐”在2020年7月和青年活動組織“706同學社”合辦了線上圓桌“在變遷之中生活”,討論教育方式變遷、公共生活變遷,以及公共生活的意義。參與對談的人,除了周濂、周保松等學者,還有一些在讀學生、藝術家等。

曾毓坤在疫情期間組織的兩次在線讀書會海報。

劉倫所在高中生社團舉行的一次讀書會海報。
圍爐成立于2015年,是主要由香港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大學等8所高校學生運營的非盈利組織。“每當面臨大的危機時,大眾都會對社會有感觸和反思”,在談起組織圓桌的意圖時,圍爐負責人楊晨告訴《第一財經》雜志。
他清楚這次對談“不僅是面對大學生了,是面向公眾的,是面向80后、90后”,“他們可能想要去了解大學生是怎么想的,或者,他們懷念大學時的討論氛圍”。
而Corona讀書會在短暫的探索后找到了更合適的路徑。最初,讀書會的形式、內容更像是學術訓練中的研討會,第一次的內容主題是“重讀流行病人類學”。他們選了兩篇這一領域不同時期的重要論文,由1到3名領讀者領讀,隨后進入自由討論。
但這種面向專業學生的讀書會并不適合大眾討論,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訪時,曾毓坤回憶,在第二期讀書會中,他們選取了福柯《性經驗史》中《死亡的權利與控制生命的權力》部分,“大家都熱情高漲,想用批判理論來好好檢審疫情里暴露出來的社會問題,但效果并不好,討論過快陷入一些關鍵概念在福柯文本里的詮釋泥淖,無法動彈。”
他們又轉而嘗試在讀書會回應當下重要的社會議題—“疫情期間的希望”“共情”“性別與疫情”—不再使用最初無論風格還是思路都像博士課程的書單。
讀書會最密集的時候,能夠達到四五天舉辦一次,“非常激情”。令曾毓坤驚喜的是,他很容易找到為讀書會做領讀和筆記的人,哪怕他們面對的是全新的議題,也可以做到迅速讀書、學習。到后來,讀書會上出現了不少話題的親歷者來做分享,例如在武漢經歷隔離的人。
“新冠是一件全新的事情,你不可能等5到10年,等一個人成了新冠專家之后,再來向他提問。”他說,在傳統的學術機構,之前非專業領域的人不太積極參與類似的討論。疫情帶來的沖擊改變了這種現狀,“群里流傳著一個氛圍,就是邊看新聞,邊讀書,邊思考。”
社會科學及其使命
社會科學專業正在成為年輕一代的選擇。根據啟德教育發布的《2021中國留學生白皮書》,2015年到2020年,商科申請占比始終排在首位(33.8%),其次是社會科學(21.2%)。而在這5年里,社會科學占比總體呈上升趨勢,增長率達到5.3%。
對于準備選社科專業留學的高中生而言,他們需要在中學階段就對選定的學科有一定認知和積累。這也驅使了一些學生討論組織、活動的形成,例如從2018年由上海平和學校高中生創辦的“中學生哲學大會”,到2021年上半年已經舉辦4屆,參會的中學生需要提交論文并現場討論。
劉倫是在高二時加入了一個討論哲學、社會學的社團,他當時就讀于北京一所高中的國際部。在學高中政治必修課時接觸到哲學知識后,他通過讀學者鄧曉芒的《康德哲學講演錄》等書籍進一步接觸了歐洲哲學。他希望能有人和他一起學習,再加上國際部的學生有辦社團、組織活動的氛圍,于是和同伴一起建了微信群,在朋友圈轉發了招新的信息。
社團在高中階段給了劉倫一個安穩的、有身份認同的討論空間。在剛決定學哲學時,周圍幾乎沒有同伴,家人也擔憂這種冷門學科會讓他在未來不好找工作。社團讓他接觸到了最初感興趣的學術領域,并且嘗試搭建起自己的知識網絡,讓他形成自己的觀點和見解。從實際的角度,參與社團的經歷也對他的留學申請有幫助。
擁有13.9萬粉絲的B站學術Up主多羅西123也是在高中階段最初接觸了社會科學知識。她在準備出國留學時接觸到了美國大學預修課程(一般稱為AP課程),在其中選擇了心理學;進入美國本科的第一年她嘗試選了哲學的課程,并在之后的三年半里選擇并修完了哲學、社會學和心理學3個學位的課程。
在耶魯大學社會學系讀博士的她最初只是在B站上傳自己彈鋼琴的視頻,在一次彈奏得到首頁推薦、收獲粉絲后,她開始把和自己所學知識相關的視頻放上去。2019年6月,她在本科畢業時講述哲學意義的演講視頻再次被推上熱門。這條視頻當時給她帶來了幾千粉絲,如今有1600多條評論,其中有不少爭議是圍繞“哲學是否有用”。
多羅西在評論中回應,“我意識到一段在下臺后只收到掌聲的演講,在走出了那個所謂哲學系或學術界的小圈子以后,是怎樣廣受質疑和不屑……我發這個視頻的目的,就是想打破這種隔離。”
在這個視頻走紅后,多羅西開始做“社哲講堂”系列視頻。除了講學科的基礎知識、邀請學者訪談,她還嘗試用學術知識解釋現實中的現象。例如孤獨、抑郁癥和焦慮癥、社交恐懼,或者身材焦慮和性開放問題。在一期社哲講堂中,她表示這是因為知道粉絲們想從她這里聽到更多哲學、社會學知識。
在這些青年的表述中,“打破壁壘”“聯結”不約而同地成為了高頻詞。比如盡管認為自己不善于組織和行政工作,劉倫還是希望能讓社團成為一個社群,這其中應該包含二三線城市的同學。
劉倫告訴《第一財經》雜志,“我確實經常能看到他們也在討論哲學、社科問題,只不過不是在我討論的地方討論。所以這種聯結很必要。”在之前接受媒體采訪時,他表示自己“肯定是要想辦法以后怎樣去幫助別人”,“文科知識分子很多有這樣一種樸素的理想主義觀點”。
在2021年3月的視頻中,多羅西講述了做“網紅”的矛盾心情。盡管因為影響力更大感到高興,她說自己很少因為漲粉感受到“純粹的快樂和自豪”,因為她擔心當“網紅”成為她的一個身份時,更會因為她拋頭露面、做與學術奉獻精神不符的事而“斷送學術生涯”。
但她在視頻的結尾引用了李普曼的《公共輿論》中知識分子的兩個職責:追求真理和傳播真理。“我在B站上做的事情,不說傳播真理,至少是在傳播知識。因為很多時候,形成階級壁壘的就是知識……如果有專業知識或者經過專業訓練的人,他不在社會有問題的時候站出來說一些什么,僅僅躲在象牙塔里,那你可不可以說學者是在摒棄自己的社會責任?”

多羅西在自己家中錄制“社哲講堂”系列視頻。
到公眾中去
在青年們成長為傳播者和行動者的過程中,少不了前輩學者的引領。
多羅西談起了自己在本科時遇上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埃里克·奧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她當時選擇了這位教授的社會學入門課程《當代美國社會》。在剛開課的時候,老師就在課堂上說,歡迎所有人去他的辦公室自由提問,如果沒有問題,自我介紹也可以。
“他很關懷學生,或者說有普世關懷。”多羅西告訴《第一財經》雜志,“他并不是在想,作為教授如何享受自己的頭銜,或者過上地位很高的生活。他想的一直都是,怎么能夠利用他的位置幫助過得不那么好的人過得更好。”
這種體會是從她自己的經歷出發的。她接受了老師在課上向全員發出的邀請,在第一次愉快溝通之后,幾乎每次教授的辦公室開放時間多羅西都會去。他們聊課上遇到的問題,也分享生活的觀察。
有一次多羅西在假期回國之后,曾向賴特描述自己在家鄉經歷的反向文化沖擊。教授在郵件中指出了她看似微觀的情感背后的社會學意義,并介紹了民族志的定性研究方法—“參與者觀察法”,既是參與者,又是觀察者。他鼓勵多羅西用學術的方式認知和探索這些情緒。
賴特在2019年因癌癥去世。多羅西曾在博客上撰文回憶起他們關于生命意義的討論。當時賴特曾講到,“對我而言,‘意義是通過我們積極影響他人的生活方式實現的。這也許并不是要影響全世界,可能就是影響親朋好友、同學同事。你不應該低估自己現在與他人接觸所產生的積極影響。”
曾毓坤說已故的美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給了他重要的啟發。格雷伯因對官僚主義、政治和資本主義的尖銳描寫而聞名,曾出版相關著作《狗屁工作》(Bullshit Job),生前曾在耶魯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等高校任教。他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是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的關鍵人物。
“他不會告訴你,所有的學者或者人類學家需要處在田野和大學的割裂之中。”曾毓坤認為,格雷伯投身社會運動,同時在人類學理論上有非常出色的貢獻,“他告訴我這種工作方式是可能的,學院和田野的二分法是可以打破的。”
“這需要不斷地去看、去問、去參與,而不是你做了田野,把那個東西僅僅轉化成講臺上講的東西,或者書桌前寫的論文,而論文要幾年之后才能發表,講臺下的聽眾就那么幾個。”
劉倫認為與公眾和社會建立聯結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它不僅本身是知識分子責任的一部分,更是“一種生存方式”。“你可以通過這個方式去學東西,然后回饋給現有的環境,并且去生存。”
他認為新媒體傳播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知識分子的概念神話”。他回憶,他的朋友曾和他談起美國的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這位女性學者在她所處的20世紀中期曾作為公共知識分子談論性自由等問題,被學術圈的人看作“奇怪的存在”。而現在,在網絡世界發聲、“走出象牙塔”已經不再是難事。
整體來說,影響這些年青人的學者有一個共性—走出學術圈,直面社會問題,做出個體的努力和行動,并肯定這種行為所帶來的哪怕微小的價值。
這種觀點也跟上一代知識分子區別開來。在此之前,公共知識分子與學者之間還有明顯的界限,前者雖包括部分學者,但更多是媒體人在充當公眾與學者之間的橋梁。而現在,知識青年在自己到公眾中去的同時,對于文化記者的認知也有所改變。
圍爐的公眾號中有一個欄目叫“圍爐對話”,由社團的成員選擇對話的對象,寫成訪談錄。這些對話者包含學者、創作者等等。入選的“學者”中有一部分是學院里的專家,還有一種是文化記者。他認為,國內的80后、90后中,有一些不在學術體系中的記者也有深刻的思想。“可能在專業知識、學術性上沒有那么強,但是有豐富的個人經驗,能做出更貼合社會現實的解釋。”
劉倫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在當下,公共和私人領域的界線正在變化,這影響到了知識分子在公共討論中的作用。之前的知識分子可能更有“固定的姿態”,會輸出“正統的概念”,而這種輸出很難激發公眾的討論。但現在,知識分子需要更多地與公眾一起卷入討論。
他認為“知識分子討論公共問題”在歷史進程中是常態,而從1970年代興起的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對這種常態有沖擊。它直接導致了不少社會問題被歸咎于個人,而非社會結構和政治議題,例如家暴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在公眾場域能做的,更多是從純粹智識、思辨的角度發聲,而非介入具體的事件。
但現在,這樣的思維方式遭到了批判和質疑。“知識分子沒法再作為一個修飾了……他可能發現自己講著講著沒飯吃了。或者學著學著,疫情在自己的家鄉暴發了,這么強烈的沖擊下,他們可能會發現自己想做的、未來要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有差別。”

2012年,大衛·格雷伯在一場占領運動中發言。他既投身于公眾事業,也在理論上有所建樹,激勵了后來的知識青年 們。
理想與現實之間
在發起讀書會一個月之后,曾毓坤開始在一家國內媒體做民生新聞的實習。
他談起那段時間最深的感觸。在當時,新聞的直接迅速緩解了他對現實關切的焦慮,“一個電話過去就能核實”,這比學術研究快得多。另外,他看到記者在短時間內迅速學習和消化醫療領域的新知識和論文,這也是他在博士期間被要求訓練的能力。
相比之下,社科研究的精確度有時并不令人滿意,“比如一些政策,可能一個跑口的記者比學者更有機會和欲望去鉆研原件,對比分析”。
他嘗試把社科知識和新聞寫作相融。在實習期間,他曾經負責寫一篇打工子弟疫情期間上網課困難的文章。在調查中,他發現打工子弟在Cover Story有故事 青年們能湊齊網課學費、也有網課設備的情況下,依然會因為缺乏家長的監督、家庭矛盾等原因導致沒法完成課程進度。他選擇用“事實性輟學”的概念來描述這個現狀,這符合社科研究領域的總結習慣,但在講求信息增量的媒體是新的嘗試。
但記者的職業也帶給他遲疑。他先是發現自己周圍的同事普遍比自己小很多,“快三十了,確實不能和剛畢業的人比熬夜寫稿”。另外他發現,有一些記者朋友希望辭職后去讀人類學,和自己選擇的路徑剛好相反。
他也與自己的同學討論過新的就業路徑,但不得不承認,博士畢業后尋找教職仍是主流的方式。面對高度內卷的學術市場,“如果一小時不讀書、不寫論文就會出現吃虧的心態”。盡管在探索“新路徑”的一年多時間里他收獲頗多,也有能說服自己的理由,但他確實有一點焦慮。
在當下如何處理發聲與學業的關系,以及,今后要如何對待“知識分子”的社會身份?這是年輕的學術行動者面臨的重要問題。
多羅西在私信中最經常收到的問題是:學哲學、社會學到底能找到一份什么工作?她承認社會上提供給這樣專業學生的工作崗位是有限的,所以在收到這樣的問題時,她往往會多問對方兩句:生活中有多少經濟需求需要滿足?喜歡這門學科到了什么程度?
上傳第一個與社科知識相關的視頻時,多羅西就在評論中看到一種說法:學習哲學的人往往是因為沒有顧慮、追求精神享樂才學了這么一個不切實際的學科。像她這樣的人是處在特權的地位的,她在教授一種普通大眾沒有條件學習的東西。
“如果經濟顧慮大的話,選擇‘更實際專業的同學做了非常理性的選擇,我不會覺得他們沒有思考,”她說,“但我希望從事不同行業的人,能通過我了解社會科學或者哲學。在保障他們生活的基礎上,體會到這些學科給他們帶來的好處。”
劉倫說,“知識分子的特權問題”是社團討論時最先遇到的問題之一。“我不認為原罪,或者身份特質應該是取消行動、拒斥某些人的行動的原因,”他說,“我覺得這種特質恰恰是這些人應該行動的一個原因,他們應該意識到自己的特質,并且正是因為這些,他們才要運用特質加入到行動之中。”
“知識分子應該追求自己的消亡”,他說的時候引用了一篇社團成員的文章,“一個知識分子,或者說一個有特權的知識分子應該做的,是不斷嘗試消解自己這種特權出現的可能性。要消滅使自身得以出現的這個環境,要消滅自身和其他人的這種分別。”
在疫情期間受到廣泛關注之后,劉倫希望能盡量退出這種注視,在我們聯系采訪時,他最初多次拒絕。“好好學習更重要”,他說。
他發現,當需要為社團爭取利益、頻繁發言時,因為要和別人辯論,他時常得站在某一個立場上。在這種時候,也許要放棄個人進取的空間,反復強調和重復現有的觀念、角色、定位,以獲得支持。這使得他很容易堅守固定的觀點不變。他設想,如果這樣下去他必須代表某一類人,這勢必使他和另一些人對立。這種局限可能會使反思和行動都受限。
他在2020年下半年退出了社團,沒有像他設想的那樣,能幫助社團擴充為能容納更多樣人群的“社群”。
在采訪中,他談起在疫情期間讓社團廣受關注的那篇文章的不足之處,表示自己現在“可能也已經不是很認同了”,“如果有人持我之前那篇文章的立場,他也可以用我自己的語言反駁。這沒有問題,而恰恰是學術討論的一大特色。”
對于年輕一代的學術青年來說,用人文知識去關心社會這個長遠目標也許短期內并不會讓他們看到多少成果,許多理想也必然在未來與現實產生沖突。但真正重要的是,在一個日漸失去對話的耐心的環境中,這些微不足道的個體試圖建立起個人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及與他人平等對話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