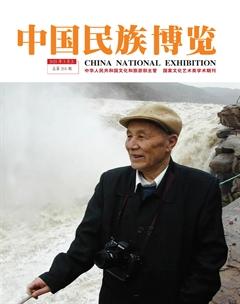生產生活變遷下的蒙古族馬文化
【摘要】蒙古族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素有“馬背民族”之稱,以馬為載體和象征的蒙古族馬文化滲透在蒙古人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更是融入了蒙古人的精神世界。文化是隨著人類社會發展而產生變化,蒙古族馬文化也不例外。本文將以蒙古族馬文化為研究對象,探討蒙古族生產生活變遷下的蒙古人與馬的互動變化,試圖指出以馬文化為代表的蒙古族傳統文化逐漸趨于減弱或消失的原因、影響以及保護價值。
【關鍵詞】文化變遷;馬文化;文化的適應
【中圖分類號】J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1)05-060-03
【本文著錄格式】格日樂塔娜.生產生活變遷下的蒙古族馬文化[J].中國民族博覽,2021,03(05):60-62.
基金項目:內蒙古自治區高等學校科學研究項目“文化人類學視角下的蒙古族傳統文化變遷及社會影響研究——以巴林草原馬文化為例”(項目編號:NJSY16433)。
文化是人類生存活動在適應和改造自然中所形成的符號,文化其本身具有變遷和適應的特點或功能。蒙古民族的文化源于北半球干旱的草原生態環境,眾所周知,它并不肥沃,甚至是貧瘠的土地。在幾千年的演化中,中國古代北方民族形成了能夠適應殘酷自然條件的游牧文化,蒙古族繼承并發揚了古老的草原文化。工業時代的到來,所謂的先進的現代文化,營造了一種生態,是政治或經濟生態,正沖擊和改變著傳統的游牧文化,并形成了新的文化變遷和適應需求。
自然環境、牧人、馬這三點是維系游牧生活的核心。蒙古族馬文化,如崇尚馬、牧馬、養馬、馴馬、調馬、賽馬、識馬(mori sinjihu)、美馬(語言文學、歌曲舞蹈、繪畫造型、器具裝飾藝術中的馬)以及相關禁忌等等。蒙古族馬文化是草原文化的精華,是蒙古族傳統文化的重要文化符號。可以這樣說,蒙古族傳統文化是在馬背上創造的。學界基本認為,馬文化在本意上是指動物民俗中的一類;在引申意上指牧馬民族的民俗。本文中蒙古族馬文化是后者,探討與馬有關的人的社會行為。改革開放,中國進入了嶄新的歷史新時期,全國以極大的速度創造經濟效益。內蒙古牧區固然也會被這股浪潮沖擊,對于草原的開發主要體現在,農業產業發展、畜牧業產業發展、草原旅游產業開發、礦產資源開發等,使之產生了劇烈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遷。也就是說現代化帶來的生產生活變遷之下的蒙古族馬文化,從蒙古人的物質文化載體及精神文化內容兩個方面討論,以及當代蒙古人的生產方式、生活習慣、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環節中的意義。
一、蒙古族生產生活環境與方式變化
“逐水草而居”“馬背上的民族”這些是通常描述蒙古人經濟生活狀態的語句,可見,古代蒙古族游牧生活基本處于游動的狀態。游牧是蒙古族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清代末期大面積官墾推行以來,逐漸改變了這一傳統的方式。尤其是工業化現代化浪潮沖擊下,蒙古族傳統生產生活方式由傳統游牧逐漸轉變至季輪游牧、定居牧、半農半牧、農耕甚至是現代化牧業、城鎮生活。蒙古族經濟社會發展是由社會內部的變化而引起的內部與自然環境變化、社會文化環境變化而引起外部共同作用的結果,這與生產生活環境與方式的變遷有著密切的關系。
(一)生存環境變化
自然環境是人類生存發展的空間,對不同民族文化的形成有著決定性作用,是文化得以產生和發展的基礎。無論任何意義上講,人類的某一種文化都是在特定的自然條件下適應和改造自然而形成的。蒙古高原位于北半球溫帶,大陸性氣候,干旱,降雨量少,風沙大,嚴寒,無霜期短。基于草原自然生態環境,起源于這片廣袤土地的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創造了歷史悠久的游牧文明。而原有生態環境地改變,文化也會發生適應性的變化。19世紀末,清政府施行官墾,內蒙古草原農耕面積不斷擴大,造成原有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尤其到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現代化工業發展則是造成了草原自然生態環境的急速退化和氣溫變暖的直接原因。自然環境地改變是造成民族文化變遷的直接原因,是重要的外部因素。
(二)生產方式的變化
生產方式的變遷不僅與自然環境變化有關,與經濟社會政策也有極大的關系。傳統上蒙古人的生產生活方式是以游牧為主要特點的草原開發活動。清末民初時期之后,人口的不斷增加,傳統游牧生產方式轉變為輪季游牧,也就是季節性輪牧。輪季游牧最大的變化就是一年里游牧移場的次數變少了,牧人無需跟著蓄群放牧,而是牲畜在既定的牧場繞包而牧。到了20世紀50年代,“以牧為主”的政策導向之下,蒙古人的生產生活方式由季節性游牧變為定居放牧,蒙古包由泥磚房取代,圍欄、蓄舍、牛糞堆(argal n oboo)逐漸出現,同時補給性的農業活動逐漸擴大。20世紀80年代以后,農耕面積不斷擴大以及家畜頭數顯著增多的原因,導致草原植被較嚴重退化,開始圍封草場分歸于各家各戶,此后逐漸結束了“游牧”的生產生活方式。后又采取了“退耕還林還草”“圍封轉移”“禁牧休牧”等政策,實施了不同形式的生態移民,使之蒙古人的生產生活方式由牧業轉向了合作化養殖業、商業等等。
二、蒙古人與馬
文化的基本特性是指“每種文化都是在社會中習得的、共享的、基于符號的、整合的和動態的”。文化變遷是指“對人口增長、技術革新、環境危機、外部入侵,或對文化內部行為和價值觀地改變所做出的反應”。
文化是隨著人類社會發展而產生變化,并產生適應和選擇。人類通過文化來實現適應環境的變化。也就是說,文化是由“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地調整及適應。蒙古族馬文化也不例外。現代化生活中的社會生活環境變化,使得馬與蒙古人之間的距離越去甚遠。比如,蒙古人通常采以牧馬的方式,將馬放歸大草原,任其自由覓食、繁殖,只有廣袤的草原才能符合蒙古人養馬的條件。但是,在發展農業、開采資源等經濟利益驅使下草原環境越趨惡化、天然草原退化,使之蒙古人無處養馬,馬的頭數急劇下降,甚至內蒙古牧區的馬群在逐漸消失。馬文化作為蒙古族文化重要的符號,是具有代表性的。馬群減少或消失,以此為載體的蒙古族馬文化自然會受到影響,甚至在影響著蒙古族社會及傳統文化的未來方向。
蒙古馬是源于蒙古高原的野馬,蒙古人稱它為“鐵赫”。在悠久的游牧生活中,蒙古人熟知馬性,積累了豐富的飼養和馴化馬的經驗,而且培育出優良的馬種——蒙古馬。馬不僅是蒙古人的交通工具,同時也是蒙古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形成了一個歷史產物——蒙古族馬文化。例如,馬群的飼養放牧文化是遵循“以自然為主導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為核心價值觀的一種生態飼養模式,即遵循馬的本性與自然環境本來的生存關系。因此,老人們會經常說,自從沒有馬群之后草原上的草都不茂盛了(蒙古人認為馬蹄踩過的地方會有利于草的生長)。
如前所述,生產生活變遷之下,蒙古族馬文化產生了變遷,呈現出了文化的適應性和選擇性。說到馬與蒙古人之間的最大變化,是馬在牧民生活中的用途之變化,即現代蒙古人逐漸脫離了馬背生活。
(一)“馬”為載體的物質文化
傳統游牧世界里馬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馬是蒙古族傳統社會生活中最主要的生活生產、交通運輸等活動的基本依靠。工業化現代化的快速發展,導致傳統牧業生產生活逐年萎縮,馬的用途在逐年下降。蒙古人飼養馬的數量以及飼養目的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如今摩托車汽車等機械設備基本普及,草原上騎馬出行與放牧的方式變遷為騎著摩托車甚至開著越野車放牧;秋季割草、干草運輸等生產作業基本上都變遷為由現代化的機械設備代替等;內蒙古人很少食用馬肉,盛大的祭祀活動中有以馬為祭品的傳統,種馬、下駒多的母馬、戰馬、狩獵馬、競賽馬、乘騎和放群馬是有著不可以宰殺禁忌的;馬的主要飲食用途是飲用馬乳及策格(馬奶制飲品),蒙古人認為馬乳是最珍貴的飲食之最,敬獻天神的飲品,目前只有極少數地區保留著這一傳統;策格更是有著治療疾病的作用,有多方面文獻記載;馬鬃幾年才會剪一次,所以很珍貴,有著結實、韌性、耐用的特點。因此經常被用于制作捆扎蒙古包的繩子;馬尾長長會剪掉賣給商人,也可以編制繩子,也會用于制作馬頭琴等琴的弦;狩獵是蒙古族經濟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冬季重要的生活補給,為了一次成功的狩獵蒙古人可以抗饑餓、抗寒冷,幾天幾夜與馬同行同住,馬是最可信親密的伙伴,這無不培養蒙古人的忠誠、勇敢、機智的品行;蒙古族傳統體育娛樂項目很多與馬有關,賽馬的分類就多種,還有馬術、馬球、騎射、騎馬障礙、套馬馴馬等;“套馬”是青年騎手賽技、馴馬的過程,有著悠久的傳統,是衡量青年人的英勇、智謀的一項活動。
(二)“馬”為核心的精神文化
蒙古人在與馬長期相互依存的互動過程中,馬的習性和稟賦也影響了蒙古民族勇往直前、吃苦耐勞、甘于奉獻、自由開放等品格和精神的形成。在蒙古人的世界里,馬不僅僅是五畜中最親密的動物,更是借以寄托人們心靈與理想的載體,是一種蘊含著能激勵人奮發進取的精神標志,也是一種美好人格的象征。蒙古馬從自然的馬到神化的馬,最終成為蒙古民族的一種文化圖騰。崇馬文化尤為凸顯。
儀式往往是繼承族群精神文化的重要環節。騎馬禮,古老的蒙古族男童育兒儀式。在幼童三歲時,用長布裹緊腰腹部,在長輩的祝福語中家長把孩子抱上馬背,牽著韁繩與眾人騎馬同行一圈,八歲時基本可以自由騎馬放牧。這樣的儀式流傳至今,但是今天不是所有的蒙古族孩子能夠有機會騎馬參與這樣的儀式。傳統那達慕的賽馬手基本上都是未成年的孩子。諸如此類,無不是社會地位角色認同和人格的塑造的儀式,也是吃苦耐勞,勇敢向前的精神訓練。
婚禮儀式上的馬也是有著重要的象征意義,新娘在啟程前往婆家之前會騎馬繞娘家父母的蒙古包三圈,再與新郎踏上前行的路,也是預示著承載著父母的祝福、思念之情奔向美好的婚姻生活。女方陪嫁里肯定有一匹馬,男方也會準備一匹馬,以此報答女方父母養育之恩。唱祝詞“贊馬詞”時婚禮達到高潮。
馬是一種具有靈性的動物。古老史詩中,有英雄,就會有駿馬。蒙古人常常賦予馬以神性,把馬視為神靈和保護神,史詩《成吉思汗的兩匹駿馬》神馬降臨懷胎,掛彩綢封為神馬,象征著力量與勝利;更是有富有傳奇色彩的神馬,蒙古族著名史詩《江格爾》中,神馬救主的故事代代相傳。“贊馬”“崇馬”是蒙古語言文字作品的獨特特點。蒙古人從小被英雄與駿馬的故事所暗示與鼓舞,被崇馬、贊馬的史詩、神話故事、歌曲贊歌等熏陶,逐漸形成英勇無畏、吃苦耐勞、豁達寬廣的民族性格意志品質。
三、結語
現代化科技正在普及到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養馬的牧戶逐年減少。內蒙古草原植被的現狀也不再適合馬群的傳統養殖。變迀是文化的結構性調整的變動過程,同樣,游牧生產生活的變遷也無法阻擋。今天的蒙古人飼養馬的目的由生產生活的必需品轉向了那達慕等比賽的賽馬、娛樂休閑的喜好馬和經濟效益的各種馬產業。有物質載體的文化才有保護和傳承的更大可能性,才會成為對現代社會有價值的文化資源。為適應經濟社會的迫切需要和自然環境的現實變化,蒙古族傳統養馬業應逐漸轉向現代馬產業即文化、旅游、體育、競技于一體的第三產業。向現代馬產業轉型,必定會給內蒙古牧區帶來經濟發展的機會和空間,同時也會給馬文化的傳承帶來一線生機。
參考文獻:
[1]芒來.馬產業、馬文化與城市生活[J].實踐(思想理論版),2015(2):50-52.
[2]芒來.蒙古族馬文化與馬產業發展之我見[J].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10(4):229-233.
[3]威廉A﹒哈維蘭.文化人類學-人類的挑戰[M].機械工業出版社,2000(1).
[4]鳥居君子(日),娜荷芽(譯).民俗學上所見之蒙古[M].暨南大學出版社,2018(12).
[5]巴﹒布林貝赫(著)喬津(譯).蒙古族英雄史詩中的馬文化及馬形象的整一性[J].民族文學研究,1992(4):3-9.
[6]蘇日娜,閆薩日娜.蒙古族的馬崇拜及其祭祀習俗[J].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40)5:41-47.
[7]宋小飛.蒙古族克什克騰部生產及生活方式的變遷——內蒙古克什克騰旗那日蘇嘎查調查報告[J].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32)4:1-7.
作者簡介:格日樂塔娜(1980-),女,蒙古族,內蒙古人,碩士,內蒙古建筑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民族政策、少數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