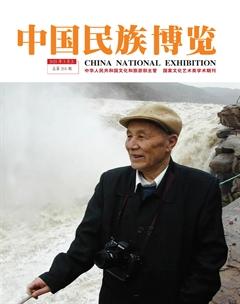“另類”關公——紅袍關公的文化詮釋
【摘要】受《三國演義》影響,今人誤以為綠袍一直就是古代關公崇拜中關羽的標準裝扮,但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存世的文獻與繪畫顯示,宋元時期關公的標準著裝其實是紅袍,這是他在當時國家封祀中王者尊號的身份彰顯,以及作為道教馘魔元帥、佛教伽藍護法、軍隊保護神的神性象征。入明之后,綠袍關公形象伴隨《三國演義》的傳播始漸入人心,綠袍成為關公儒家品格的外顯表征。但至少到清初,紅、綠袍關公都處于共存狀態,綠袍像并非絕對主流的關公造像范式。
【關鍵詞】關公;紅袍;綠袍 ;造像范式
【中圖分類號】J61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1)05-190-03
【本文著錄格式】居鯤.“另類”關公——紅袍關公的文化詮釋[J].中國民族博覽,2021,03(05):190-192.
《三國演義》中反復描寫了關公的“青巾綠袍”,而我們今日所見戲劇表演、繪畫、彩塑等其它藝術載體中的關公形象絕大多數也是身著綠袍的,人們對此已習以為常,即使在當今學術界,也普遍將綠袍視為古代關公崇拜中一貫的標準裝扮,鮮有研究者做過認真探考。實際上,宋元時期的標準關公像是穿紅袍的,入明之后才出現綠袍關公,并借《三國演義》的流傳逐漸深入人心。這一轉變看似具體而微,但卻應當得到足夠重視,因為服飾在傳統社會里是身份地位的標志、品格性情的象征,關公袍服的變化事關他在古代崇祀中的地位與神性定位,所以對于關公文化研究而言是一個具有文化史意義的重要問題。
一、宋元宗教想象中的標準關公像
目前學界一般認為《三國演義》成書于元末明初,但關公崇拜則早在此前就開始了,從現存文獻資料來看至少可上溯至唐代,宋元時已是蔚然成風,那時的關羽又是怎樣一副服飾行頭呢?筆者所見的一些研究者論述認為也是綠袍,例如胡小偉在《關公崇拜溯源》一書中已經注意到了《宣和遺事》“絳衣金甲”關羽的描寫,但仍說:“‘絳衣之說則僅此一見,后世關羽則以‘綠袍為標準服飾。”這與事實并不相符,胡先生甚至忽視了他本人在《溯源》一書中提到的《道法會元》、明代隆慶《儀真縣志》等材料中都有紅衣——也就是“絳衣”關羽存在。
實際情況究竟是怎樣的?讓我們就從宋元話本《宣和遺事》談起,其中記關羽奉張天師命赴解州鹽池斬蛟后降神:
忽有二神現于殿庭:一神絳衣金甲,青巾美須髯;一神乃介胄之士。繼先指示金甲者曰:“此即蜀將關羽也。”
《宣和遺事》的故事自然是出自道教正一派,而匯編宋元道教符箓派法術的《道法會元》卷二百五十九《地祇馘魔關元帥秘法》中,有三段關羽肖像描寫,穿著分別是“天青結巾,大紅朝服,玉束帶,皂朝靴”“紅袍,金甲”“紅袍金甲綠靴玉帶”。
以上描寫中的關羽都身著紅袍,主要原因應是宋元時期的國家封祀中,關羽數次封王,而從唐宋以來,輿服典章制度就規定紅色是帝王的常用服色。《宋史·輿服志》中記載,天子之服有“通天冠、絳紗袍”,朝服中“朱衣裳”也是“三公,左輔,右弼,三少,太宰,少宰,親王,開府儀同三司服之”。既然關羽獲封王爵,造像祭祀時自然也應按王者儀制,其中就包括穿紅衣紅袍。
參照本朝輿服等級制度設定神祇與歷史人物服色,在古人的鬼神和歷史想象中是普遍現象。如宋人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別集》記一人死而復生后描述死后經歷“吾適登一所,若世之官府,兵衛森列,有王者戴平天冠,衣猩紅袍……”,鬼神中的王者便穿紅袍;再如鐘馗,在宋人的想象中著綠袍,《東京夢華錄》記當時百戲“有假面長髯,展裹綠袍靴簡,如鐘馗像者”,陸游《新歲》也有“改歲鐘馗在,依然舊綠襦”詩句。鐘馗作為進士初入仕途,品級不高,正應當著綠袍。《事物紀原》即引《宋朝會要》記載:
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十二日,賜新及第進士諸科呂蒙正以下綠袍、靴笏,非常例也。御前釋褐,蓋自是始。
宋元時期的關羽身著紅衣紅袍,還與他身負斬邪、馘魔、護法的職責,同時又是軍隊戰神,以及受毗沙門天王形象影響有關。首先,用紅色來驅邪是古人常用的方法,其實際運用的歷史十分久遠,《周禮·夏官》記方相氏身穿“玄衣朱裳”驅逐疫鬼,《南齊書·明帝本紀》也說明帝患病時“身衣絳衣,服飾皆赤,以為厭勝”。關羽既然在佛道二教都有降魔護法之責,服色尚紅以震懾邪魔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其次,古代軍隊崇尚紅色也是由來已久,《詩經·小雅》有“韎韐有奭,以作六師”之句,南宋人王與之在《周禮訂義》中明確解釋這兩句:“正謂兵服赤色……赤者南方色,火烈不可向邇,其威赫然,故以赤為服也。”正因為紅色象征威武,史志中便有了不少將士出征作戰時,不受品級約束而身穿紅色服飾的記載:《新五代史》中有梁軍將領陳章“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元史》也記載元軍將領李進身穿紅半臂與宋軍作戰,得到特別賞賜。關羽既以武勇著稱,且至少在宋代便已是軍隊崇奉的戰神,理應給他穿上紅衣紅袍。
二、宋元戲劇、繪畫中的紅袍關公
我們還可以通過明初朱有燉《關云長義勇辭金》雜劇的描寫,以及《脈望館鈔校古今雜劇》關羽的“穿關”,推斷明代以前關羽是被塑造成紅袍紅衣形象的。《義勇辭金》有五次描寫關羽身穿紅色衣甲,分別見第二折關羽唱詞《駐馬聽》“披掛了絳紅鎧甲滲金盔”,第三折探子三次描述關羽“他披掛縷金鳳翅錦兜鍪,鎖子鎧猩袍護”“紅錦袍,染猩血”“青龍刀,赤兔馬,黃金甲,絳紅袍”,第三折曹操說關羽“紅衲襖,錦征衣” 。朱有燉作《義勇辭金》是在永樂十四年(1416),上距元代不遠,古典戲劇中重要人物的裝扮自有固定程式,如果元代演劇關羽不是扮作紅衣紅袍,朱有燉應當不會在劇中數次這樣描述;另據宋俊華《關神崇拜與元明雜劇中關羽的行頭》一文統計,趙琦美《脈望館鈔校古今雜劇》中附有關羽“穿關”的八種元雜劇、一種明雜劇都是“滲青巾、蟒衣曳撒、紅袍”。脈望館本的“穿關”是否直接抄錄自元代劇本,目前雖有爭論,但它與元代“穿關”有很大關聯是無疑的。脈望館本關羽“滲青巾、紅袍”的裝扮,既與《宣和遺事》《地祇馘魔關元帥秘法》的描繪一致,且脈望館本是萬歷年間所抄,當時綠袍關公形象已頗為流行了,如果元代劇本中關羽“穿關”本來不是身穿紅袍的,脈望館本不會出現這樣一致的描寫。
內蒙黑水城發現的金代《義勇武安王》版畫也能提供一些線索。雖然原畫是墨線印本看不出顏色,但關羽袍服胸前、下擺位置所繪的是龍形圖案,正與王者身份相合。金代會不會出現后世關羽像中龍形圖案與綠袍搭配的樣式呢?筆者以為是不可能的。即便與龍袍接近的蟒袍、飛魚服等,在古代都是尊貴的袍服,而綠色卻自唐代以來一直被規定為品級較低的官員所用服色。將綠色與蟒袍甚至龍袍搭配起來是關羽在后世崇祀中所穿的非常獨特的服式,始自明代,如弘治到嘉靖間重修的河北石家莊毗盧寺毗盧殿壁畫、正德間重修的山西靈石資壽寺大雄寶殿壁畫,都可見身著此類袍服的關公。假如金代便出現獨特的龍形圖案與綠袍搭配的關公像,那么當時關羽穿綠袍就應當已是相當普遍的造像范式了,筆者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否則元代平話、雜劇不會對其綠袍只字不提,而《三國演義》中關羽形象的其它特點,如“面如重棗”“長髯”“丹鳳眼”等,在元話本和雜劇那里卻都有相同或類似描寫;另外《宣和遺事》《地祇馘魔關元帥秘法》《義勇辭金》雜劇也不會一再描繪紅衣關公。
三、紅綠袍關公并存的明代
需要特別澄清的一點是,入明以后,雖有《三國演義》推波助瀾使綠袍關公逐漸被大眾接受,但宋元時期傳統的紅袍像并未消失,至少延至清初,仍在宗教祀典、鬼神想象、文學藝術描繪中普遍存在,并非后人受了《三國演義》影響想當然地認為都是綠袍的情形。當時的一些文獻與繪畫例證可以證明這一點,試舉數則:
文獻方面,除前文所述《義勇辭金》雜劇外,還有商輅《敕修都城關廟碑記》“成化丁酉春二月初吉,皇上命內官監太監宿政重加修葺……并制紵絲大紅織金等袍”;成化說唱詞話《花關索傳·貶云南傳》“且說關公怎打扮,連環凱(鎧)甲戰袍紅”;隆慶《儀真縣志·關王廟》“正德間,劉賊舟過江上……后聞賊見陣中有巨人紅袍若王者”;胡應麟《關忠義侯廟作二首》“絳節緋袍氣凜然”;清人薛所蘊《覃懷重修關帝廟碑》“帝緋袍躍馬,環城若巡警者”。
繪畫則如弘治間修建的山西繁峙公主寺大雄寶殿“崇寧護國真君”紅袍關公壁畫、萬歷慈圣皇太后敕繪《關元帥像》、上海博物館藏明代《孔明出山圖》紅袍關公等。
更有一段文字和一幅畫作,能顯示出由明至清關公形象從紅袍向綠袍轉變的痕跡。萬歷間人周暉《二續金陵瑣事》記載關羽托夢明太祖請求立廟,仍描繪他“頳面赤衣”,但到了清代褚人獲《堅瓠集》中,同樣一件事,幾乎相同的文字,“頳面赤衣”就變成了“頳面綠衣”;托名隋唐間人董展《三顧草廬圖》,有薩都剌題記,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楊鐮先生在《元詩文獻新證》一文中明確董展與薩都剌均系偽托,并指出題記中提到的“廉訪楊孟載”只能是明代吳中四士之一的楊基。據《明史·文苑傳》記載,楊基是在洪武六年(1373)以后才任按察使也就是所謂“廉訪”。因此偽托董展的這幅畫實際上不可能早于洪武六年。此畫雖然是偽作,但對本文的研究還是有價值,其中關羽內穿紅衣而外披綠袍,這一獨特著裝正是入明以后紅、綠袍關公曾經并存的明證。
四、結語
綜上所述,由宋至明,關公在崇祀中的王者之尊,與護法驅邪、英勇尚武的神性定位,決定了身著紅袍紅衣才是他的一貫形象。而明代以來,綠袍成為關公日益凸顯的儒家內在品格的外顯表征。毛批《三國演義》第六十六回寫關羽單刀赴會來到吳營——“云長青巾綠袍,坐于船上;傍邊周倉捧著大刀;八九個關西大漢,各跨腰刀一口”,毛氏對這段描寫批道:“儒雅之極,英雄之極。”明確地將綠袍與儒雅聯系起來;康熙時臺灣關帝廟同時祭祀關羽之父,其塑像竟也是“方巾綠袍”的儒士裝扮。儒家品格上升為關公崇拜第一要義這一內在的文化驅動力,使后起的綠袍像隨《三國演義》傳播逐漸成為主流的關公造像范式,反令曾經的紅袍標準像逐漸被遺忘。
參考文獻:
[1]胡小偉.關公崇拜溯源[M].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
[2]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宣和遺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1).
[3]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4][元]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
[5][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別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6]鄧之誠.東京夢華錄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2:194.
[7][宋]高承.事物紀原[M].北京:中華書局,1989:171.
[8][宋]王與之.周禮訂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M].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93):594.
[9][宋]歐陽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1):259.
[10][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12):3639.
[11]周貽白.明人雜劇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12]參見宋俊華.關神崇拜與元明雜劇中關羽的行頭[J].民族藝術,2001(1).
[13]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寺觀壁畫全集[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1.
[14][清]周廣業、崔應榴.關帝事跡征信編,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M].北京:線裝書局,2003.
[15]朱一玄校點.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M].北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16][明]申嘉瑞《儀真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M].上海:上海書店1981.
[17][明]胡應麟《少室山房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18][清]薛所蘊《澹友軒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M].山東:齊魯書社,1997.
[19]北京文物鑒賞·明清水陸畫[M].北京: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2005:44.
[20]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繪畫全集[M].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文物出版社,2000.
[21][明]周暉.金陵瑣事·續金陵瑣事·二續金陵瑣事[M].南京出版社,2007:291.
[22][清]褚人獲.堅瓠集,筆記小說大觀[M].江蘇: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4(7):488.
[23]此圖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筆者從臺灣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網站“典藏臺灣”子系統中檢索到該畫圖片資料.
[24]楊鐮.元詩文獻新證[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3).
[25][清]張廷玉.明史[M].中華書局,1974(24):7329.
[26][清]黃叔璥.臺海使槎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M].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592):893.
作者簡介:居鯤(1978-),男,漢族,江蘇南京人,博士研究生,南京師范大學泰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古代小說戲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