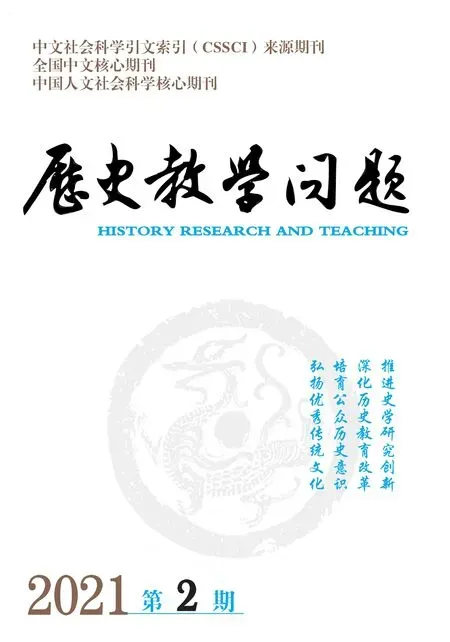奪命的流感:大正中期日本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及危機應對
孫 志 鵬
明治維新以降,日本采取開國進取之方針,人員和商品的海內外流通日趨頻繁。但是流入日本本土的不僅有資本和工業品,還有在世界各地蔓延的傳染病。霍亂、鼠疫等烈性傳染病,讓近代日本人親身體驗了“文明的苦果”。1918 年西班牙流感是第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傳染病,日本自然不能避身事外。西班牙流感主要癥狀與感冒相似,并非烈性傳染病,此后也未再發生,故而在日本曾長期處于“有記錄而無記憶”的狀態。①近40 年來,國外學界從傳播學、統計學、醫學史、社會史等視角,考察了西班牙流感在日本的傳染路徑、死亡率分布、典型癥狀及并發癥、致病原因、對特定人群的影響等,但對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民間社會的具體防治措施著墨不多。國內學界尚未見專題研究。②“奪命的流感”③與霍亂、鼠疫一樣,都是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政府首先要考慮的是如何應對危機。因此,本文擬從大流感在日本的傳播狀況及統計學分析、中央政府的防治方針、地方政府和民間社會的防治措施等方面,分析大正中期日本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基本模式,窺探近代日本公共衛生制度的典型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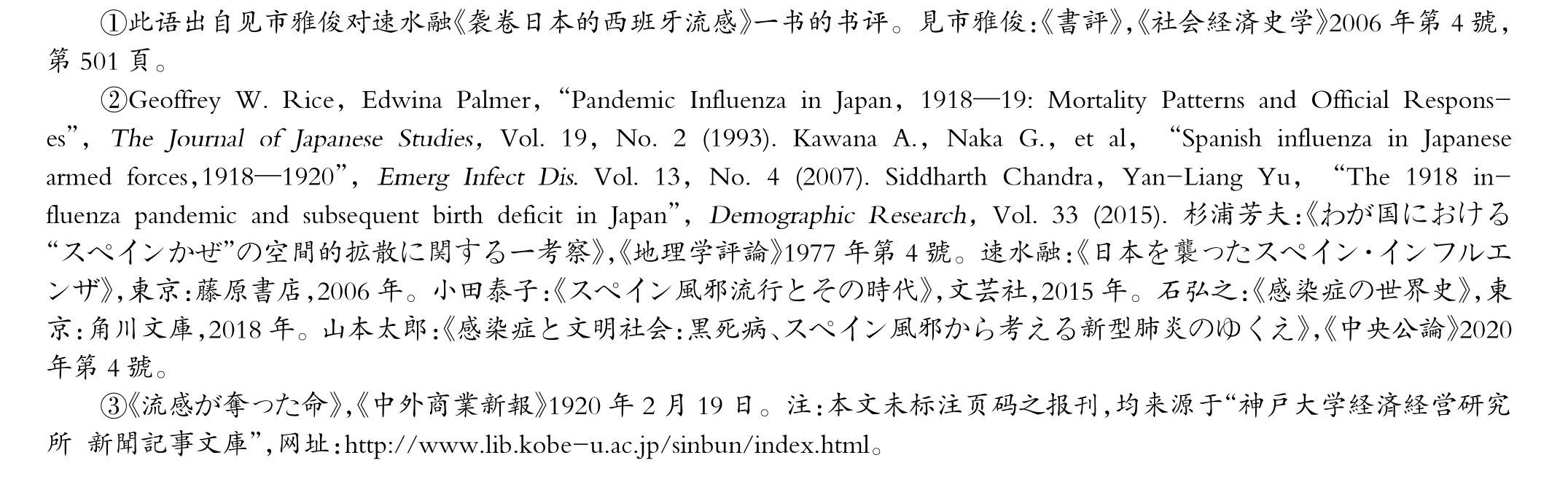
一、流行性感冒在日本的傳播與數據統計
流行性感冒是一種由流感病毒毒株突變引起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常發病于秋冬、冬春季節交替之時,可通過空氣中的飛沫、人與人的接觸、人與被污染物的接觸而傳播,傳染性強、傳播速度快。日本歷史上關于“流感”的最初記載見于平安時代的《三代實錄》,貞觀年間(859—877)曾出現四次“咳逆”流行景象,如貞觀五年(863)載:“自去冬末,至于是月,京城及畿內畿外,多患咳逆,死者甚眾矣。”①近世以來,中醫“風”的概念傳入日本后,常稱之為“風疾”“風邪”“感冒”。②明治中期,1889 年冬暴發于俄羅斯的流感傳入歐洲后蔓延至北美,內務省指出流感“傳染迅速且流行區域廣泛,……此病之流行不分人種、東西、冷熱”。③各府縣也先后發布告示,提醒民眾注意并統計患病人數,如大阪自初發至7月初共上報患者3287 人,④東京在整個流行期間共有患者約15 萬人,而日本患者總數約占全國人口的1∕10。⑤盡管如此,根據1880 年《傳染病預防規則》(其中規定了6 種法定傳染病,即霍亂、傷寒、痢疾、白喉、斑疹傷寒、天花),⑥日本政府并未將俄羅斯流感作為全國性傳染病,而是放任各府縣及個人自行應對。1897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傳染病預防法》,新增了猩紅熱、鼠疫兩種法定傳染病。⑦1917 年,在大日本國民教育會編寫的傳染病預防冊中,根本沒有提及流行性感冒。⑧因此,當1918 年西班牙流感侵襲日本全島之時,日本政府起初并未予以重視,而當疫情暴發后又發現沒有應對全國性流感的前期經驗可循,以致錯過了防治大流感的窗口期。
由于流行性感冒在日本不屬于法定傳染病,醫生在收治流感病人時,無需遵照規定上報衛生科,故而當日本政府試圖追溯西班牙流感在日本的傳入路徑時,根本無法確認傳染源。根據報紙記載,水島銕也(神戶高等商業學校首任校長)的主治醫生大木,認為水島在1918 年2 月上旬“罹患了流行性感冒,后演變為肺炎,出現40 度的高燒”。⑨不過,普通感冒也會引發肺炎和高燒,難以斷定水島所患之病是否屬于西班牙流感。有人指出1918 年4 月,東京的相撲運動員中出現了“相撲風邪”,⑩但也不能確定具體的傳染路徑。從感染規模上看,內務省根據有限記載,初步推斷1918 年5 月上旬由南洋返航橫須賀的軍艦上的250 名患者,以及9 月初由北美駛入橫濱的船舶上的多名患者,可能是西班牙流感大規模傳入日本的源頭。①橫須賀與橫濱均位于神奈川縣,所以神奈川縣及周邊交通便利之府縣,在第一次流行期間患者人數眾多,關西、中部、東北、九州也幾乎在同一時段暴發,北海道、沖繩亦未能幸免,流感覆蓋日本全國。西班牙流感在日本以1918 年10 月至1919 年4 月為第一次流行,1919 年10 月至1920 年4 月為第二次流行,但后者規模僅為前者1∕10 強,而1920 年冬至1921 年春的所謂第三次流行已經是強弩之末,屬于流感病毒自行消退的時期。

根據日本內務省統計,1918年8月至1919年7月,日本共有流感患者21,168,398人(占全國人口37%),其中死者257,363人(病例死亡率1.22%);?1919年9月至1920年7月,共有流感患者2,412,097人(占全國人口4.2%),其中死者127,666人(病例死亡率5.29%);?1920年8月至1921年7月,共有流感患者224,178人(占全國人口0.4%),其中死者3,698 人(病例死亡率1.65%)。①兩次患病和死亡高峰都出現在第一次流行期間,1918 年11 月、1919 年2 月最為突出。由上可見,第一次流行時期患病率高而致死率低,第二次流行時期患病率低而致死率高。這可能是由于第一次患病的人體內產生了一定免疫力,且流感病毒本身在第二次流行時發生“抗原漂移”(antigenic drift)而毒性增強,②導致很多躲過第一次流感的人卻因病情惡化、引發肺炎等并發癥而喪命于第二次流行。③
在三次流行期間,從地域分布上看:東京患者總數最多(1,914,409 人),愛知(1,070,795 人)、兵庫(965,208 人)、大阪(888,716 人)次之;東京死亡總數最多(26,873 人),兵庫(23,409 人)、大阪(22,043人)次之;高知、沖繩患者總數(死亡總數)較少,分別為152,362 人(1,415 人)、117,246 人(2,421 人);④死亡率最高的是大阪(24.8‰),兵庫(24.2‰)次之,最低的是愛知(8.8‰),高知(9.0‰)次之,東京(14‰)屬于平均水平。總體上看,在患、死者數中,關西地區高于關東地區,本州島、九州島高于四國島、北海道、沖繩。這表明西班牙流感與各地域的人口密集度、交通便利程度具有高相關性,符合人際傳播傳染病的特征。
以1919—1920 年為例,從性別比例上看:5 歲以下和81 歲以上的女性患者略高于男性,6—80 歲的男性患者略高于女性;總體上,男性患者數(115,626 人)略高于女性(110,501 人),男性死者數(6,203 人)略高于女性(6,114 人)。從年齡段分布上看:21—30 歲、11—20 歲、31—40 歲患者率(死亡率)分別為18.16%(22.46%)、18.06%(12.83%)、16.28%(17.36%);61—70 歲、71—80 歲、81—90 歲患者率(死亡率)分別為3.26%(4.26%)、0.88%(1.41%)、0.11%(0.23%)。可見,西班牙流感對青少年傷害最大,尤其是21—30 歲的青年人,患病率和死亡率均為最高,而對70 歲以上的老年人傷害最小。從職業上看:平均感染率為5.15%,農業人員感染率(41.11%)最高,畜牧業(12.28%)次之,感染率最低的是化學制造業(0.12%),水產制造業(0.22%)次之。⑤這與流感病毒可能以雞和豬為宿主有關。
二、中央政府的指導性防治方針
1918 年春,西班牙流感傳入日本之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寺內正毅內閣將主要精力投注于通過西原借款獲得在華利權、謀劃出兵西伯利亞,并不關心流感問題。在流感暴發前的窗口期,即1918 年8—9 月,日本正處于波及全國大部分地區的“米騷動”以及由此引發的國內政權交替的敏感時期,內政問題的緊迫性也遮蓋了政府對“特種感冒”的關注。1918 年9 月29 日,日本歷史上第一位平民首相原敬正式拜受大命組閣,大正民主主義運動終于在政治上結出碩果。但是,10 月9—20 日,日本在孟買、上海、香港、新加坡、舊金山的駐外領事官,報告海外各國出現“惡性感冒”,“病毒猛烈無可比擬,死者多斃命于肺炎或心臟麻痹,死亡率超過5%”等,提醒外務省注意防范。⑥新上任的首相原敬也出現感冒癥狀,10 月26 日的日記中記載:“昨夜受邀參加北里研究所財團法人的祝賀宴,席間罹患風邪,夜里發燒至38.5 度。”29 日記載:“上午從腰越回京,近來風邪在各地傳播,變成流行感冒(俗稱西班牙風)。”⑦
1918 年10 月23 日,內務省衛生局長向警視總監和各地方長官發出了第一份“關于預防惡性感冒”的通告,提醒各部門注意。11 月13 日,衛生局長要求恩賜財團濟生會派遣醫生到山間偏僻之地進行醫療救濟。⑧但是,內務省對此次“惡性感冒”的病因、傳播途徑、防治措施等關鍵信息,沒有任何指示或建議,仍由地方和個人自行應對。直到“比兇暴的德國更兇猛、比令人恐懼的霍亂和鼠疫更兇惡的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再次席卷日本時,⑨1919 年1 月下旬內務省才如夢初醒,將“流行性感冒”列為“指定傳染病”,⑩緊急命令各府縣統計本地自流感發生以來至1919 年1 月15 日的病例數量以備參考,同時匆忙起草《流行性感冒預防心得》,印刷5 萬份配發至各地。2 月1 日,內務省在應對無措之際,只能要求各地方長官“廣泛促進普通國民的自覺,繼續努力”,①同時駁回了各縣希望由國庫劃撥防疫費的申請,將防治流感的首要責任加諸地方政府和國民身上。

《流行性感冒預防心得》體現了內務省應對流感的前期措施,包括四個主題:(1)流行性感冒如何傳染?“流行性感冒是一種由人傳染人的疾病,罹患流感者打噴嚏和咳嗽時,會有肉眼看不見的細微泡沫飛入空氣中,可達三四尺的范圍,吸入者將罹患此病。……病愈者的鼻咽腔會殘留病毒,……與病人同樣危險”;(2)防止患病,方法是不接近患者、不去人群聚集之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需佩戴口罩、早晚以鹽水或藥水漱口;(3)若已患病,需臥床靜養并及時就醫、只有看護人員才可進入患者房間、遵醫囑防復發;(4)其他注意事項,如保持清潔、先灑水再掃地、開窗通風、以日光或藥劑消毒、在他人面前打噴嚏和咳嗽時要以手絹掩住口鼻、講究衛生公德。①大日本國民教育會編:《日常衛生と伝染病予防心得》,第150—154 頁。不難看出,這些措施雖然首次向民眾解釋了流感的傳播途徑并闡述了一些防治方法,但也存在語言晦澀、條目復雜、重點不明等問題,不利于應對流感這種突發傳染病。
在隔離措施上,內務省雖然對民眾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進出學校、工廠、娛樂場所等做出限制性規定,但并未禁止人群聚集,在東京、神奈川、京都、兵庫等疫情重災區,甚至出現了依照此前防治霍亂、痢疾等傳染病時經常采取的召集群眾現場召開通俗衛生講話會或觀看動畫短片的經驗性行為,反而助長了流感的傳播;尤其是在各種預防宣傳中,只強調隔離病患和保持社交距離,但沒有提到“退燒”措施,導致很多人在1919 年春死于高燒下的肺炎,因而在第一次流行期間防治和醫療成效有限,先后出現高患病率和高死亡率。
總體上看,在西班牙流感第一次流行時期,日本內務省在針對傳染病的現有治理體系與面對新型傳染病時的預期有效治理能力之間,存在明顯的“治理滯距”。②朱靜輝、熊萬勝:《治理滯距:新公共衛生事件對現代治理體系的挑戰》,《探索與爭鳴》2020 年第4 期。當內務省開始重視流感時,病毒已經發生變異,因流感引發的肺炎、腦膜炎、中耳炎等并發癥成為主要死因,死亡率迅速攀升。1919 年2 月,日本全國人口患病率為15.74‰,比1 月中下旬(8.67‰)高出近一倍,這正是防治遲緩與應對不當的直接后果。
鑒于第一次流行釀成的“慘禍”,同時也在實戰中積累了防治流感的具體經驗和技術,在第二次流行到來之前,內務省提前做好了防備。1919 年10 月22 日,內務省又印制了5 萬份《預防心得》(此次加上了“預防接種”一項)分發至各府縣,同時注意到在防治流感這種“人傳人”的傳染病時,個人的自律性非常重要,因此內務省再次強調“宣傳預防方法,喚起國民自衛心”。③內務省衛生局編:《流行性感冒》,第122 頁,第123—135 頁。1920 年1 月,內務大臣床次竹二郎在“內務省訓令第一號”中提醒各府縣注意使用口罩、預防注射和漱口消毒等。④《內務省訓令第一號》,《官報》第2232 號,1920 年1 月15 日,第217 頁。鑒于第一次流行期間存在宣傳用語不易被普通民眾理解、病例報告制度不完善、醫療資源不足等問題,內務省在第二次流行期間采取了一些新的防治措施。
首先,將預防心得中的生僻用詞改為口語化詞匯、將冗長的預防說明化約為簡單的口號等。將800字左右的原文提煉為四個短語:“勿近患者、覆蓋口鼻、預防注射、早晚漱口”,醒目地指示預防要旨;隨后制作和印刷了5500 萬份簡單易懂、生動形象的標語、海報、宣傳畫,或張貼于公共場所,或直接分發給民眾,這些舉措取得了顯著的宣傳效果。其次,鑒于第一次流行初期未建立病例報告制度,以致流感病患數量不明與各縣統計信息存在差異等問題,將病例報告制度化和標準化。在流感嚴重的1 月中旬至3 月中旬,采取“日報”,在流行稍緩時為減少地方行政部門工作量而改為“旬報”“半月報”,密切關注疫情整體動向;同時,制定了統一的病例報告樣式,要求各府縣以此為標準上報病患信息。再次,新增和協調醫療資源。鑒于流感期間醫院病床嚴重匱乏問題,內務省建議各地利用已有的傳染病醫院或建立臨時病舍,以提供更多的床位隔離傳染源;內務省派遣了73 名防疫官和64 名防疫員至各府縣,專門負責監督和協調各地防疫事務,盡力做到資源優化配置。最后,招募志愿者。內務省注意到志愿者在流感防治中的靈活性和主動性,鼓勵各地利用公益團體、組織志愿者積極協助防疫工作。⑤內務省衛生局編:《流行性感冒》,第122 頁,第123—135 頁。這些新措施針對性強,更加貼合實際行動,便于各地執行,取得了切實效果。
1920 年5 月初,為了更加有效預防流感并學習先進經驗,內務省派遣防疫官兼內務省技師加藤源三前往美英,參加國際會議、前往各地調查、收集資料等。9 月,內務省委托以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高野六郎為代表的4 名醫學科研人員,為預防流感提供專業意見;隨后,在對全國600 余名醫務工作者問卷調查的基礎上,編纂了比較完備的《流行性感冒預防要項》。1921 年1 月,內務省再次以“內務省訓令第一號”的形式,①《內務省訓令第一號》,《官報》第2526 號,1920 年1 月6 日,第18 頁。向全國發布預防要項,包括病原及傳染路徑、預防方法、醫療及看護、醫療材料供給、貧困救濟等五大項,在預防方法中重點闡述了“切斷傳染路徑”,包括防止飛沫傳染、使用口罩、隔離患者、限制集會、消毒等。②內務省衛生局:《流行性感冒ノ豫防要項》,東京:內務省衛生局,1921 年,第1—7 頁。防治措施更加專業化和系統化,可謂與國際接軌,達到了先進水平,為后期流感防治提供了藍本。
三、地方政府和民間社會的具體防治措施
盡管日本內務省在應對流感時反應遲緩,但是作為直接受害者的民眾及地方政府,首先感受到了危機的存在,個別縣市早于中央命令采取了有限的救治措施。在1919 年初中央定調以后,各府縣開始大規模落實預防措施,實際執行時既有共性,也有差異。前者體現在啟蒙國民思想,執行佩戴口罩、漱口消毒、預防注射三大指示,派遣巡回醫療隊;后者表現為地方政府以及多樣化社會團體的活動。
與中央政府一樣,宣傳預防知識也是地方政府首先采取的措施,而且花樣百出。在印刷品數量上,內務省只印了5 萬份預防手冊,平均到各府縣僅1千余冊,根本達不到宣傳效果。所以,各地都以地方財政自費增印各種宣傳物分發給民眾,如山梨縣出資150 日元印刷了大小兩種手冊共22500 份,福島縣出資500 日元印刷了10 萬份手冊及宣傳畫,愛媛縣增印了15 萬張海報。在宣傳手段上,各縣既有采取傳統形式者,如在公共場所張貼海報和宣傳畫、制作宣傳板、登載報紙廣告等;更有利用新技術者,如不少縣市廣泛使用的“活動寫真”、③“活動寫真”是明治、大正時期日本人對電影的稱謂,但與電影稍有不同,指的是荒誕的古裝劇和戲劇的真人版。幻燈片,在民眾觀看戲劇的休息時間,展示標語或播放動畫;福島縣利用汽車進行路邊宣講,埼玉縣甚至動用飛機向偏遠地區散發傳單;茨城、島根、熊本等縣通過學校教育,讓中小學生回家時將簡單易懂的預防知識告知家人,既教會了學生,也達到了廣泛宣傳的目的。不過,很多縣市普遍采取的個別宣傳措施反而不利于流感防控,如東京、京都、兵庫等地召集民眾在現場召開衛生講話會;琦玉縣很早就發現集會有增加流感傳播的可能,拒絕采用這種形式。④內務省衛生局編:《流行性感冒》,第152—160 頁,第161—176 頁。總之,雖然各地在宣傳上耗費了不少資源和精力,但主要目的是為了喚醒民眾的“自衛心”,以降低醫療和行政成本。整體而言,在第二、三次流行期間,地方政府宣講的預防措施,民眾基本都能遵守,收效顯著。不過,由于日本都道府縣情況復雜,執行效果不一。高知、琦玉、茨城等縣宣傳和預防措施比較到位,巖手、岐阜、大分、兵庫等縣存在宣傳不力、輕視統計、執行不到位等懶政現象,造成區域防疫差異較大,不利于遏制流感傳播。
由于當時國際醫學界未能確定流感病因,只是知道流感通過飛沫傳播,所以佩戴口罩就成為最基本的防護措施。口罩成為整個社會的緊俏商品,一些不法商人便開始投機倒把,口罩價格從5—15 錢左右暴漲至35—80 錢甚至更高,⑤1 日元=100 錢且限量售賣。這既影響了正常的市場秩序,也容易因口罩短缺而引起社會恐慌,后者正是政府最為擔憂之事。日本政府雖然在個別地區(如東京、栃木、滋賀、福井)采取了由警察嚴格管控口罩投機商或直接命令降價的行政手段,但更常見的做法是迅速增加產量、成本價發售、滿足貧困者需求、鼓勵家庭自制口罩,通過提高供應量和減少需求量的溫和調控方法,壓低市價、打擊口罩投機商。如靜岡縣,當地口罩價格曾一度飆升至每副20—50 錢,縣政府組織服裝學校、中小學女生制作口罩,先后向社會和市場投放10 萬余副,直接將市場價格拉低至7—15 錢;1919 年1 月流感高峰時,神奈川縣口罩價格暴漲,縣政府從救濟協會調入口罩原料,讓工業學校提供金屬部件,8 所高中女校學生在不影響學業的情況下趕制口罩,幾天內便制作了11600 副,最后委托紅十字會將其一半批發給學校、公司,另一半在市場直銷,售價僅5 錢,取得良好效果;福島縣以紅十字會捐助的2000 日元購買了15000 副口罩,分發給貧困者;群馬縣鼓勵民眾自制口罩,新潟、茨城、千葉等縣佩戴口罩的人數明顯增多。⑥內務省衛生局編:《流行性感冒》,第152—160 頁,第161—176 頁。
在提供漱口水和預防接種上,地方政府的思路與提供口罩基本一致。針對前者,主要以縣財政為主,直接購買漱口水原料并委托藥廠生產,在公共場所免費提供漱口水,或公開漱口水的簡易配方,讓地方政府或社會團體自行調配;針對后者,基本以免費為主,優先接種醫護人員、學生、貧困者,愛媛縣還專門組建了3 個汽車接種隊,前往交通不便之地為貧困者免費接種。接種人數最多的是新潟縣(695,274人),其次是東京(591,770 人)、埼玉縣(330,559人),最少的是石川縣(624 人),全國接種人數在500萬人以上。①每支接種液的價格在15 錢左右,這對于地方財政而言,可謂是不小的負擔。②更令人惋惜的是,西班牙流感是由病毒引發,當時的醫療認知還處于細菌學范式之下,所謂預防接種并非針對“病毒”,而是針對細菌性感染及肺炎并發癥,療效自然受限。不過,預防接種展現了地方政府積極的流感防治態度,也發揮了穩定民心的作用,值得肯定。
在預防措施中,還有針對患者的隔離措施。地方政府一方面在內務省指導下利用傳染病醫院或擴建隔離病舍,以容納更多患者,同時設置免費診所、發放診療券,嚴格看護制度,防止家屬探望病患時新增傳染源;另一方面對民眾的生活行為進行限制,如禁止隨地吐痰、不佩戴口罩禁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工廠企業有義務為工人提供口罩和漱口水、體溫超過37.5℃禁止進入學校、短期關閉患病人數較多的學校和工廠、避免葬禮上人群聚集、在火葬場限制吊唁死者的人數等。③這些限制措施雖然能夠有效遏制流感傳播,但由于各地僅是有條件限制而非完全禁止人群聚集,如當時歐美的幾個國家都關閉了劇院和電影院,而日本的車站、劇院、電影院、旅店、飯店等在流感期間正常營業,所以上述防治措施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又被抵消。
除了各府縣的官方行為外,各府縣還與各種社會團體合作,如紅十字會及各府縣支部、恩賜財團濟生會、各地醫師會和衛生組合、在鄉軍人會、青年團、婦女會、花之日會等,積極在各地進行宣傳、分發口罩、預防接種、提供醫藥品、指導隔離方法等活動,有效補充了政府行政功能的不足。其中,比較重要的便是組建小型巡回醫療隊。流感暴發后,不單是普通民眾罹患此病,大量醫護人員因更早、更頻繁地接觸流感病人而患病甚至死亡,一時間造成全國醫護不足,病人就診需長時間排隊等待,醫護人員勞累不堪,醫療資源擠兌嚴重,不少家屬正是在醫院罹患流感,更加不利于流感防控。有鑒于此,內務省和地方政府都積極號召各社會團體就近組建巡回醫療隊(一般由3—5 名醫護人員組成,常見模式是4 人隊,即1 名醫生、1 名藥劑師、2 名護士),尤其是彌補鄉村醫療的漏洞。如,京都府組建2 支市內救療隊,協助各部門治療;神奈川縣設置2 支救護治療隊,攜帶醫藥品赴各戶治療,共診治2733 戶(3283 人);福井縣特設救護隊,專門到交通不便和醫療困難的偏僻鄉村,對無法就醫的患者,不論癥狀輕重,一律免費救治,效果顯著;香川縣的5 人救療隊,在流感最猖獗時,深入木田郡奧鹿村救治了91 名患者。④
西班牙流感在日本肆虐期間,對普通民眾造成極大影響,個別家庭甚至全部罹患流感,以致造成“一家全滅的悲劇”。⑤在這種遠超人類控制能力的突發疫情下,很多人紛紛前往神社祈禱,希望神佛能早日驅逐病魔。⑥不過,對于絕大多數患者及其家屬而言,采取各種可能的手段進行治療才是最自然的反應。社會上層家庭有人患病時,每個病人至少會專門雇請一位護士進行照護,有時甚至多達3—5 名,更使醫護短缺的局面雪上加霜。同時,日本的醫療資源主要用于應對肺炎并發癥等重癥患者,對輕癥患者則鼓勵居家治療。因此,無法在醫院接受治療的情況下,家庭護理就成為民間社會最常見的治療方式。通常首先是臥床靜養,其次是采用各種方法退燒,如服用傳統漢方藥、用冰塊為身體降溫等,最后是喝熱水、綠茶、熬制的雞湯以補充體液和增強抵抗力,或者食用被認為對治療流感有效的蜜柑等各種瓜果蔬菜。⑦總之,日本民眾日常的衛生習慣、家族互助傳統、傳統漢方醫學中的風寒感冒和養生觀念,⑧以及面對急癥而大膽用藥的醫生和江湖郎中,有時也能產生較好的治療效果。醫生杉本宇吉甚至根據古方,誤打誤撞地使用“鹽酸規尼涅(奎寧酸)”治療流感,效果明顯且成本低廉,能夠為一般民眾所承受。①杉本宇吉:《流行性感冒治療法》,東京:東京堂書店,1920 年,第6—7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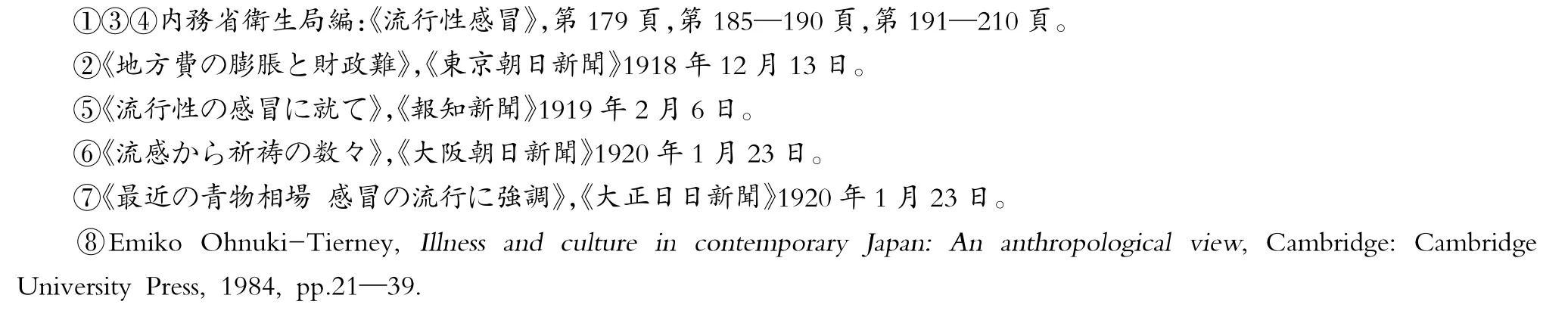
四、結論與反思
1918 年春,西班牙流感由海外傳入日本;1918年冬,患病率達到頂峰;1919 年春,死亡率再創新高。1918—1921 年間的三次流行,共造成近2400 萬人感染(約占全國人口42%)、39 萬人死亡(病例死亡率1.6%)的慘狀,與1923 年的關東大地震(傷亡10 萬人)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面對這種由新型傳染病誘發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日本中央政府起初未予重視,產生了“治理滯距”。隨著疫情暴發,內務省在無前例可循的慌忙應對中,提出大力宣傳疾病知識以喚醒國民“自衛心”和以佩戴口罩、漱口消毒、預防接種為核心的三大預防措施等指導性方針。但是,這種在應對細菌性傳染病時累積的經驗,不足以有效應對病毒性傳染病。有了前車之鑒,內務省在第二、三次流行到來之前,提前采取了更加貼合實際和系統化的應對措施,相對有效地遏制了流感的大規模傳播及肺炎并發癥造成的影響。當然,西班牙流感的消退更可能是病毒良性變異的自然結果,而非人力所為。而且,近代日本的公共衛生歸屬于警察行政,在流感防治過程中,內務省通過發放印刷品、限制社交等形式,直接將國家意志傳達給國民,國民的身體甚至動作都進一步被置于公共權力的塑造和監控之下,強化了公共衛生的權力嵌入結構。
在集體防疫過程中,地方政府遵照中央指示,首先采取了在公共場所張貼簡單形象的標語、海報等方式,宣傳防控流感的知識,啟發國民“自衛心”。其次,各府縣最主要的實際行動體現在,通過組織女學生和志愿者趕制口罩進而低價銷售或直接向貧困者免費提供口罩等措施,既設法滿足民眾的口罩需求,同時打擊口罩投機商,恢復市場秩序,維持地方穩定。最后,通過迅速補充醫護隊伍和派遣巡回醫療隊的方式,為小城市尤其是偏遠鄉村提供流動醫療救助。
民間社會在面對醫療資源不足、西藥未見成效的情況下,雖有求助于神佛保佑的無奈之舉,但更多的是采取家庭護理、臥床靜養、服用治療感冒的傳統草藥、補充營養等措施,表現出積極的自我救治態度。盡管效果往往并不理想,但并未將流感的厄運歸咎于國家,更鮮見訴諸社會暴力,既反映了日本政府通過宣傳預防方法喚醒國民“自衛心”的策略有效性,更體現了日本國民“克己奉公”的集團主義精神。
總之,從日本政府和社會應對西班牙流感的過程及措施可以看出,中央指導、地方執行、全民動員是近代日本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基本模式,凸顯了中央集權和集團主義的特征,公共衛生行政的權力嵌入和身體規訓均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