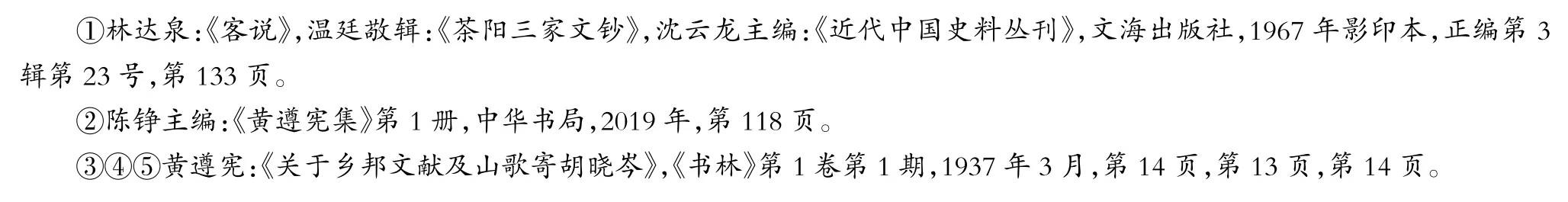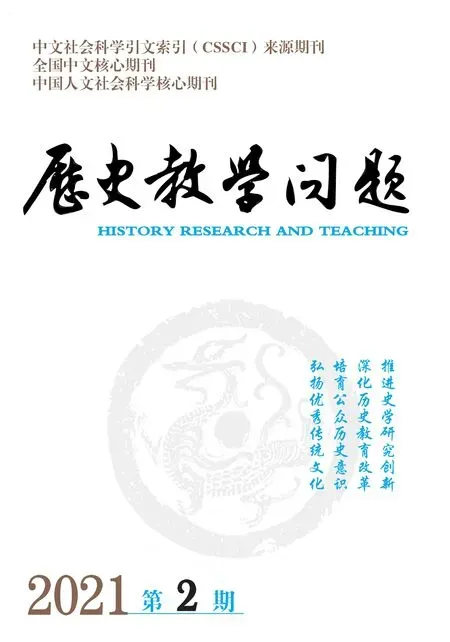傳教士歐德理的客家婦女研究
楊 揚(yáng)
一、引 言
有學(xué)者在回顧現(xiàn)代客家研究史時(shí)強(qiáng)調(diào),20 世紀(jì)90 年代以來(lái),專(zhuān)題性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現(xiàn),是客家研究深化的一個(gè)表征。①在這些專(zhuān)題性研究成果中,客家婦女研究占有一席之地。其中,人類(lèi)學(xué)家李泳集的《性別與文化:客家婦女研究的新視野》和歷史學(xué)家謝重光的《客家文化與婦女生活:12—20 世紀(jì)客家婦女研究》是常被提及的兩部力作。這兩部力作有一共同目的,即探究客家婦女與客家文化的關(guān)系。本文所涉及的對(duì)象即傳教士歐德理(E. J. Eitel,1838—1908)的客家婦女研究,也有同樣的旨趣,不過(guò)卻是上述兩書(shū)出現(xiàn)疏失或未置一詞的。前書(shū)雖然提到“英國(guó)人愛(ài)得爾(E. J. Eitel)在其所出版的《中日訪問(wèn)記錄》(1870)一書(shū)談到:‘……客家婦女更是中國(guó)最優(yōu)越的婦女典型’”,②但是復(fù)核此話,國(guó)籍、文獻(xiàn)形態(tài)與出版時(shí)間、引文均存在問(wèn)題。后書(shū)雖然指出客家婦女“清末已引起……外國(guó)傳教士的注意”,③但是翻遍全書(shū),未見(jiàn)歐德理的身影。有鑒于此,本文將對(duì)傳教士歐德理的客家婦女研究做系統(tǒng)深入的討論,以為當(dāng)今客家婦女研究者提供一個(gè)較早且準(zhǔn)確的學(xué)術(shù)史參考系。
上文提到,有學(xué)者在涉及歐德理的客家婦女研究時(shí)出現(xiàn)疏失,故而有必要在正式討論前做一糾正。歐德理不是英國(guó)人而是德意志人。他受巴色會(huì)派遣于1862 年來(lái)到香港,由于巴色會(huì)的傳教對(duì)象是客家方言群,故而他一開(kāi)始便到鄰近香港的新安縣客家社區(qū)傳教,雖然到1865 年時(shí)因?yàn)榻Y(jié)婚問(wèn)題被迫離開(kāi)巴色會(huì)加入倫敦會(huì),但是由于他掌握的客家方言正是倫敦會(huì)的傳教對(duì)象博羅縣客家人所說(shuō)的語(yǔ)言,故而他又前往博羅縣客家社區(qū)傳教,直到1870 年才離開(kāi)此地。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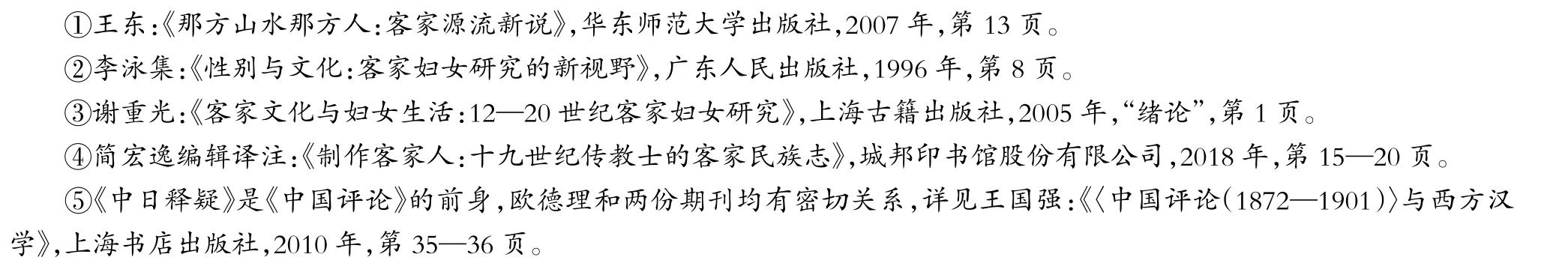

檢視歐德理的客家婦女研究相關(guān)文章,筆者并未發(fā)現(xiàn)“客家婦女更是中國(guó)最優(yōu)越的婦女典型”一言。既然沒(méi)有此言,那么歐德理關(guān)于客家婦女說(shuō)了什么?他的目光聚焦在客家婦女與三種客家文化現(xiàn)象的關(guān)系上。
二、歐德理的客家婦女研究之內(nèi)容
客家風(fēng)習(xí)是第一種客家文化現(xiàn)象。在歐德理筆下,風(fēng),即風(fēng)俗(custom),習(xí),為習(xí)慣(manner)。他在談?wù)摽图绎L(fēng)俗時(shí),一上來(lái)就指出,客家人、本地人、福老人③在風(fēng)俗上“最明顯的差別就是婦女”,④由此可知,他把客家婦女當(dāng)作客家風(fēng)俗特色的例證者。接著,他從五個(gè)方面比較了客家婦女和本地婦女、福老婦女的不同。其一,勞動(dòng)分工。客家婦女是主外的,她們像男人一樣負(fù)擔(dān)大部分的戶外工作:把重貨帶去市場(chǎng)、把干草帶去爐灶、整地、挑水、到遠(yuǎn)處割草、帶著農(nóng)產(chǎn)品赴墟等。本地婦女和福老婦女則是主內(nèi)的,她們除了做針線活之外,主要工作是操持家務(wù)。其二,對(duì)外態(tài)度。如果村落有洋人到訪,客家婦女不害怕他,本地婦女和福老婦女則會(huì)躲在房屋門(mén)后。其三,身體形態(tài)。客家婦女即使家庭有錢(qián)也很少纏足,本地婦女則家庭小康就會(huì)纏足,福老婦女也會(huì)纏足但是沒(méi)有本地婦女普遍。其四,婚姻情況。一夫多妻的現(xiàn)象在本地人中常見(jiàn),販賣(mài)婦女的現(xiàn)象則常現(xiàn)于富裕的福老人中,客家人較少有這兩種惡習(xí)。其五,女?huà)朊\(yùn)。殺女?huà)肫毡榇嬖谟诟@先撕涂图胰酥校镜厝藙t少有此種惡習(xí)。⑤就前四點(diǎn)來(lái)說(shuō),由于客家婦女自食其力、對(duì)外友好、身體少受摧殘、婚姻較為簡(jiǎn)單,故而歐德理得出客家風(fēng)俗“最值得贊賞”的結(jié)論,⑥反過(guò)來(lái)說(shuō),客家婦女是客家風(fēng)俗美善這面的化身。但是,就第四點(diǎn)而言,由于客家婦女也有悲慘境遇,故而歐德理覺(jué)察到客家風(fēng)俗恐怖的一面,反過(guò)來(lái)說(shuō),客家婦女也是客家風(fēng)俗丑惡那面的載體。
客家婦女除了是客家風(fēng)俗特色的例證者,她們也是客家習(xí)慣特點(diǎn)的例證者。歐德理在講到習(xí)慣之一的打扮時(shí)指出,客家人和本地人、福老人在男性打扮上差別細(xì)微,但是在女性打扮上差別“相當(dāng)明顯”。⑦概言之,歐德理認(rèn)為,本地婦女和福老婦女的品味完全相同,客家婦女則展現(xiàn)與前兩者不同的原創(chuàng)性。⑧具說(shuō)之,歐德理作了從頭到腳的摹寫(xiě):客家婦女用一銀環(huán)把頭發(fā)束緊在頭的正上方,夏天時(shí)戴上一頂涼帽,涼帽中間有讓發(fā)髻穿過(guò)的圓洞,發(fā)髻和圓洞配合可以把涼帽牢牢固定住,冬天時(shí)則把一塊藍(lán)布披在頭上然后用棉條固定住,本地婦女和福老婦女討厭這種頭部打扮,覺(jué)得它像獸角或茶壺,她們會(huì)把頭發(fā)編起來(lái);客家婦女的肩上會(huì)垂下一片方形、扁平的小銀飾,這是她們特有的配件;客家婦女外衣的袖子比本地婦女和福老婦女的窄;客家婦女會(huì)系腰帶,這也是他們特有的配件;客家婦女的鞋子是圓頭的且向上彎曲,本地婦女和福老婦女的鞋子則是尖頭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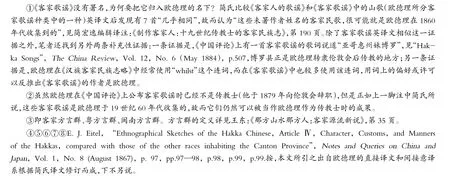
客家歌謠是第二種客家文化現(xiàn)象。歐德理將客家歌謠分成6 個(gè)種類(lèi),根據(jù)他給出的這6 種客家歌謠的定義或舉出的對(duì)應(yīng)文本,可知客家婦女是其中至少4 種客家歌謠即山歌、和歌、采茶歌、小兒歌的創(chuàng)作者。由于歐德理提供的和歌、采茶歌、小兒歌的文本無(wú)漢文歌詞,②而山歌的文本多有漢文歌詞,故而以下以山歌為例展開(kāi)討論。從山歌漢文歌詞來(lái)看,歐德理呈現(xiàn)的客家婦女創(chuàng)作之客家歌謠的內(nèi)容可以歸納為三個(gè)主要方面:連情、送別、求友。
連情,指客家婦女在婚姻出現(xiàn)問(wèn)題時(shí)口吐苦水。列三首歌謠如下:“更深深時(shí)夜又寒;苧蔴績(jī)盡油點(diǎn)干。男人冇句真說(shuō)話,害咱一夜門(mén)唔閂。”③“亞妹生成鳳凰身:朝日擔(dān)柴受苦辛。早知今日窮難過(guò),何不當(dāng)初嫁好人。”④“亞哥說(shuō)話不公平。世間由命不由人。官人都系男人做:亞哥何不做官人?”⑤送別,指客家婦女因?yàn)檎煞蛲獬鲋\生而心生不舍。也列三首歌謠如下:“送郎送到十里亭,再送十里難舍情:再送十里情難舍:十分難舍有情人。”⑥“送郎送到屋檐下,眼淚流來(lái)把袖遮。手中捉竟郎衫袂,問(wèn)郎何日轉(zhuǎn)回家。”⑦“送郎送到伯公亭:洗手燒香拜神明。燒香拜神無(wú)別意,保佑咱郎早回身。”⑧求友,指客家婦女熱切希冀結(jié)識(shí)如意郎君。亦列三首歌謠如下:“日頭一出炳怱怱,小妹門(mén)邊種壢蔥。日里愁來(lái)冇蔥摘,夜里愁來(lái)冇老公。”⑨“有好日頭冇好天,有好花木冇好園,有好禾苗冇好谷;有好女子冇人連。”⑩“日頭一出凹里黃。那介亞姑唔想郎?枕冷衿寒猶且可,蠔情一發(fā)正難當(dāng)。”①
為何連情、送別、求友成為客家婦女創(chuàng)作之客家歌謠的主要內(nèi)容?歐德理未予解釋。羅香林在客家歌謠研究的經(jīng)典性專(zhuān)著《粵東之風(fēng)》中,從普遍的人類(lèi)心理與特殊的客家社會(huì)環(huán)境之結(jié)合的角度提出解釋。筆者大體同意羅氏的解釋?zhuān)识迷撜撘怨┳x者參考:“性的愛(ài),是人類(lèi)所同有的。有了性愛(ài),便有欲求”,“不幸了,欲求橫被障礙竟達(dá)不到,那么‘憤憤于心’,‘神志沮喪’,嗟嘆哪,呻吟哪”,客家“青年男女所具有底性愛(ài)的強(qiáng)度,自然也是不消說(shuō)的。可是一不幸受了舊禮教和舊宗法的壓迫”,“夫婦間若有了不融洽的地方,也只好抱恨在心,不敢明目張膽地在家長(zhǎng)前說(shuō)話”,“因此許多青年男女的性受(筆者按,應(yīng)為愛(ài)),都不能于正當(dāng)?shù)牡胤桨l(fā)泄,然而又不能壓迫地消滅,而且還要依物理學(xué)上彈力的定律,發(fā)出他們和她們的反抗力來(lái),所以一片‘連情’的呼聲便直破禮教的綱維而出”。“不幸受了地理上的影響,許多青年夫妻,因?yàn)橐S持各人的生計(jì),不能不頻唱驪歌,住在山谷的女同胞們,更是因?yàn)槌3H芜^(guò)苦的勞作,覺(jué)得生活枯燥,恰巧家里要叫她們上那禮綱不到的山崗上去采樵,而她們的性愛(ài)的沖動(dòng),也就使她們自然而然的發(fā)表她們求友的唱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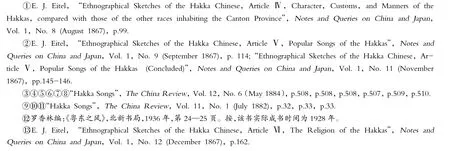
客家宗教是第三種客家文化現(xiàn)象。在歐德理筆下,客家婦女是客家宗教的參與者。雖然多數(shù)時(shí)候歐德理是用客家人這個(gè)不分性別的稱(chēng)謂來(lái)論述客家宗教的參與者,但是他還是提供了五段特別標(biāo)明客家婦女是客家宗教的參與者之論述。第一段論述與佛教神祇觀音有關(guān)。歐德理認(rèn)為,觀音在客家人中難說(shuō)流行,例外是客家婦女農(nóng)歷每年兩次去觀音廟享用以觀音之名奉獻(xiàn)的施食。?第二段論述與客家人的迷信有關(guān)。歐德理指出,客家人的迷信起因于他們對(duì)于惡魔的持續(xù)性恐懼,為了降低這種持續(xù)性恐懼,他們倚賴宗教專(zhuān)家的服務(wù),客家婦女扮演的仙婆(仙姑)就是宗教專(zhuān)家之一。①第三段論述與社公社母的崇拜儀式有關(guān)。歐德理看到,客家人的社公壇位于村落旁邊,是露天的。農(nóng)歷每年仲秋和仲春,每個(gè)村落的長(zhǎng)者會(huì)派一位信使去按家庭收錢(qián)用來(lái)買(mǎi)相當(dāng)數(shù)量的豬肉,然后在社公壇旁邊煮,如果錢(qián)是自愿捐獻(xiàn)的就還會(huì)置些酒。當(dāng)萬(wàn)事齊備后會(huì)敲鑼打鼓以為信號(hào),所有村民,男人、婦女和小孩,就從自家房屋趕來(lái)社公壇。他們各帶碗筷,圍坐在社公壇周邊的草地上,如果草地潮濕,他們還會(huì)帶席子給小孩坐。然后村民在一位拿著交錢(qián)名單的長(zhǎng)者的指揮下分發(fā)豬肉、粥和酒,食物分配原則是看人數(shù)而非錢(qián)數(shù)。分到食物后,他們平靜地分散到草地或圍繞社公壇的樹(shù)下享用它們,從吸奶的嬰兒到銀發(fā)的老婦女都有份,會(huì)餐通常在傍晚舉行,伴著余暉,景象美妙。②
第四段論述與冥婚儀式有關(guān)。歐德理說(shuō)道,客家人深信靈魂不滅和另一個(gè)世界的存在,故而如果小男孩在父母為他找到妻子之前就去世,父母會(huì)向鄰居和朋友詢問(wèn)他們有無(wú)同齡的夭折女孩,如果有,兩位夭折小孩的父母會(huì)為小孩舉行莊嚴(yán)的訂婚儀式,所有細(xì)節(jié)都仿照活人的婚禮,就像新娘和新郎都還活著一樣,客家人相信這樣可以結(jié)合兩個(gè)小孩的靈魂,讓他們不管在哪里都像有真正的婚姻生活一樣。③
第五段論述與使受驚小孩康復(fù)的儀式有關(guān)。歐德理提到,如果有小孩沒(méi)有什么明顯的原因就突然生病,通常客家人會(huì)認(rèn)為小孩受驚了,這時(shí)小孩的母親或祖母會(huì)拿一個(gè)蛋、一碗米飯、一件這位小孩的外衣,仔細(xì)地卷起來(lái),接著把這些東西擺在灶前屬于司命灶君的神圣空間,然后她點(diǎn)燃乳香,重復(fù)念數(shù)次:“什么驚著小孩?求司命灶君指點(diǎn)保佑!”。之后,她大喊三聲小孩的名字,每次都在名字后面加上“快回臥室與你父母睡”的話,在重復(fù)念著這句話的同時(shí),她把那顆蛋、那碗米飯和那件外衣拿到臥室,然后放在靠近枕頭的床架上,那里是床頭亞公和床頭亞婆的神圣空間,她再次點(diǎn)燃乳香。上述儀式會(huì)在接下來(lái)兩天重復(fù)進(jìn)行。第三天,在床頭亞公和床頭亞婆前點(diǎn)燃乳香后,她把盛米飯的碗和蛋打碎,碗的碎片和蛋清蛋黃被仔細(xì)地檢查,然后在她的眼中顯示出驚到小孩的狗或水牛或馬或其他動(dòng)物的形象,依照每種情況的結(jié)果,她會(huì)去拿相應(yīng)動(dòng)物的毛綁在小孩的身上,她相信這樣會(huì)讓小孩馬上康復(fù)。④
三、歐德理的客家婦女研究之價(jià)值
在歐德理之后,還有其他傳教士關(guān)注過(guò)客家婦女。第一位是畢安(Ch. Piton,1835—1905)。他是法國(guó)人,為巴色會(huì)成員,于1864 年來(lái)華傳教,在客家社區(qū)待了20 年。⑤他于1874 年在《中國(guó)評(píng)論》上發(fā)表《論客家人的起源與歷史》一文。在文中畢安提及歐德理的《漢族客家民族志略》。該文透過(guò)客家婦女看到客家風(fēng)俗的美善一面,說(shuō)她們?yōu)榱恕跋碌馗苫詈桶徇\(yùn)重貨”而“拋棄了荒謬的纏足風(fēng)俗”。⑥
第二位是黎力基(R. Lechler,1824—1908)。他是德意志人,也是巴色會(huì)成員,于1847 年抵達(dá)中國(guó),先是對(duì)閩南方言群傳教,失敗后轉(zhuǎn)對(duì)客家方言群傳教。⑦他于1878 年發(fā)表《漢族客家》一文,登載在《教務(wù)雜志》上。在文中黎力基也提及歐德理的《漢族客家民族志略》。此文留意到客家婦女反映的客家風(fēng)俗的美善這面,講她們“赴墟”“背負(fù)重貨”“從山上割草以作燃料,養(yǎng)豬以為買(mǎi)賣(mài),為全家煮飯,整地”;“不纏足”;“一夫多妻的現(xiàn)象”不常見(jiàn)。⑧此文也留意到畢安未看到的客家婦女反映的客家風(fēng)俗的丑惡那面,發(fā)現(xiàn)“殺女?huà)氲默F(xiàn)象相當(dāng)常見(jiàn)”。⑨此文還留意到畢安未看到的客家婦女參與客家宗教的情形,提及客家婦女扮演的仙婆可以幫助客家人與陰間溝通,并且以一位客家婦女“不認(rèn)為此生有罪,卻因?yàn)榍笆赖男袨椋行〇|西礙著她”的言論說(shuō)明客家人相信輪回。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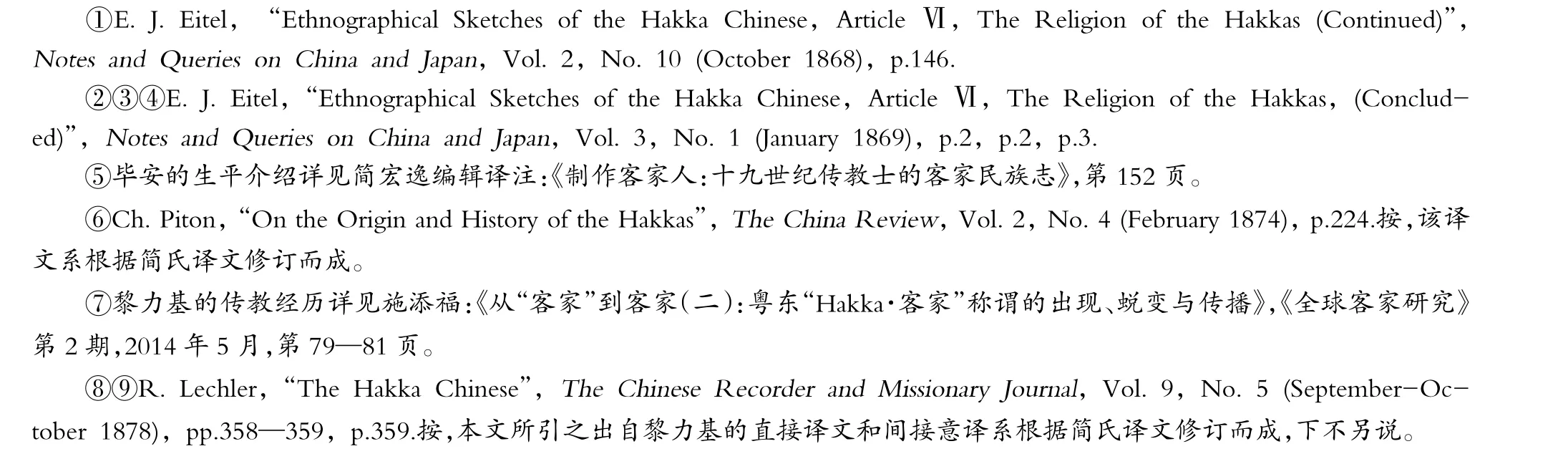
第三位是何必烈(F. Hubrig,1840—1892)。他也是德意志人,于1866 年來(lái)華傳教時(shí)隸屬巴陵會(huì),到了1872 年由于巴陵會(huì)中止在華傳教就轉(zhuǎn)入巴勉會(huì),在這兩個(gè)會(huì)中他都是向客家方言群傳教。1879年3 月,他在柏林人類(lèi)、民族、史前學(xué)會(huì)例行月會(huì)上宣讀《論漢族客家》一德文文章。②有學(xué)者經(jīng)過(guò)對(duì)查,認(rèn)為這篇文章的題材和內(nèi)容類(lèi)似歐德理的《漢族客家民族志略》。③在論述客家婦女與客家風(fēng)俗的關(guān)系時(shí),與畢安和黎力基的文章點(diǎn)到為止不同,該文詳細(xì)得多。就客家婦女體現(xiàn)的客家風(fēng)俗美善這面,他寫(xiě)到:“客家婦女從不抽煙與游戲,她們與丈夫一起在田里工作,把作物帶到市場(chǎng)販賣(mài),在男人的社會(huì)里也行動(dòng)自由。在秋冬兩季,她們從山上割下干草作為燃料,一部分自用,一部分拿去賣(mài)。在沒(méi)有水運(yùn)的地方,你會(huì)看到一大群客家婦女扛著最重的貨物走很遠(yuǎn)的路橫跨山嶺”;“即使是家里最有錢(qián)、身分最尊貴的客家婦女,都保持天然足,因此可以比本地人和福老人的婦女更自由地活動(dòng)”,“雖然工作得比較辛苦,客家婦女作為妻子,看起來(lái)比本地人婦女更快樂(lè),因?yàn)楹笳叱3R渌男℃⑶閶D、奴隸等人分享她的權(quán)利。一夫多妻的現(xiàn)象在客家人之中比本地人來(lái)得少。有錢(qián)的客家人只有在第一個(gè)妻子沒(méi)有為他生下兒子時(shí)才會(huì)娶第二個(gè)妻子,而且必須取得第一個(gè)妻子的同意,且第二位會(huì)成為第一位的侍女”。④就客家婦女體現(xiàn)的客家風(fēng)俗丑惡那面,他說(shuō)道:“很少有客家婦女會(huì)養(yǎng)育超過(guò)一兩個(gè)女兒,其他的都在出生時(shí)就殺掉了。由此可說(shuō),幾乎所有的客家婦女都可以被視為殺嬰兇手。許多殺了四五個(gè)女?huà)耄踔劣袣⒌绞陨系陌咐胪ǔS勺婺笀?zhí)行。女孩也經(jīng)常因?yàn)樨毟F而被殺,由于父母付不起教養(yǎng)她們所需的花費(fèi)。有時(shí)女孩則因?yàn)槊孕疟粴ⅲ捎诟改赶嘈趴梢砸虼苏衼?lái)男孩。當(dāng)有越多的女孩出生,殺嬰的方法也就越殘酷,因?yàn)樗麄兿嘈疟粴⑺赖膵雰簳?huì)轉(zhuǎn)世成為下一個(gè)孩子,所以越殘酷的殺法能夠讓靈魂不希望變成女孩的樣子被生下來(lái)。”⑤另外,該文也論述了客家婦女與客家習(xí)慣的關(guān)系,這是畢安和黎力基未提及的。他將客家婦女的打扮摹寫(xiě)如下:“發(fā)型簡(jiǎn)單,就是往后梳起來(lái),結(jié)成球狀,插上銀簪”,“都會(huì)戴上銀制的粗耳環(huán)”,“外衫比較長(zhǎng),袖子窄,領(lǐng)口也窄”。客家婦女這樣的打扮,彰顯客家人與本地人、福老人在習(xí)慣上的不同。⑥再有,該文認(rèn)為客家婦女是客家歌謠的創(chuàng)作者,⑦這也是畢安和黎力基沒(méi)發(fā)現(xiàn)的,不過(guò)未能給出佐證文本。又有,該文和黎力基一樣給出客家婦女是客家宗教的參與者之論述,即客家人仰仗客家婦女扮演的仙姑,因?yàn)樗齻兛梢詭?lái)靈界消息、叫回逃離的靈魂(例如生病小孩的靈魂)。⑧
第四位是艾希勒(R. Eichler,生卒年不詳)。他同樣是德意志人,先前是巴勉會(huì)成員,其后改隸倫敦會(huì),接替歐德理在博羅縣的傳教工作。⑨他于1883年發(fā)表《幾首客家歌謠》(Some Hakka-Songs)一文,登載在《中國(guó)評(píng)論》上。在文中艾希勒以漢英對(duì)照的形式寫(xiě)出客家歌謠,這和歐德理在《中國(guó)評(píng)論》上寫(xiě)出客家歌謠的形式相同。此文彌補(bǔ)了何必烈未給出客家婦女是客家歌謠的創(chuàng)作者之佐證文本的遺憾,公布了內(nèi)容為連情的歌謠,例如“三年唔嫁紅粉女,嫁郎一朝打身體,頭發(fā)松松毛又脫;啀郎追舊又貪新”,⑩也公布了內(nèi)容為送別的歌謠,例如“大船拉起三張巾里;小船架槳兩邊搖。船上水下番娘屋,囑咐啀連心莫憔”。①

如果將這四位傳教士的客家婦女研究成果合觀,可以發(fā)現(xiàn),他們的意圖與歐德理的旨趣相同,都注目于客家婦女與客家文化的關(guān)系;他們舉出的事例也多和歐德理提及的事例重合,像是戶外工作、不纏足、?一夫多妻的現(xiàn)象少見(jiàn)、殺女?huà)肫毡榇嬖凇⑼庖滦渥虞^窄、連情歌詞、送別歌詞、仙婆等等;他們得出的結(jié)論亦與歐德理的三點(diǎn)論斷一樣,即客家婦女是客家風(fēng)習(xí)特征的例證者、客家婦女是客家歌謠的創(chuàng)作者、客家婦女是客家宗教的參與者。考慮到他們都曾閱讀過(guò)歐德理的客家研究文章,我們有理由認(rèn)為是歐德理觸發(fā)了傳教士畢安、黎力基、何必烈、艾希勒的客家婦女研究,前者建構(gòu)的客家婦女形象成為后者的認(rèn)知模版,由此,若想明了傳教士客家婦女研究的學(xué)術(shù)脈絡(luò),就必須熟悉作為起點(diǎn)的歐德理的客家婦女研究。
在19 世紀(jì)60 年代,歐德理不是唯一一位客家婦女研究者,因?yàn)榭图抑R(shí)精英也討論過(guò)客家婦女。一位是林達(dá)泉(字海巖,1830—1878)。他在《客說(shuō)》一文中以“男女皆耕織”為據(jù)證明客家風(fēng)俗“勤”的一面。①另一位是黃遵憲(字公度,1848—1905)。他在《送女弟》這一組詩(shī)中一方面從“雞鳴起汲水,日落猶負(fù)薪”等客家婦女從事戶外工作的情形中得出“尤見(jiàn)”客家“風(fēng)俗純”的結(jié)論,另一方面也以“盛妝始脂粉,常飾惟綦巾”的客家婦女打扮讓讀者感知到客家習(xí)慣特點(diǎn)。②除了對(duì)客家婦女與客家風(fēng)習(xí)的關(guān)系著墨外,他也留心采集整理客家婦女創(chuàng)作的客家歌謠,并在多年后將它們書(shū)之紙上,其中既有內(nèi)容為連情的歌謠,例如“見(jiàn)郎消瘦可人憐,勸郎莫貪歡喜緣。花房蝴蝶抱花睡,可能安睡到明年”,③也有內(nèi)容為送別的歌謠,例如“送郎送到牛角山,隔山不見(jiàn)儂自還。今朝重到山頭望,牛角依然彎復(fù)彎”,④亦有內(nèi)容為求友的歌謠,例如“一家女兒做新娘,十家女兒看鏡光。聲聲銅鼓門(mén)前打,打到心中只說(shuō)郎”。⑤
將上述兩位客家知識(shí)精英的客家婦女研究成果合觀并與歐德理的客家婦女研究文章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后者要比前者更全面且豐富。就全面性來(lái)說(shuō),在歐德理的論述中,既論及客家知識(shí)精英提到的客家婦女與客家風(fēng)習(xí)、客家歌謠這兩種文化現(xiàn)象的關(guān)系,也述及客家知識(shí)精英未提到的客家婦女與客家宗教這種文化現(xiàn)象的關(guān)系。就豐富性而言,在雙方都有的客家婦女與客家風(fēng)習(xí)的關(guān)系之論述中,歐德理既舉出客家知識(shí)精英講到的戶外工作和打扮這兩個(gè)事例,還舉出客家知識(shí)精英未講到的對(duì)外友好、不纏足、一夫多妻的現(xiàn)象和販賣(mài)婦女的現(xiàn)象少見(jiàn)、殺女?huà)肫毡榇嬖诘仁吕S纱耍雽?duì)19 世紀(jì)中期客家婦女的形象有清晰的認(rèn)知,只知道同時(shí)期客家知識(shí)精英的客家婦女研究而不了解歐德理的客家婦女研究,我們將無(wú)法實(shí)現(xiàn)此目標(biāo)。
在與他人成果的比較中成一家之言是學(xué)術(shù)進(jìn)步的通則,故而輕視傳教士歐德理的客家婦女研究這一事實(shí)上存在的學(xué)術(shù)史參考系,當(dāng)今客家婦女研究者便失去一種可供比較以彰顯創(chuàng)新的資源,這不能不令人惋惜。希望借由本文的宣介,當(dāng)今客家婦女研究者能重視傳教士歐德理的客家婦女研究,通過(guò)與之比較,進(jìn)而找到自己的客家婦女研究之合適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