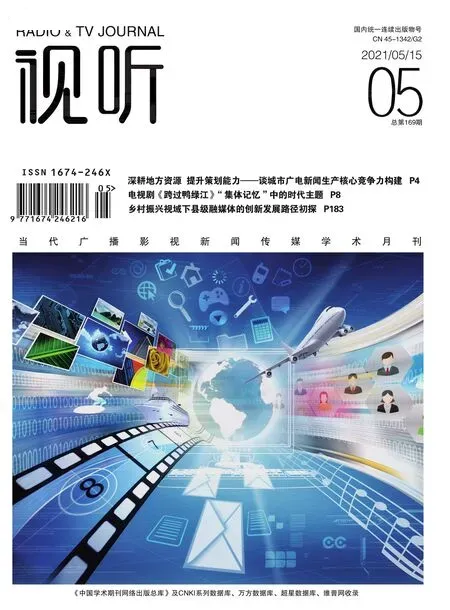互動儀式鏈視角下網絡綜藝的群體互動機制探究——以《說唱新世代》為例
□ 楊榮菲
CNNIC第47次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9.89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0.4%。同時,我國網絡視頻用戶規模達9.27億,占網民整體的93.7%。視頻化敘事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呈現方式。伴隨著受眾需求的與日俱增以及技術和資本的支持,網絡綜藝蓬勃發展。據微熱點大數據研究院統計,2020年度上線的網絡綜藝節目高達128檔,層出不窮的網絡綜藝市場競爭日益激烈。
一檔網絡綜藝節目想要出圈,需要多重要素的加持。優質的內容輸出、精準的用戶定位、平臺資源依托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互聯網時代,用戶面臨更為豐富多樣的內容選擇,僅僅將用戶吸引過來遠遠不夠,還需秉持互動意識增強用戶黏性。因此,著手打造完整的互動模式以提高用戶留存度,成為網絡綜藝的制勝關鍵。
2020年8月22日,由B站出品的說唱型綜藝《說唱新世代》上線。該節目立足于說唱文化,以綜藝形式與其他主流視頻平臺騰訊視頻、愛奇藝、優酷視頻等同臺較量。截至本文成稿時,節目播放量已達4.4億,豆瓣評分也高達9.1分。該節目聚集了主理人導師、人氣選手、說唱文化等吸粉利器。因此,對于探究擁有不同生活背景的用戶群體如何建構互動儀式并產生互動效果具有重要意義。
一、理論框架:互動儀式鏈
20世紀下半葉,美國社會學家柯林斯提出了互動儀式鏈理論。該理論是柯林斯在總結涂爾干關于儀式的研究,并在借用戈夫曼“互動儀式”概念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互動儀式鏈的基礎和核心是互動儀式。所謂互動儀式,指的是小范圍內即時即地發生的面對面的人際交流,它們是生活中人與人之間最凡常不過的儀式性交往。柯林斯詳解了發生于特定情境下的人際互動,是如何在參與者的“情感能量”這一根本引擎和變壓器的驅動下啟動、推進并結束的。
如圖1,在柯林斯看來,互動儀式的構成要件有四:1.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身體共同在場,即實現“群體的聚集”;2.群體集合的實現使得對局外人設置邊界得以實現;3.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活動或者對象身上;4.獲得共同的情感或者體驗。

圖1 互動儀式鏈圖式
同時,柯林斯的研究也涉及到了互動儀式所帶來的結果,即隨著互動儀式的各個組成要素深度融合后,參與者也會獲得相應的情感體驗。1.群體團結,即個體對自身作為群體成員的身份認同感。2.個體的“情感能量”,一個人會從群體互動過程中得到充分的情感能量。這也是整個互動儀式鏈得以持續存在的關鍵所在。3.形成共同的群體符號,柯林斯將其解釋為標志或其他象征物。個體的情感能量也會附著于存儲象征符號的承載物上。4.道德標準,即一種存在于個體心中維護群體正義感的感受。
二、《說唱新世代》中互動儀式的構成要素
(一)虛擬在場:互聯網奠定互動基礎
作為互動儀式啟動的前提性要件,身體的在場是實現互動的基礎。柯林斯認為,個體的親身在場可以實現情感能量的及時反饋,充分的身體接觸能夠為參與者提供共享關注與情感。但是隨著互聯網技術發展,網絡的低延時性可以最大程度提升信息傳播速度,人們通過網絡即時交流能夠實現非物理空間的身體在場,并因此進行流暢、有效的實時互動。
對于網絡綜藝節目來說,實現虛擬的身體在場一般依托于彈幕表達機制。其他說唱類網絡綜藝節目,例如《中國新說唱》《說唱聽我的》等依附于愛奇藝、芒果TV等視頻播放平臺播出。雖也有彈幕表達機制可以實現實時交流互動,但是其彈幕發送無門檻限制,內容質量相對較低。而《說唱新世代》的制作平臺B站作為國內最大的彈幕類視頻網站,擁有成熟且嚴格的準入機制,具有得天獨厚的互動屬性和社交屬性。用戶需學習彈幕禮儀,通過答題之后才可發送彈幕。較高水準的彈幕表達機制使得陪伴式在場得以實現,受眾突破了空間限制在互聯網場域得以聚集。
通過屏幕,受眾不僅可以獲得節目的實時動態,并通過彈幕與其他觀眾實現實時互動。尤其在PC端可以看到同時在看的用戶數量,網友也會因在彈幕中留言獲得一種共同在場的陪伴感。彈幕的獨特設置使得網友可以共同討論節目并表達自己的觀點,同時其他人也可以隨時回復,例如彈幕“前面的等我,我也這么認為”“+1”等。這便突破了時空限制,實現了以往語境下的身體在場式互動。這種新型的虛擬在場式聚集,也能夠促進受眾在互動中產生情感共鳴。
(二)對局外人設限:粉絲社群的準入機制
互動儀式鏈得以形成的另一重要前提便是對局外人設定了界限。這使得參與者知道誰在參加,而誰被排除在外。《說唱新世代》節目精準定位其受眾大多屬于“Z世代”,憑借獨特的青年文化表達特質給局外人設定了明顯邊界。“習慣了”“貸人”“沙一汀痛苦面具”“文化綠洲VS文化沙漠”“真漂亮”“散財童子”等簡單明了的特色表達方式給非節目觀眾理解其真正內涵帶來了一定困難,而節目粉絲卻通過這些特定的文字符號得以聚集。
對局外人設限還體現在節目粉絲社群的準入機制上,不論是熱門選手的官方粉絲群還是豆瓣討論小組都設置了嚴格的問題審核流程。“一句話證明你看過《說唱新世代》”,審核者通過內容鑒別從而獲知申請加入者的身份。這種簡單粗暴的審核方式對局外人設定了限制,同時也能夠維護粉絲社群的秩序,從而進一步強化對于選手及節目的認同感。
除此之外,從節目本身觸及的說唱文化本身著手,出身于地下的說唱文化一直以來并不屬于主流文化的一種。盡管2017年《中國有嘻哈》的火爆一定程度上使其“出圈”,但其鮮明的音樂特質也在一定程度上對不喜歡此類型音樂的受眾劃定了門檻。
(三)共同關注的焦點:促成受眾關系升級
作為互動儀式的過程性要件,共同關注的焦點是互動儀式鏈的重要一環。只有受眾擁有共同關注焦點才能夠對此進行交流和討論,帶來更深層次的互動行為。與同時期的其他兩檔說唱類綜藝節目走專業化路線或流量路線不同,《說唱新世代》另辟蹊徑,選擇打造屬于年輕一代自由表達的說唱節目,打出“萬物皆可說唱”的口號(slogan)。節目意見領袖既有作為流量擔當的主理人黃子韜,也有專業導師更高兄弟、MC熱狗。同時還有李宇春、騰格爾及多位UP主等跨界觀察官。這種不同圈層的搭配碰撞出了獨特的火花,吸引了更為多元化的受眾。
《說唱新世代》通過“生存+說唱”的新形式實現了競演綜藝的創新,每期選手的作品更是聚焦于社會熱點,為不同群體發聲。如圣代的《書院來信》聚焦于豫章書院事件;C-LOW的《一塊膠布》探討文化自由;doggie的《real life》為高考被頂替者發聲,并反映校園暴力問題。優質的內容形塑受眾共同關注的焦點,在網絡中引發激烈討論并登上熱搜榜單,“#說唱新世代總決賽#”熱搜閱讀量高達6.6億,討論量達56.9萬。基于對共同關注內容的熱愛,粉絲群體更是建立了相應的“超話社區”,并為其制作表情包、視頻混剪和周邊設計等。這極大地增強了不同個體的體驗感并建立起鮮明的關注焦點和情感紐帶。
(四)情感共享:體驗分享強化受眾互動
情感共享作為互動儀式鏈的最后一環,也是互動儀式得以完整呈現的重要條件。人們關于共同關注的焦點進行交流互動,能夠催生情感共鳴以激發更強烈的表達欲,從而與群體其他成員進行情感共享。情感共享可以使群體成員的關系更加牢固。在網絡綜藝節目《說唱新時代》的觀看過程中,反饋機制能夠方便受眾及時表達自己的情感傾向。大家可以通過“一鍵三連”,投幣、點贊、分享、收藏等方式與列表成員共享這種情感體驗。
除此之外,基于節目本身進行二次剪輯創作的內容也是觀眾共享情感體驗的方式。在平臺搜索《說唱新世代》的相關內容,用戶自制視頻播放量高達百萬的不在少數。粉絲群體基于原文本進行再解讀的行為賦予了節目新的內涵與意義,其他觀看者也通過觀看評論獲得新的情感共享體驗。同時,在節目結束后也有很多UP主會將自己觀看時候的狀態制作成新的“reaction”視頻。這種共享自己觀看狀態與情感傾向的內容文本給其他觀眾帶來了新的體驗感,并在其中尋求認同感,形成新的情感集聚。
三、《說唱新世代》中的互動效果
(一)儀式互動積聚情感能量
在柯林斯看來,個人會在互動儀式中獲得情感能量,即個人通過一次次短暫的互動行為不斷積累情感體驗,最終轉化為長期的情感能量。《說唱新世代》的節目導演嚴敏一直秉持“說唱的本質是為社會發聲”的理念。出于對優質內容的呼喚,節目組對于內容體現了更大的包容性和開放性,歌曲表達的深度和廣度更為深刻。節目中涌現了一大批關心社會事件的優質作品,并引發網民“一個敢說,一個敢播”的熱議。熱門選手“圣代八小時”極限創作《書院來信》,聚焦豫章書院事件,以藏頭詩的形式為學生們發聲,使得這一事件再次被提及并引發熱議,網民的社會責任感和正義感呼之欲出。
說唱本身來源于美國黑人街頭文化,許多原生內容并不具有普適性,但是“萬物皆可說唱”打破了原有的框架,有利于突破社會上的固有認知,促進小眾亞文化的“出圈”。節目中多種新生力量的涌入也使人們看到了年輕人通過說唱關注社會議題,表達個人觀點的意愿。這也有助于社會正向情感能量的聚集,增強青年的社會責任感。
(二)共同關注形塑群體符號
柯林斯認為具有共同關注焦點的人們能夠延伸具有團結感的共同符號。一開始人們只是基于“身體在場”得以共同關注某一個事件焦點,并因此產生某種連帶的群體情感,而經過長期的積累和轉化,短期的情感能量能夠形成群體符號,成為群體的標志。對于《說唱新世代》來說,并不缺少共同關注的焦點,不論是集中于節目內容本身抑或是集中于節目嘉賓,討論熱度不減。隨著互動儀式的不斷增強,觀眾從每期節目出發玩梗,并不斷衍生出相關表情包、代名詞、漫畫等。例如大家將自己稱作“貸絲”(意指《說唱新世代》的粉絲),并制作相關表情包。由于節目預算有限,攝制現場也是半露天場所,為防止擾民一般只能白天錄制,觀眾在互動中戲謔稱此為“精準扶貧”。隨著互動儀式加深,“小破站”等群體符號更加深入人心。
群體符號實際上是群體成員在互動儀式中的情感投射,一系列互動行為所反映的情感會附著于象征符號之上。節目觀眾作為B站用戶具有年輕化的特征,戲謔自由的解讀方式體現在這種個性化參與與個性化表達上。以表情包為例,雖然節目已結束,但是表情包作為一種群體符號得以延續,在超話社區及各大熱搜評論區,依舊能看到粉絲群體刷的表情包留存,同時不斷有人跟帖表示認同。
(三)情感共享強化身份認同
節目播出初期,大部分觀眾的到來大都是出于對說唱文化的熱愛,抑或是出于對節目嘉賓及選手的認同。通過觀看節目及與其他成員進行情感互動能在很大程度上強化這種自我認知。大部分觀眾并不熟悉節目中選手背后的各大廠牌,而說唱愛好者憑借自身優勢可以對其進行科普,彈幕中不乏各類科普性質的內容。此類觀眾通過共享自己愛好且擅長的領域可以獲得他人的認同感,并為自己贏得社交貨幣。這種基于說唱文化愛好者的標簽式互動也能夠滿足自身對于理想身份的認同,進而對群體產生歸屬感和強烈的認同感,保證了這種互動儀式的順利進行及延續。
除此之外,《說唱新世代》還通過打通線上線下儀式鏈來強化觀眾的身份認同。決賽后節目組簽約熱門選手成立W8VES廠牌并進行線下活動巡演,熱度持續不減。互動儀式由一開始借助互聯網技術實現新的“身體在場”到線下活動時的真實在場,將情感共享發揮到最大效用,強化了參與者對其身份的認同感。
四、結語
一檔網絡綜藝節目的成功出圈,自然少不了優質的內容供給,不過在受眾話語權不斷提升的當下,打造完整的互動儀式鏈以增加用戶黏性也是關鍵。《說唱新世代》通過新的“身體在場”與共同聚焦關注點等構筑互動儀式鏈,并以此打造新的群體符號、積聚情感能量、強化身份認同,取得了流量與口碑的雙重豐收。而未來音樂類網絡綜藝節目也可以從多方面著手,例如,合理設置關注焦點、打通線上線下輔助儀式以深化群體認同、打造群體符號以凝聚情感能量等,以期利用好互動儀式為其發展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