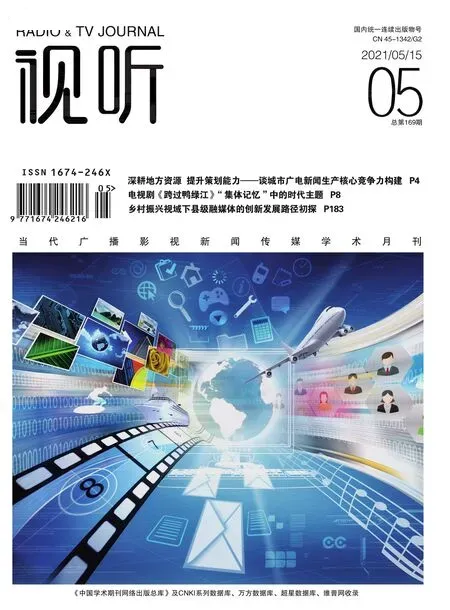看與被看:“看中國·外國青年影像計劃”的策略性敘事
□ 紀卓言
2020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亞洲文明大會上指出:“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我們要加強世界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鑒,夯實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作為一項中國文化體驗項目,“看中國·外國青年影像計劃”的影像敘事,將外國青年感受到的中國文化傳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有效的文化溝通。我們知道,敘事的本質是一種“戰略性文本”,即“通過實施這種戰略,政治行動者試圖為過去、現在和未來賦予確定的意義,以實現政治目標”。“看中國·外國青年影像計劃”通過“對事實要素的策略性模塑過程,形成特定的敘事方案,從而達到引導受眾理解的目的”。這種策略性敘事,主要表現在創作者的組織傳播、內容生產方式和傳播效果這三個方面。
一、創作者:系統引導下的組織傳播
“看中國·外國青年影像計劃”(下文簡稱“看中國”計劃)由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AICCC)和會林文化基金聯合主辦。十年來,該計劃形成了以民間公益藝術基金組織為資方、以專業學術型機構為承辦者的格局。
(一)創作者文化背景的多樣性
“看中國”計劃以外國青年為主要創作者。以2018和2019年“金目獎”獲獎作品為例,如圖1所示,我們可以看出,創作者國籍上具有多樣性,涵蓋亞洲、北美、北歐、南非等世界各國區域。一方面,中國日新月異的變化帶給創作者嶄新的體驗;另一方面,創作者將自己對中國形象的認知傳遞給中國觀眾。這種互動傳播,打破了人們對于傳統紀錄片文本的認知,為文化價值提供了重新闡釋的機會。

圖1
(二)創作者的視角
“看中國”計劃以弘揚傳統中國文化為出發點,將傳統的中國元素以新的視角進行敘述,有助于在國內外更好地傳播中國文化。紀錄片《The Living Past》(《活著的過去》)主要講述了重慶市自然歷史博物館恐龍化石修復師朱松林的故事。創作者沒有停留在對朱松林的刻畫,而是將敘事重點放置在修復恐龍化石這一事件上。于是,紀錄片的內核抽象到“傳承”這一概念,恐龍化石修復師被塑造為文化堅守者的形象。
此外,創作者大量使用了窺視鏡頭的拍攝方式。紀錄片《Early Summer》(《早夏》)拍攝的是小女孩被送到農村的爺爺奶奶家過暑假的故事。創作者將攝像機架在一旁,利用固定鏡頭進行真實生活的記錄,不做任何的主觀干預,也沒有對事情的評判。觀眾隨鏡頭一起,窺視他們一家人的生活。窺視鏡頭將想象的空間給予觀眾,滿足觀眾對于一個場景或事件的想象。
(三)傳授者的雙向互動
“看中國”計劃系列紀錄片在互聯網平臺和國內外高校平臺進行了傳播。各高校資源上的優勢互補,能夠為計劃的持續進行提供良好的信息資源。“看中國”計劃的價值,一方面是外國青年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接受,另一方面是中國青年對外國青年觀察視角的研究。這種雙向互動形成了一種“看”與“被看”的格局。這種主導創作的組織方式,通過多重視角審視文本,構造了更多樣、更客觀的形象認知,在東方與西方、國內與國際、官方與民間構成了信源的交互式平衡。
二、內容呈現:超文本敘事方式與多維化內容生產
“看中國·外國青年影像計劃”與傳統紀錄片的基本模式有著較大的差異性。模塊化和超鏈接敘事的形式下,呈現了多維化的內容。
(一)超文本敘事方式
傳統的紀錄片文本敘事多運用的是閉路結構,也就是單向敘事,講求結構的完整性,注重開頭結尾以及內部沖突。“看中國·外國青年影像計劃”則運用了更加開放和自由的敘事模式。該計劃中,每一部紀錄片被分成了10分鐘左右的小模塊,體現出不同創作者所了解的中國文化。在2018年的紀錄片《Blue Sheep》(《巖之精靈》)中,創作者通過對于喜愛巖羊的人們進行采訪,呼吁更多人保護巖羊。與此不同,紀錄片《Little Princess》(《小公主》)則是拍攝動物園中的雪豹生活。兩個紀錄片文本各成一個獨立的模塊,看似完全沒有關系的選題蘊含著相同的人文內涵:對瀕危動物的保護。
因此,“看中國”計劃的所有作品形成了一種超文本形式。該計劃中的紀錄片包含人文類、自然科學類、故事類等多種類型。在互聯網平臺,觀眾可以任意選擇該計劃的紀錄片進行觀看。盡管每個紀錄片的內容都相對獨立,但其意義依舊是存在于該計劃的網狀敘事之中。
(二)多維化的內容生產
“看中國”計劃的策略敘事包括“看”和“中國”兩個方面。
就“看”的方式而言,“看中國”系列紀錄片充分利用了多視角的拍攝手法。紀錄片《The Seal》(《封》)中,表現城市與農村的區別時,利用了太極師傅、攀巖者、解說者三個不同視角進行文本內容的創作。這種多角度敘事的手法給觀眾視覺上產生完全不同的體驗,使單個紀錄片的文本內容更加全面而具體。以人為主要敘事中心的紀錄片則通過自我講述的“個人化”敘事方式,將人的成長與外部世界相呼應。紀錄片《The Life of a Seed》(《一顆種子的故事》)以種子做隱喻,表現了一位植物愛好者成為植物專家的故事。《The Farmer》(《幸福田園》)則通過一個農民的自我敘述,講述了典型的傳統農民生活。在這些紀錄片中,主人公是故事的講述者,也是事件的親歷者,通過主人公的自我闡述,表達出對夢想、希望的追求。《The Farmer》(《幸福田園》)中,主人公表達了對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的一種追尋以及渴望得到繼承的愿望。
如果說“看”是體現在創作者對文本內容的選擇,而“中國”則是中國元素的具體呈現。“看中國”計劃中的紀錄片摒棄了對于如長城、故宮這種最能體現中國形象的元素,反而將鏡頭對準了小眾題材。影片《Blessed Earth》(《濟世》)將鏡頭對準了藏醫,以科巴和彭措多杰這對父子為例,展示他們為患者看病的日常生活以及制藥銷售過程。紀錄片表現了父子二人對藏醫事業的堅持與傳承,同時重點挖掘草藥對于治療的獨特價值。《Hanging High》(《壁上人》)則以攀巖者黃小寶和羅登平為拍攝對象,表現了貴州深山之中攀巖者的生活。這些小眾題材紀錄片,從另一個視角體現了傳統中國元素具有的內涵。紀錄片《Lover for Sight》(《依曦》)主要拍攝了茶葉的制作過程。與傳統展示茶文化的紀錄片不同,該片沒有分步驟講解茶葉制作過程,而是采用了“slience(寂靜)”作為整體的主題基調。片中沒有一句臺詞與解說詞,只有最原始的背景音。作品將茶與“靜”結合起來,將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融合在一起。
三、傳播效果:意識形態的再生產
“看中國·外國青年影像計劃”的觀看視角與內容文本,體現了對于中國文化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價值觀的理解。
(一)中國文化符號的所指意義
“看中國”計劃中的“中國”,并不局限于傳統的國家命名含義之上。中國民俗、中國醫學技術、中國稀有保護動物……這些與中國相關的內容都被劃為“中國”這一符號的范圍之內。中國文化的符號意義滲透于各個方面,引導觀眾理解中國文化。以《Three Flavours of Chongqing》(《重慶三味》)為例,紀錄片一開始,運用了大景別的鏡頭展示重慶市的整體景觀。而在展示重慶火鍋時,則是利用了小景別的拍攝方式,突出重慶火鍋的局部細節。大景別使鏡頭以“鳥瞰”的方式觀察重慶的城市景觀。而小景別的運用則能夠凸顯出細節的局部信息,能夠拉近人與事物的距離。吃火鍋的團圓氛圍,不但體現了人情味,還有秩序與傳承、包容與圓融。在反差鏡頭下,觀眾不但了解了重慶市與火鍋的關系,也將火鍋與中國文化有機地聯系在一起。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際社會日益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面對世界經濟的復雜形勢和全球性問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世界體系是一個具有整體意義的變量體系,中國在世界的地位也發生著變化。“西方中心論”已經不符合當下世界體系的要求。“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一種話語力量,倡導用平等的話語建立命運共同體之間的和諧共處與共通交流。外國青年對于中國的觀察視角、中國青年對外國青年的理解角度,建立起了一種百花園式的話語生產場域。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下,更需要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將中國故事提升為人類文明的共同經驗。
四、結語
“看中國·外國青年影像計劃”為觀眾打開了新的視角,也為傳播學中的策略性敘事理論提供了新的構建方式。該計劃既對文本形式進行了再構建,又將敘事手段進行了更新,從而為策略性敘事的本土傳播帶來了新的視點。當然,由于不同的生活環境與思維方式,創作者在對中國元素的理解上會與中國觀眾產生偏差,而這種偏差恰恰是值得我們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