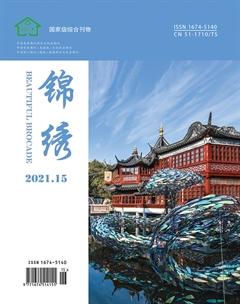中國當代首飾設計中“天人合一”傳統美學的體現
馮雪
摘要:當代首飾雖然從誕生到現在的發展時間較為短暫,但當代首飾已經跳脫出了傳統首飾以服飾、身體裝飾或身體裝扮的邊界,進而向探測首飾的根本性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索與研究,當當代首飾這一領域隨著當代藝術的洪流進入中國后,它不可避免的與中國本土性的審美美學發生沖擊與交融,從而開拓出了相當廣闊且豐厚的靈感土壤,創作出帶有強烈的中國哲學美學色彩的作品,大部分作品具有表達“天人合一”這一美學觀點的共性,逐步探索出了一條在全球化大環境下獨特的藝術之路。
關鍵詞:中國當代首飾;“天人合一”傳統美學;當代首飾設計
一、中國當代首飾現狀分析
當代首飾的歷史到目前為止十分短暫,但這不影響他從誕生以來便帶有極強大的生命力與影響力,并在20世紀90年代末漸漸走入中國,耕植在了中國特有的藝術土壤中,吸取了博物廣大的民族藝術養分,強調了多層面的思考以及重視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與對話式的生動性,同時受后現代主義藝術風格的影響,權威主體的消失與反對同一性的藝術理念使得當代首飾設計出現多元化、差異性特征,手工制作變成了一個多維的、和歷史相關的、具有復雜定義的行為,發展至今日已然呈現出多種多樣的面貌出來,他早已不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征,已然搖身一變成為了對于人、世界、文化更為人文和本質的探索,一部分中國當代首飾藝術家們通過他們的創新實踐來挑戰陳詞濫調的表現主題,運用智慧的方式與方法吸引觀眾來重新關注傳統理念,給予了中國當代首飾新的發展契機。
二、“天人合一”傳統美學
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中國美學無論如何都繞不開的一個點,諸學各家雖都提出過自己的觀點并且不盡相同,但幾乎都普遍的肯定人與自然的統一性關系,即天人一致或天人合一,李澤厚在《中國美學史(第一卷)》中認為,天人合一是中國哲學的一個基本問題,并成為其的根本思想,這與中華民族在長期的艱苦斗爭中對自然的改造征服分不開,也與原始公社氏族殘余的長期存在,以及中華民族在物質生產上長期以農業為主體分不開。馬克思在談到包括亞細亞所有制在內的原始公社的特點時曾指出:“個人把勞動的客觀條件簡單地看作是自己的東西,看作是自己的主體得到自我實現的無機自然。勞動的主要客觀條件并不是勞動的產物,而是自然。”因此由于上述原因,我們得出,中國古代的生產是如何調節自然來利用自然并達到人的目的的活動。而根據馬克思提出的物質生產對人本質力量的對象化的具有決定力量,所以,在中國古代人與自然是密不可分的統一在一起的,并且人不完全受受制于天,是不完全依賴于天的,人的力量與價值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三、“天人合一”中國傳統美學在當代首飾中的運用
中國首飾設計師們具有與生俱來的中國工藝美學和造物理念,《考工記》中寫道:“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 以為良。”其中體現了特殊“適用”的中國造物觀,以因地制宜為美,充分考慮功能與人的關系為工藝制作原則,從而制作出了相當富有中國美學情懷的首飾作品,他們帶著這些獨特的首飾設計在當代首飾界中開拓出了屬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3.1、“以小見大”美學觀的體現
中國哲學與藝術理論中存在著一個十分重要的藝術理念,那就是以小見大,我國先秦時期以大為美的思想占據主要位置,《詩經》贊揚“碩人”之美,孟子的“充實以為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公羊傳》的“美,大之之辭也”,莊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由于歷史社會原因,直至中唐后,小的趣味更加明顯,引領社會的士大夫階層人文意識開始覺醒,往返于山水之間,以人為主體的觀察一花一木,觀摩感受山水、世界、宇宙之大,王勃登滕王閣,有“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詩人借登高的感受,打破了兩個世界的界限,由小的世界越入大的宇宙,這也影響了人們對于小園、盆栽、篆刻、精美工藝品的喜愛,中國傳統美學中以小見大的哲學觀的轉變,一花一葉中都蘊涵了整個世界的秘密,它影響深遠,直至近現代也在多個藝術門類中產生著重要的影響。
中國當代首飾藝術家的寧曉莉以陶瓷為創作材料,制作了大量以“空谷幽蘭”為靈感的首飾作品,她認為“蘭生幽谷中,倒影還自照。無人作妍媛,春風發微笑。”這與八大山人的友人為他而畫的《個山小像》中八大山人對其友人的贊語:“個,個,無多,獨大,美事拋,名理唾……大莫載兮小莫破。”有異曲同工之妙,我是山林天地中的一個點,雖然是一點,但我卻是獨立的,是大全的圓滿。一朵小花,一枝幽蘭,一只寒蛾,都是一“個”、一“點”,縱使無人欣賞無人關照,它依然是一個充滿圓足的生命個體。以小見大的哲學理念影響著中國首飾藝術的內容,但同時,作為首飾這樣一個體量的存在,本就是屬于“小物”的范疇,現當代人們在回歸本源美學理論的同時,也在不自覺中受以小見大這樣哲學美學觀的影響,重新重視并定義了現代首飾這樣一種表達方式,茫然無覺者無小,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國,在小小的一枚首飾中探索一個更為廣博的世界,發掘探索世界與生命的深刻意義,正是現當代中國首飾藝術家的共同藝術目標。
3.2、“大巧若拙”美學觀的體現
“大巧若拙”是由老子提出的,老子在思考天工和人為關系中,提出最高的巧,就是不巧,不巧之巧,可以稱之為天巧,韓愈《贈東野》詩云:“文字覷天巧。”此中的天巧就是老子所說的大巧,是無巧之巧,是自然而然的,非人為的,從人的技術型角度來看,他是笨拙的,沒有技術含量可言的,但從天的角度來看,它蘊含著不可逾越的美感,即道之巧,有純全之美,樸素而不追求浮華,《磨玉》一作品是滕菲對廢料可能性的嘗試,他們未經過多的雕琢,渾然天成,在保有玉石廢料的基礎上稍加琢磨,直至廢料整體形狀完善和諧,后加入編號進行存檔后展出。這些廢料是一種無為的無用狀態,而她正是對于這些無用之物,以一種保留其本身拙劣的方式進行塑造,作品最終呈現出一塊塊碎石的樣貌,這些碎石在有用與無用來回搖擺的狀態下尋找到個體的獨特性與獨立性,達到一種對自我的完滿與美好,這便是道家所崇尚的終極境界,藝術家所強調的并不是對于外在形態追求天然這樣的一種顯像狀態的體現,而是以這樣的思想成為在創作這件作品時的一種指導方向,秉承著這樣一種創作思維,進行對于“玉”這樣一種已經形成完整程式化、并且有著強大不可撼動力這樣的創作模式的打破,也正是我們先當代首飾藝術家們面臨的重要藝術問題,而滕菲的這樣一件作品給予了我新的思考角度,在如何進行傳承與創新之間,留下了一種尺度的示范與界定。
四、結語
鐘嶸《詩品序》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行諸舞詠。”“若乃春風春鳥, 秋月秋蟬,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人作為感受萬事萬物的主體,在感受萬物后實現內心的觸動,創作的作品也體現著我與物的統一,即物我交融,在作品中的表現便是“天人合一”。這種天人合一的創作思維,體現了中國美學的獨特特征,錢穆曾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對于世界最大的貢獻”,“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歸宿處”,屬于我們本土的當代首飾的創作更是體現了這一特征,萬物道通為一,首飾已經并非單純的作為裝飾自身的漂亮意義而存在,而是賦予了每件首飾于創作者來說一定的意義,以及心靈的體驗,是佩戴者與首飾創作者的雙向表達的一種媒介,在當下這種帶有極強的不確定性的生存空間中,傳遞著我們需要的更多的精神慰藉,她同時也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的載體而存在,中國首
[4]李薇.我國網絡文學IP運營及轉化模式探析[J].出版廣角,2017(18):44-46.飾設計師們針對當下的設計理念而作出相應的介入與結合,尋求一種不同文化地域相互影響與共同發展的相互滲透的形式特征,在向世界傳遞中國美學的精神與魅力中,擔當著自成一格、別出一派的重要角色。
參考文獻
[1]朱良志.《中國美學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年4月
[2]李澤厚、劉綱紀.《中國美學史·第一卷》.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1990年1月3次印刷
[3]杭間. 《中國工藝美學史》. 人民美術出版社.2018年12月第3版第1次印刷
[4]朱良志《中國藝術論十講·曲院風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
[5]劉驍、李普曼.《當代首飾設計:靈感與表達的奇思妙想》.中國青年出版社.2014年8月第一次印刷
[6]滕菲.《首飾:一種精神的載體美術研究》. 2008年01期 .第48-50頁
[7]朱志榮《中國美學的“天人合一”觀》.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5年02期 第17-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