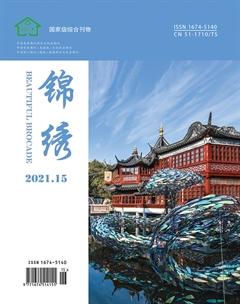未成年人網絡直播打賞行為的法律分析

摘要:近年來,隨著網絡直播行業的發展興起,一些社會問題也隨之而產生,特別是未成年人高額打賞網絡主播而引發的經濟糾紛問題頻繁發生,以成為一大社會問題。本文通過對現有文獻的梳理,總結歸納目前存在的關于打賞行為性質的三種主要學說,通過對文獻的綜述,發現在救濟時證明未成年人是打賞主體、追回打賞金額困難的問題。未來預防未成年人打賞還需要完善相關法律制度以及需要社會各方共同努力。
關鍵詞:未成年人;網絡打賞;性質;民事行為能力
截止2021年,筆者以“未成年人直播打賞”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中文期刊進行檢索,共得到文獻302篇。根據下表圖一所知,在2016年之前這個問題基本無人問津,但在2016年之后我國對未成年人直播打賞研究的數量急劇增加。為什么論文數量急劇增加,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第一,互聯網以及科學技術的進步使得普通大眾可隨時借用手機觀看直播。第二,商業利益的趨勢導致多數人涌入直播領域。第三,未成年人直播打賞糾紛頻繁被媒體報道,引發社會關注。
筆者1通過文獻分析法,對近年來在關于未成年人直播打賞問題的文章梳理,總結當前關于打賞性質的三種最具有爭議的觀點、目前對限制行為能力人打賞行為效力如何認定以及是否可以追回打賞金等問題。通過歸納文獻,發現在具體應用中還存在的問題及其提出一些建議。
一、網絡直播打賞的法律性質界定
學術界對于網絡直播的法律性質的理解與認定各執一詞,至今尚未達成統一共識,對于網絡打賞行為的法律性質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主要有服務合同說、贈與合同說、區別說。下文中將根據不同學者的觀點分別加以闡述對網絡直播的性質認定問題。
(一)贈與合同說
根據我國《合同法》的規定,贈與是指贈與人將自己的財產無償給予受贈人,受贈人表示接受贈與的行為。周熙瑩、譚子恒等學者認為,網絡打賞的隨機性以及打賞行為的非強制性決定其對網絡主播的打賞并不是一種對待給付性的義務。打賞行為是出于對網絡主播情感的寄托和愛的表達,具有非對價性的將其財產所有權轉移于網絡主播的特征[3]。程嘯、樊競合也對打賞行為構成贈與合同是贊同的,觀眾的打賞與網絡主播的表演解說并不具有服務合同意思的約束。觀眾對網絡主播的打賞是為了滿足其情感的需求,而不是去創造經濟價值,雙發承擔的義務不具有對價性。贈與合同享有撤銷權,成立贈與合同為撤銷權的行使留下了余地[2]。
(二)服務合同說
我國現行的《合同法》并未有關于服務合同的具體條文規定,但在學界以及具體實務中都有其存在。所謂服務合同,全部或者部分以勞務為債務內容的合同。潘紅艷教授認為網絡直播平臺是互聯網商業化的產物,根據在知識產權中表演行為的有償性,觀眾對網絡主播所提供的表演解說而進行的打賞不是贈與,而是一種新型服務合同。另外,其他持“服務合同”說的學者也同樣認為,以勞務為債務內容去定義或理解服務合同,那么觀眾的網絡直播打賞行為就是對網絡主播所提供的勞務服務的一種消費購買,網絡主播是勞務服務的提供者,相應的實施打賞的觀眾就屬于接受勞務服務者,由此在觀眾與網絡主播之間就形成了一個債權債務關系[1]。
(三)區別說
打賞行為的性質究竟是何種合同,其界定相對而言較為模糊,還需根據具體的實踐以及其他情況來加以分析。持區別說的學者認為,網絡直播打賞不能簡單的劃分為贈與合同或者是服務合同,應根據觀眾在打賞時的主觀心理態度等具體的實際情況加以分析。如果觀眾是發至內心的想要打賞,不要求任何的回報,那么打賞行為就是贈與。如果觀眾的打賞行為是為了通過消費獲得其他的一些服務,如尋求安慰,獲得與主播聊天或者線下見面的機會,則打賞為服務合同。但在具體的實踐中對于觀眾到底是出于怎樣的心理態度而打賞的認定是較為困難的,觀眾可能出于一個因素,也可能出于多個因素的相互作用。
二、未成年人打賞行為的法律效力認定
(一)行為有效
直播打賞不同于傳統的線下交易活動,可以通過面對面交流獲悉交易對象是否具有交易能力。劉韻認為,如果直接全盤否認未成年打賞行為的效力是有違民法中的公平原則,在平臺或者是網絡主播有理由相信對方在實施打賞行為時具有行為能力,那么法律就應對打賞的效力予以肯定。其他一些學者認為,在直播打賞交易的過程中,當事人是否具有締約能力是難以考察的,而且考察成本過高,因此,不應當將不具備相應的行為能力來否認未成年人實施打賞行為的效力,
(二)行為效力待定
根據我國《民法總則》十八條、十九條的規定,不滿八周歲的未成年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實施民事法律行為。八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民事法律行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經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認,但是可以獨立實施純獲利益的民事法律行為或者與其年齡、智力相適應的民事法律行為。以此可以得知,不滿八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只能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實施,其所實施的打賞行為無論數額多少均是是無效行為,在此沒有爭議。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八周歲以上的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所實施的打賞行為的效力。因打賞引發的糾紛多是未成年人實施的與其年齡、智力不相適應的高額打賞行為,未成年人動輒在直播中打賞主播幾千甚至幾萬、幾十萬元,明顯與其正常的年齡、智力、認知狀況不相符合。并且最高人民法院新出臺的《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二)》,對這些糾紛也進行了明確的法律解釋。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包括八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在沒有經過其法定代理人同意的情況下,參與了網絡付費游戲或者是網絡直播平臺“打賞”等方式支出與其年齡、智力不相適應的款項,其監護人請求網絡服務提供者返還該款項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三)其他觀點
也有少部分學者認為,對于在網絡直播過程中未成年人是否具有行為能力,不是法律解決的問題,而是技術需要解決的問題,網上交易的局限性只是導致了在識別對方當事人身份時具有困難,并且隨著技術的發展變革,在以后的將來,這是一個可以解決的問題。【15】
三、未成年人打賞救濟時的問題
雖然國內眾多的學者對未成年打賞的性質以及法律效力問題都進行了探討,使得讀者對這些問題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但在具體應用法律來解決未成年人打賞問題時,還存在一些頗有爭議的問題需要解決。
(一)證明未成年人是打賞主體證明難問題
在多數的關于未成年人高額打賞網絡主播的民事糾紛中,如何證明未成年人是打賞的實施者是一大難題。未成年人往往使用家長的賬號登陸直播平臺或者某些未成年人用父母的身份信息注冊賬號使用,利用以家長的身份綁定的銀行卡、微信、支付寶等支付工具進行打賞等轉賬消費活動。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這就需要家長對在打賞時實施的主體是未成年人進行證明。但是,打賞行為的即使性導致家長在取證時面臨著重重的困難,甚至家長在行為發生的幾個月后才發現未成年人在其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大額轉賬消費行為,在此期間,也很有可能使得相關的證據滅失。
(二)負責返還打賞金錢的主體
未成年人的監護人在追回打賞金的過程中,負責返還打賞錢款的義務主體是直播平臺還是網絡主播?我國學者對此看法是,需要根據網絡主播與平臺之間的關系等具體情況來判斷,如主播與平臺之間是勞務合同關系,那么由直播平臺承擔無過錯責任,未成年人的監護人直接向直播平臺討還打賞金即可。如果主播與平臺之間構成服務合同關系,那么監護人在請求返還打賞金時,可同時起訴網絡主播和直播平臺,要求網絡主播以及直播平臺返還打賞的金額。
(三)追回打賞金困難問題
筆者在黑貓投訴上以“未成年直播打賞”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僅在2020年十二月份投訴案件達300多件,并且投訴成果的寥寥無幾,投訴失敗的原因多數是平臺認為未成年人的監護人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證明打賞行為是未成年人實施的而被駁回。或者平臺答應與監護人協商,但平臺又遲遲不肯退款,造成毀約的情況。監護人走投無路尋求訴訟途徑救濟,但訴訟周期較長成本高證據不足等問題也都導致追回打賞金困難。
四、預防未成年人打賞的建議
(一)家長需加強對未成年引導和教育
家長需積極引導未成年人適度合理的使用手機,防治孩子過度沉溺于網絡;家長還需要加強與未成年孩子之間親子關系的交流和培養,陪伴孩子健康快樂的成長;家長還需保管好銀行卡,手機支付密碼,對未成年人的異常行為保持警惕。未成年人還未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容易被網絡中光怪陸離的世界所蒙蔽,家長要引導孩子樹立正確的金錢觀和消費觀,使其具有健全的人格。
(二)加強完善相關立法
我國對未成年人打賞網絡主播如何進行救濟的立法尚不完善,目前關于網絡直播方面的相關國家規定只有《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關于加強網絡直播服務管理工作的通知》、《網絡表演經營活動管理辦法》等,并且規定內容比較籠統和碎片化,難以真正去執行。家長要求退還打賞費用主要是通過向平臺申訴或者與平臺協商,對此國家應逐步完善互聯網環境下未成年人保護相關法律規定,規范直播行業打賞的標準,逐步完善相關立法。
(三)規范取證制度
未成年人的監護人在索退打賞金時面臨舉證打賞行為是未成年人所實施、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賬號混用的困境。因此,規范取證責任制度,在具體的糾紛中,可以根據用戶注冊紀錄、登陸狀態、聊天內容、彈幕內容等分析,結合打賞次數、打賞金額、打賞頻率、設備IP 地址等綜合因素判斷打賞行為是否是未成年人所實施,規范取證制度,維護未成年人的權益。
五、結語
隨著互聯網經濟的深入滲透,網絡直播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在提升全社會創造力和生產力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如何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利的問題。網絡直播服務者在提供直播服務時,應當遵守法律法規,堅持正確的價值導向,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積極健康的網絡文化,為青少年的健康成長提供一個風清氣正的網絡世界。為此,營造良好的網絡環境,培養未成年用戶正確的社交觀和消費觀是平臺、主播、家長以及社會不可推卸的責任。
參考文獻
[1]程嘯,樊竟合.網絡直播中未成年人充值打賞行為的法律分析[J].經貿法律評論,2019(03):1-15.
[2]周熙瑩,譚子恒.法律視角下未成年人網絡直播打賞行為研究[J].太原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9(05):201-204.
[3]廖正.網絡直播平臺與網絡主播的合同爭議及法律規范[J].山東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21(03):56-63.
[4]閆斌.網絡直播行業的法律風險與規制[J].社科縱橫,2019,34(02):75-79.
[5]文慧.論未成年人的網絡直播打賞行為[J].西部學刊,2019(01):70-75.
作者簡介:
秦效,1996.4,女,漢,山東濟寧,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