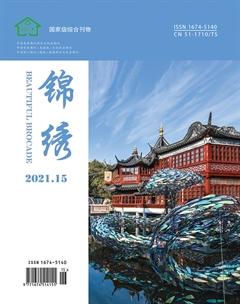在中國“硅谷”里狗茍蠅營
摘要:NHK作為一家持續(xù)關(guān)注中國社會的日本媒體,堅持探討和反映中國各個角落所發(fā)生的現(xiàn)象與產(chǎn)生的問題。在《三和人才市場》(2018)這部紀(jì)錄片中,鏡頭聚焦于廣東深圳三和人才市場里活躍著的一批特殊人群——“三和大神”身上。
狹義上“三和大神”的主體構(gòu)成是第一代農(nóng)民工進城務(wù)工后留在農(nóng)村的留守兒童,多出生于九十年代以后,也被成為“第二代農(nóng)民工”或“新生代農(nóng)民工”。當(dāng)他們沿著父輩的足跡來到一線城市打工,卻發(fā)現(xiàn)他們早已不能像第一代農(nóng)民工那樣恒定的保持初心與夢想,也不愿吃苦耐勞、逆來順受去接受現(xiàn)實的打壓。佛系、草食、低欲望是“大神們”進入中產(chǎn)階層后更體面更具欺騙性的表現(xiàn)形式,得過且過、狗茍蠅營是他們信誓旦旦信奉的信條,夢想與能力的不匹配最終將他們的理想與追求吞噬干凈。究其本質(zhì),其實是對社會固化后一種消極無聲的反抗。
在本文中,我會簡要的將第一代傳統(tǒng)農(nóng)民工與第二代新生代農(nóng)民工的生活方式、性格特征等方面進行對比分析,探討其異同點。
關(guān)鍵詞:社會困境;NHK;紀(jì)錄片;農(nóng)民工;灰色地帶
一、相同點
無論是傳統(tǒng)農(nóng)民工還是新生代農(nóng)民工,他們來到的大城市都會賦予他們一個身份——“異鄉(xiāng)人”。就像影片中經(jīng)營豆?jié){店鋪的左撇子陳用發(fā)說的一句話:“這是別人的城市,不是我們的,我們只是在這掙錢。”城市自發(fā)的排他性讓農(nóng)民工們沒有歸屬感、獲得感,究其原因,有兩部分構(gòu)成。
第一部分,是農(nóng)民工自身條件與能力跟其所在的大城市需求的不匹配。影片中數(shù)據(jù)顯示,在深圳打工的人群中初中學(xué)歷的占到了60%以上,上過大學(xué)的寥寥無幾。沒有與崗位相匹配的技術(shù)與能力,沒有知識與學(xué)歷的支撐,他們只能投奔又臟又累的勞動密集型產(chǎn)業(yè),做著最累的活,拿著最少的工資。前身為留守兒童的他們被托付于祖父祖母,年齡與代溝弱化了教育與求知意識,從教育到生活再到成長,他們都沒有得到良好的引導(dǎo)和撫育。這個問題的產(chǎn)生不能怪他們或他們的父母,這是一個結(jié)構(gòu)性的問題,牽一發(fā)而動全身,是急劇發(fā)展中的整個中國社會出了問題,只不過由他們來承擔(dān)罷了。
第二部分,是社會資源整體的不足以及部分分配的不均。曾經(jīng)我們愛說,中國的優(yōu)勢在于“人口紅利”,人多力量大,對于勞動密集型產(chǎn)業(yè)農(nóng)民工們起到了支柱的作用。然而,人多了,每個人人均分得的資源自然而然就少了一杯羹。90年代初,中國制造業(yè)崛起,因此帶動了整個中國的農(nóng)民工進城打工熱潮,吃力不討好的他們,沒有社保、沒有醫(yī)保、沒有工傷賠償,甚至連工資要不要得回來都成問題。就像陳用發(fā)所提到的小孩上學(xué)所采用的積分分批排名問題,要參考的因素有社保、居住證、租房、戶口、是否超生等等,各項指標(biāo)綜合計算后所得的積分進行排名,排上了有學(xué)可上,排不上便無緣上學(xué)。這種做法雖然過度的將政策優(yōu)勢和資源向城市本地人方向傾斜,但是這是我國人口眾多的區(qū)域化管理模式的必要之舉,因此資源的不符與不均就成了必然的結(jié)果與問題。
總結(jié),傳統(tǒng)農(nóng)民工和“新生代農(nóng)民工”的共同之處在于他們都處于城市社會的邊緣灰色地帶,由于自身硬件條件與城市社會需求的不符以及社會資源總量的不足以及分配的傾斜,他們往往無法在城市中找尋到歸屬感和獲得感,從而成為夾縫中生存的邊緣人。
二、不同點
從影片中可以顯而易見的是,傳統(tǒng)農(nóng)民工和“新生代農(nóng)民工”在勞動意識、生活方式、性格特征等方面都有著巨大的差異。一代是吃苦耐勞、勤勤懇懇努力掙錢養(yǎng)家的追夢人;一代是干一天玩三天、地為床天為被、昏天黑地的做夢人。
很多人的貧窮和與貧窮相伴而生的挫敗,有時并非個人不努力的結(jié)果,很多情況下它更像是一個結(jié)構(gòu)性不公平所引發(fā)的連帶效應(yīng)。如果說成功代表著財富和機會的話,那么流竄在三和人才市場的廣大青年們則是一群徹徹底底的失敗者:貧困,沒有出路,甚至連希望都沒有。努力是要能向著光前進,或者至少有影子供人追隨,但這幫人就連這種可能性都沒有了。他們屢試屢敗,不是被騙就是被剝削,一切努力換來的不是生活的向好,而往往是更深的絕境或者死胡同,他們就像是被命運斬斷旅路途的流亡者,沒有道路,唯有漂流。
“三和大神”曾經(jīng)也滿懷著熱血與激情來到這座城市,卻被畸形的社會邊緣磨光了身上所有的銳氣和棱角。他們生在了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達的向好時代,看得見卻摸不著。他們知道馬云以“每秒鐘”的速度賺錢,他們也知道深圳市中心的房價是500萬一套,他們看著車水馬龍,心里卻是五味雜陳。在當(dāng)今的城市社會中,貧富差距成為了不可繞開的一大問題——有資本的人進行創(chuàng)業(yè)和投資,對資本進行再生產(chǎn)的處理,只會變得越來越有錢;而沒有資本的人只能憑借著一身蠻力和匪氣,在社會里一試再試,渴望著一個機遇的轉(zhuǎn)身,卻屢屢碰壁。
再反觀第一批來到城市打工的農(nóng)民工們,他們的目的就很純粹——為了父母和子女。他們的視野和感知比較閉塞,信息不通,只知道當(dāng)時有這么一股農(nóng)民工進城的潮流,二話不說一股腦就跟著去了,這種狹隘和閉塞可能成就了他們。就像斷了一只手臂的陳用發(fā),在深圳打拼了18年,經(jīng)營著一家收入穩(wěn)定的早餐店。“沒有退路,才有出路。”在那個工商業(yè)急劇發(fā)展的年代,農(nóng)業(yè)遭受重創(chuàng)和擠壓,不走出大山與田地,可能意味著一家人這輩子都被困于貧窮與無知中。正是這種對家人、對家庭甚至于對整個村莊的責(zé)任與使命感,推動他們進城務(wù)工,成就了一批有責(zé)任、能吃苦的追夢人。
對于第一代農(nóng)民工和第二代農(nóng)民工,兩者性格、生活方式上的種種差異并不能說明他們哪一種做得好、哪一種做得不對。只是在不同的特殊的時代、不同的政策、不同的生活環(huán)境與成長歷程中所塑造出的人迥然相異,是歷史的產(chǎn)物,也是時代的烙印。
紀(jì)錄片就像一支鋒利冰冷的手術(shù)刀,冷靜而又精準(zhǔn)的剖析著中國社會的病狀和癥候群。《三和人才市場》對于“三和大神”的精細刻畫,像一個置身事外的旁觀者,又像一個渴望伸出援手去解救的朋友,更像一個期待改變與進步的憤青——中國社會現(xiàn)狀的剖析與思考,我們一直在路上。
參考文獻
[1]NHK紀(jì)錄片的中國表征與價值取向[J].徐曉波,田雪,孫儒為.當(dāng)代傳播.2013(06)
[2]日本農(nóng)民工轉(zhuǎn)型的啟示[N].童卉欣.中國商報.2010(006)
[3]中國文化對外傳播面臨的問題及其對策——基于文化層次性的研究[J].潘榮成.理論月刊.2018(05)
作者簡介:梁思琪(2001-08),女,漢族,湖北武漢,本科在讀,四川大學(xué),研究方向:新聞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