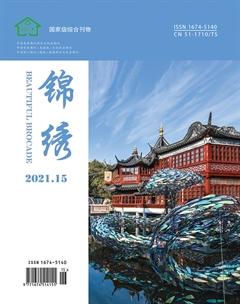白先勇小說中的南京、上海書寫
摘要:白先勇幼年輾轉(zhuǎn)多地,很多地方的文化對他的創(chuàng)作都有深遠影響,例如南京的秦淮河文化和上海的百樂門文化。南京的秦淮河文化以《游園驚夢》中的錢夫人為代表,體現(xiàn)強烈的懷舊意識。上海的百樂門文化以來自上海百樂門舞廳的尹雪艷和金大班這些舞女為代表,描述十里洋場的紙醉金迷。兩種文化的不同在于,南京有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而上海則是新興的摩登女郎。
關(guān)鍵詞:南京;上海;秦淮河;百樂門
一、白先勇小說中的南京書寫
(一)秦淮河文化
南京最著名的秦淮河被稱為“中國第一歷史文化名河”,它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空間,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空間和意蘊。在晚明,“南京冶游,最時興挾名妓乘畫舫以游秦淮。……凡有特客,或外地之來南京者,必招游畫舫以表示敬重。”[2]雖然秦淮河在古時盛極幾代,但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落。陳源曾在散文《南京》中寫道“我實在不愛秦淮河!”、“什么六朝金粉,我只看見一溝腌臜的臭水”[3],曹聚仁在《秦淮河上》中也說,“‘如雷貫耳,聞名已久的秦淮河,簡直是一道臭水溝”。[4]傳統(tǒng)的秦淮河已經(jīng)在我們的心中形成了一個固定的形象,對它有某種意蘊期待,帶著自以為是的期待視野去觀察,就會產(chǎn)生情感的異變。現(xiàn)在的秦淮河已經(jīng)物是人非,以往才情出眾能和文人吟詩作對的雅妓已經(jīng)不再。想象中的往昔和現(xiàn)實的不堪,強烈的對比讓人對秦淮河產(chǎn)生了不滿,更加向往逝去的秦淮河。懷舊,也成為了秦淮河的主題。
(二)《游園驚夢》中的秦淮河文化
秦淮河文化主要呈現(xiàn)在白先勇的《游園驚夢》中。《游園驚夢》以傳統(tǒng)戲曲《牡丹亭》為主線,無論是人物、情節(jié)、主題都和《牡丹亭》相輔相成,渾然一體。主人公錢夫人曾是南京秦淮河畔得月臺唱昆曲的優(yōu)伶——藍田玉,一曲《游園驚夢》讓她被錢鵬志娶回家,二十歲就嫁給六十歲的老頭,從此做了將軍夫人。她到臺北以后受昔日姐妹竇夫人之邀去參加票友會,當(dāng)初一起在得月臺的姐妹淘個個光鮮亮麗,明艷動人,反觀自己獨身一人,還是坐計程車前去赴宴。在席間,往事和現(xiàn)實相互交錯,作者運用意識流寫法突出了錢夫人內(nèi)心因為命運轉(zhuǎn)換產(chǎn)生的復(fù)雜懷舊之情。
整篇小說通過錢夫人在現(xiàn)實和回憶中的兩次宴會強烈對比,深化了作者想要表達的悲劇命運的主題。“三十年河?xùn)|,三十年河西。”過去的自己風(fēng)華正茂,現(xiàn)在連當(dāng)年不如自己的桂枝香都比自己更加明艷。這種命運轉(zhuǎn)換是悲劇的,人人都可能會是從前的錢夫人今日的竇夫人,但今日的竇夫人以后也會成為今日的錢夫人。在白先勇看來,普及于個人的命運法則是:燦爛只是一瞬,而黯淡則是永恒;興盛是變量,只有衰敗才是恒量;擁有僅僅是一種偶然,失落才是命定的必然。[5]秦淮河文化亦是如此,從前的興盛變成了如今的衰敗,這是注定的悲劇。雖然錢夫人的命運和秦淮河的命運不盡相同,但錢夫人身上隱藏的悲劇命運與當(dāng)年盛極一時的秦淮河何其相似。白先勇在《游園驚夢》中將歷史變化的實質(zhì)與錢夫人的悲劇命運聯(lián)系在一起,還將故國不再的懷舊意識貫穿整篇小說,這是南京秦淮河文化在《游園驚夢》中的主要表現(xiàn)。
二、白先勇小說中的上海書寫
(一)百樂門文化
上海在外國勢力強勢侵入下,衍生了很多西方的標(biāo)志性建筑。對于傳奇的百樂門舞廳,有一段生動的描述:
出了戲院,我們就去百樂門,那里有夜總會和舞廳。百樂門是新近由中國銀行家建的,里面設(shè)計極其現(xiàn)代,有大量的鎳、水晶和白色木頭布置。白色的大理石旋轉(zhuǎn)樓梯通向大舞廳,陽臺上另有一個舞池,玻璃地板,下方有腳燈,讓人感到像在雞蛋上跳舞。舞臺正對著人口,上面是樂隊,都是俄國樂師,但奏的都是最新的美國爵士樂。我們到的時候恰逢表演開始。表演合唱的也是俄國女子,有些是金發(fā)美人。她們穿戴很少:帽子、淺幫鞋和非常細的腰布。和美國的合唱隊姑娘相比,她們演得不算好,常用不流暢的英語唱最新的美國歌。一個英國朋友告訴我,雇俄國女子比雇中國人便宜多了,而中國人又非常崇拜金發(fā)白人女子。1
白先勇見證了1946至1948年的上海,他目睹了上海從繁華變成沒落。金融危機和種種原因讓上海的百樂門成為了歷史,所以他寫下了《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永遠的尹雪艷》。“尹雪艷總也不老。......不管世事變遷,尹雪艷永遠是尹雪艷,在臺北仍舊穿著她那一身蟬翼紗的素白旗袍,一徑淺淺的笑著,連眼角兒也不肯皺一下。”[1](130)白先勇把對那個繁華的百樂門時代的懷念之情寄托在了這些舞女身上,尹雪艷和金大班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百樂門文化的化身。
(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百樂門文化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以舞廳為場景描寫了一個舞女的前半生。金兆麗是在舞廳打拼了二十年,歷盡大風(fēng)大浪撐起夜巴黎場面的玉觀音。她在從良前的最后一夜,在這人生重要轉(zhuǎn)折點,回想了自己的前半生。小說在這一特定時空將歷史倒回和現(xiàn)實穿插,演繹了一場濃縮的人生戲劇。過去金大班在上海百樂門時代的那種風(fēng)頭,數(shù)遍上海十里洋場,“大概只有米高梅五虎將中的老大吳喜奎還能和她唱個對臺”,就連現(xiàn)在的夜巴黎也是靠她玉觀音的老牌子撐起來的。但無論外表再風(fēng)光,也不能彌補金大班心中的失落和不安全感。作為在風(fēng)塵打滾的舞女,她比普通人更渴望一段真摯的感情。年輕時的她看見其他人嫁給有錢老頭還嗤之以鼻的瞧不起她們,說“我才沒有你們那樣餓嫁,個個去捧塊棺材板。”她不愿自己的命運像其他舞女一樣為了金錢嫁人。所以,當(dāng)她真正愛上月如時,她以一種虔誠的姿態(tài)奉獻自己,想為他生孩子,但最終還是沒能敵過命運的安排。月如走了,她為月如懷的孩子也被迫打掉。正是因為她經(jīng)歷過這些,被現(xiàn)實磨滅了對抗命運的熱情和勇氣,成為了現(xiàn)在的金大班。現(xiàn)在的她更注重現(xiàn)實利益,所以當(dāng)她面對秦雄那份熾烈的感情,選擇了視而不見,最終選擇了有錢的老頭陳發(fā)榮。四十歲的老女人已經(jīng)不能再折騰了,她沒有那個資本再放縱的愛一次,可就連她自己也惋惜道“要是十年前她碰見秦雄那么個癡心漢子,也許她真的就嫁了。”。年輕時的金大班也想過抗?fàn)帲拖瘛豆聭倩ā分械奈鍖氄f的“這就是命。”所以,她們都沒能逃脫命運的枷鎖,最終回到命運為她們安排的位置上。
從《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也很容易看出歷史從興盛到衰敗的過程。從前的金大班在百樂門風(fēng)光無限,“當(dāng)年在上海,拜倒在她玉觀音裙下,像陳發(fā)榮那點根基的人,扳起腳趾頭來還數(shù)不完呢!”[1](174)但現(xiàn)在,四十歲的金大班在自己看不起的夜巴黎舞廳,就要嫁給曾經(jīng)看不起的陳發(fā)榮之流。白先勇在金大班的人生中穿插了從上海到臺灣的場景,貌似一切都沒有變,但實質(zhì)上已經(jīng)變了。上海百樂門的繁華已經(jīng)不復(fù)存在,衰敗才是常態(tài)。
三、秦淮河文化與百樂門文化的和而不同
南京和上海文化都屬于南方文化,它們的地域文化特征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兩者的代表文化——秦淮河文化和百樂門文化都描述了一個紙醉金迷、繁華綺麗的世界。這點從錢夫人和金大班對大陸的回憶中可以看出。錢夫人總覺得,大陸的東西要比臺灣的好。為了赴宴她專程拿出舍不得穿的杭綢做旗袍,因為“她總覺得臺灣的衣料那么粗糙,光澤扎眼,尤其是絲綢,哪里及得上大陸貨那么細致,那么柔熟?”[1](255)就連臺灣的花雕也不如大陸的那么醇厚,總有點割喉。金大班也還沒從過去繁華的百樂門中走出來,依然懷念那個自己曾經(jīng)風(fēng)華絕代的上海舞廳。白先勇將對南京上海文化的懷舊之情寄托在這兩名女子一生的描寫中,將她們回憶中保留美好記憶的南京上海精準(zhǔn)的描繪出來。白先勇在秦淮河文化和百樂門文化中深藏的含義是兩者都已衰亡,證明世事無常,不要貪戀現(xiàn)有的繁榮,因為衰敗才是永恒的,繁榮只是一時的。
和上海文化相比,秦淮河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古代的韻味更加濃厚。秦淮河畔優(yōu)伶出身的錢夫人與昆曲《游園驚夢》關(guān)系匪淺,因為一曲《游園》被娶回家當(dāng)上了將軍夫人,更在《游園》中啞了嗓子。南京經(jīng)歷過這么多朝代的更替,懷舊和今非昔比也是十分容易感受到的。以南京為背景的《思舊賦》,整篇小說充滿了荒涼衰敗的落寞之氣,以前風(fēng)光的“李公館”現(xiàn)在已是破敗不堪,讓人唏噓不已。在《國葬》中回憶南京的秦義方,在李將軍的葬禮上,想起抗日勝利那天在南京意氣風(fēng)發(fā)的場景,為李將軍的晚年感到悲痛萬分。
而上海是商業(yè)化的新興城市,現(xiàn)代氣息更加濃厚。《謫仙記》中李彤上海家的別墅“.......寬大堂皇,花園里兩個大理石的噴水泉,在露天里跳舞,泉水映著燈光,景致十分華麗。”還有一直懷念百樂門的金大班,總是瞧不起夜巴黎舞廳,甚至認為“百樂門里那間廁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還寬敞些呢”。還有總也不老的尹雪艷“好像是上海百樂門時代永恒的象征,京滬繁華的佐證一般。”。她在臺北的新公館從來不肯把它降低于上海霞飛路的排場,從沙發(fā)到麻將間,無一不讓人感到舒服精巧。
從《游園驚夢》看秦淮河文化的歷史進程,從《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看百樂門文化的興盛衰亡,兩種文化共有的懷舊情緒和命運意識讓讀者深省。二者和而不同在:秦淮河有著深厚的歷史積淀,是美人遲暮;上海則是新興的摩登女郎,讓人新奇。
參考文獻
[1]白先勇.白先勇自選集[M].廣州:花城出版社,1996.
[2]武舟.中國妓女文化史[M].上海: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2006: 215.
[3]陳源.丁帆.江城子———名人筆下的老南京[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86.
[4]朱自清.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8.23.
[5]白先勇.第六只手指[M].廣州:花城出版社,2000.
[6]劉俊.悲憫情懷:白先勇評傳[M].廣州:花城出版社,2000:266.
[7]李歐梵.上海摩登[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2001.
摘自李歐梵《上海摩登》31頁,引文出自德爾,《上海1935》,49頁。
作者簡介:文君竹,女,1993年出生于重慶萬州。于2018年獲得文學(xué)碩士學(xué)位,現(xiàn)為重慶三峽學(xué)院傳媒學(xué)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