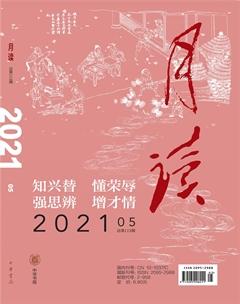?何氏家風(fēng)面面觀
周甲辰
湖南省永州市道縣的何氏世家自何凌漢開(kāi)始,繼以何紹基、何紹祺兄弟,再經(jīng)過(guò)何慶涵,直到何維樸,歷經(jīng)四代,名人輩出,享譽(yù)中外。其代表人物何紹基,字子貞,號(hào)東洲,別號(hào)東洲居士,晚號(hào)蝯叟(一作猨叟)。他身經(jīng)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四朝,歷任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國(guó)史館提調(diào),以及福建、貴州、廣東鄉(xiāng)試主考官,四川學(xué)政等職,后主講山東濼源書院與長(zhǎng)沙城南書院,為晚清著名書法家、詩(shī)人、畫家。他的書法師古而不泥古,自成一家,被譽(yù)為“有清二百余年第一人”。
一、勤苦自強(qiáng)的精神
南宋初期,山東青州益都路何氏家族的何念大、何念二、何念三兄弟因逃避金人,跟隨父親舉家向南遷徙。歷經(jīng)艱險(xiǎn),于宋理宗嘉熙年間(1237—1240)到達(dá)道州(今道縣),并在道州東門村定居下來(lái)。初到道州時(shí),人生地疏,何氏一家靠打短工、賣苦力勉強(qiáng)度日,后憑借勤勞節(jié)儉,慢慢站穩(wěn)了腳跟。發(fā)展到第六代孫何榮時(shí),家業(yè)漸興,兄弟四人也都識(shí)文斷字。為不忘家族艱辛,牢記先輩教誨,何榮擬了一副對(duì)聯(lián):“記祖宗二字格言克勤克儉,示兒孫兩條正路惟讀惟耕。”他將這副對(duì)聯(lián)貼在正房神龕上,作為治家理念,教育后代子孫,自此開(kāi)啟了這個(gè)家族耕讀傳家、詩(shī)書繼世的文化傳承。
此后,何氏家族逐漸興旺起來(lái),自第八代至第十九代,歷代子孫明經(jīng)茂才,儒業(yè)相繼,代有其人,先后出過(guò)四名進(jìn)士,六名舉人,后人大都能堅(jiān)守勤儉家風(fēng),家族“書香綿延,至明清而愈顯”。
何凌漢是何氏家族的第十九代孫,出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他“少失怙恃,孤苦淬礪”,白天上學(xué)讀書,早晚下地干活,起早貪黑,少有休息的時(shí)候。因家中貧苦,“夜不能具燈”,他經(jīng)常“燃松枝讀書”。即便是在高中探花、步入仕途之后,他依然勤學(xué)不輟。擔(dān)任經(jīng)筵講官期間,他“在詞館內(nèi)攻讀,苦如諸生”。其子何紹基出生于嘉慶四年(1799),“承家學(xué),少有名”,一生愛(ài)學(xué)、勤學(xué)。他說(shuō):“惟書愛(ài)最真,坐臥不離手”(《生日書懷》)。因?yàn)榭炭鄬W(xué)習(xí),何紹基博學(xué)多才,通經(jīng)史、工書法、精律算,對(duì)文學(xué)、音韻、訓(xùn)詁、金石、碑刻等都有較深入的研究。桂文燦的《經(jīng)學(xué)博采錄》稱贊何紹基:“于學(xué)術(shù)無(wú)所不窺,博覽而詳說(shuō)之。六經(jīng)、子史皆有著述,尤精小學(xué),旁及金石碑版文字。凡歷朝掌故,無(wú)不了然于心。”
何紹基愛(ài)好書法,求教于多師,一輩子尋碑練帖,癡迷不倦。至遲在26歲時(shí),他已花重金買下《張黑女志》的墨拓孤本,自此“無(wú)日不在篋中”,日夜揣摩,“每一臨寫,必回腕高懸,通身力到,方能成字,約不及半,汗浹衣襦矣”(《跋魏張黑女墓志拓本》)。晚年主講濼源書院時(shí),何紹基雖已書名顯赫,但他仍要探本溯源,專攻“八分”之法,“自課之勤,并世無(wú)偶”。由于飽讀詩(shī)書,廣泛臨帖,何紹基的書法作品“學(xué)養(yǎng)兼到”,具有很高的氣韻和格調(diào)。
何紹基的孿生胞弟何紹業(yè)恬淡脫俗,“實(shí)無(wú)志科名”,但他于科舉之外的學(xué)問(wèn)用力很深,精于繪畫、書法、篆刻,“于天文、儀象、律呂、六書之學(xué)無(wú)不通”(何紹基《仲弟子毅墓志》)。何紹基之子何慶涵天資敦厚,專勤嗜學(xué),一年之中除吟詩(shī)作文外,無(wú)一刻不溫書,“年逾七十,專勤如少時(shí)”。何氏家族的勤苦精神一直受人欽敬。
二、儉樸端直的品格
道州臨近舜帝陵墓所在地九嶷山,舜德文化氛圍濃厚。由于舜德文化與家族傳承的影響,何氏世家的子孫均崇德尚儉,品行端直。他們躋身官場(chǎng),能清廉自守,敢言直陳,心系百姓;歸隱山林后,或勤于耕作,或寄情書畫,為人耿介,趣味高雅。
何凌漢為人莊敬刻厲,辦事勤勉謹(jǐn)慎,“治家嚴(yán)肅如官府”。他的妻子廖氏嫁到何家后,布衣粗食,親自操持家務(wù),還干過(guò)挑水舂米一類的粗活。何凌漢在官場(chǎng),“持大體,抑奔競(jìng),崇樸實(shí),與人和而不同”(何紹基《先考文安公墓表》),任人堅(jiān)持“以根底器識(shí)為先”,從不以個(gè)人好惡定取舍。他曾多次諫阻增稅,并力主簡(jiǎn)放冗員,千方百計(jì)減輕百姓負(fù)擔(dān)。在“位日高,望日隆,俸祿漸豐”之后,其日常生活依然跟當(dāng)秀才時(shí)一樣簡(jiǎn)樸,糲食布衣,鹽菜佐食。何凌漢雖貴為兩朝重臣,但他一生沒(méi)有置下多少私產(chǎn)。每逢生日節(jié)慶,他人送來(lái)的禮物,除花卉與水果外,其余一概拒收。他心系故土,曾斥巨資為鄉(xiāng)中學(xué)校添置義田校產(chǎn),促進(jìn)家鄉(xiāng)教育的發(fā)展。
何凌漢“教子孫以忠儉樸為訓(xùn)”,其子何紹基生活同樣簡(jiǎn)樸。擔(dān)任提督四川學(xué)政后,何紹基曾說(shuō):“余性不嗜海菜,不喜浮華,所至如桌圍、椅披、地毯等皆撤去,吏役不準(zhǔn)濫用頂戴,仆輩不得綢緞及外套出門,止隨一仆轎前,不得有馬。川督學(xué)雖四品以下皆乘綠幃轎,余不敢也。”(《道州志》卷九)何紹基性格耿直,剛直不阿,見(jiàn)到他人有不善之處,哪怕事不關(guān)己,也常當(dāng)面指出。久之,人“咸親其和而憚其峻”。對(duì)此,他倒是很有自知之明,說(shuō)道:“自知道性癖難諧俗,且喜身閑不屬人。”還說(shuō):“看破浮云憐世味,生來(lái)瘦骨見(jiàn)天真。”督學(xué)四川期間,何紹基不僅努力整頓考風(fēng),汰除冗員,飭裁陋規(guī),還仗義執(zhí)言,同眾多貪官污吏發(fā)生正面沖突。弄得“權(quán)貴側(cè)目,謗焰熾騰”。最終因直陳時(shí)務(wù)十二事,被皇帝斥為“肆意妄言”而丟官去職。
何紹基的元配夫人陶氏安于簡(jiǎn)樸生活,喜言忠孝節(jié)烈之事,“平生無(wú)華服,殮后檢其篋,多嫁時(shí)故衣,無(wú)一鮮麗者”(何紹基《元配陶安人傳》)。
何紹基的弟弟何紹祺隨順謙和,給人以至德君子的印象。他為官期間勤于政務(wù),清廉自守,興教勵(lì)學(xué),治水賑災(zāi),頗有政聲,被內(nèi)閣大學(xué)士萬(wàn)青藜譽(yù)為“滇中好官第一”。其妻陳氏一生布衣粗食,“雖貴盛卻不御紈綺,仍率婦作勞”。由于為官清廉,又樂(lè)善好施,何家到何慶涵時(shí)依然“家無(wú)余財(cái)”。
何凌漢以及何紹基兄弟在書法上喜愛(ài)顏真卿的拙重,堅(jiān)持“橫平豎直”的創(chuàng)作原則,這既源于他們對(duì)書藝規(guī)律的探索與把握,也是他們做人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表現(xiàn)。
三、明理獨(dú)立的思維
道州是何凌漢父子的故鄉(xiāng),也是理學(xué)開(kāi)山周敦頤的故鄉(xiāng),何氏與周氏世為婚姻,兩大世家家風(fēng)家教相似,何家受宋明理學(xué)影響很深。何家所崇尚的“勤”,從深層次看,既包括勤學(xué)與勤耕,也包括勤思與勤研。何氏子弟因而具有明理獨(dú)立的品性,在思考社會(huì)、人生與藝術(shù)等各種問(wèn)題時(shí)頭腦清醒,不隨流俗。
何凌漢“于宋儒之言性理者,亦持守甚力”(何紹基《宋元學(xué)案敘》)。他求學(xué)應(yīng)考的年代,書壇上館閣體一統(tǒng)天下,他雖然沒(méi)能完全避免館閣體的影響,但習(xí)練書法時(shí)堅(jiān)持從顏入,經(jīng)歐、李,過(guò)漢魏諸碑,再旁及其他,以“橫平豎直”為標(biāo)準(zhǔn),獨(dú)立選擇和規(guī)范習(xí)練途徑,最終成功跳出了館閣體的窠臼。他的“書法重海內(nèi),朝鮮、琉球貢使索書,應(yīng)之不倦”(李元度《清朝先正事略·何文安公事略》卷二十四)。他還曾“入乾清宮侍書,寵光稠渥,可謂極儒人知遇之榮矣”(李鏡蓉修、許清源纂《道州志》)。
何紹基提出做人要“立誠(chéng)不欺”“真我自立”“做成路數(shù)”,認(rèn)為孝悌謹(jǐn)信,出入有節(jié),若不是發(fā)自內(nèi)心,便僅僅只是應(yīng)酬而已。在藝術(shù)上,他非常重視真性情與獨(dú)創(chuàng)性。他說(shuō):“書家須自立門戶,其旨在熔鑄古人,自成一家。否則,習(xí)氣未除,將至性至情不能表見(jiàn)于筆墨之外。”(《使黔草序》)他習(xí)練書法雖然碑帖兼修,一生搜集并臨摹了無(wú)數(shù)名碑好帖,但他不盲從名家,更不因襲前人。即便是臨帖,也總是堅(jiān)持臨中有創(chuàng),入古出新。他“曾致力于漢隸至勤,東京諸碑,臨寫殆遍”(馬宗霍《書林藻鑒》卷十二),雖然對(duì)每種漢碑的臨摹可能都不下百遍,但由于臨摹中有創(chuàng)造,故所臨“乃無(wú)一相似者”。在學(xué)習(xí)古人、探索筆法的過(guò)程中,何紹基創(chuàng)造了一種名為“蝯書”的獨(dú)特書體,執(zhí)筆用懸肘,如開(kāi)強(qiáng)弓勁弩,其握筆、運(yùn)筆完全不同于常法,從而奠定了他在中國(guó)書法史上的獨(dú)特地位。他的書法成就高,影響大,“草書尤為一代之冠。海內(nèi)求書者門如市,京師為之紙貴”(林昌彝《何紹基小傳》)。
何紹基還是晚清著名詩(shī)人,他認(rèn)為“從古詩(shī)人貴性真”(《奉別余芰香》),明確堅(jiān)持“不逐時(shí)好”“不傍古人”“不將就俗目”“不偏離大本大源”等創(chuàng)作原則,追求自成家數(shù)、超拔時(shí)俗。他說(shuō):“詩(shī)是自家的,便要說(shuō)自家的話。凡可以彼此公共通融的話頭,都與自己無(wú)涉。”還說(shuō):“學(xué)詩(shī)要學(xué)古大家,只是借為入手,到得獨(dú)出手眼時(shí),須當(dāng)與古人并驅(qū)。若生在老杜前,老杜還當(dāng)學(xué)我。”(《與汪菊士論詩(shī)》)他“一生不作強(qiáng)顏詞”,凡作詩(shī)必是有感而發(fā),且在創(chuàng)作中,一心追求自由,不愿受任何約束。他說(shuō):“吾臂如生駒,未肯就羈勒。”(《久不作小字舟中試為之》)他的詩(shī)題材廣泛,風(fēng)格多樣,大都具有很強(qiáng)的藝術(shù)感染力。
四、淡泊重藝的雅趣
道州何氏以耕讀立家,在這個(gè)家族中,“讀”與“耕”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他們以求知問(wèn)學(xué)為樂(lè),以藏書豐富為榮。要求子孫無(wú)論多窮多苦都要送后人讀書。
何凌漢的父親何文繪窮得家徒四壁,卻以“食無(wú)隔夜糧,家藏萬(wàn)卷書”為榮。他規(guī)定家人:不管家里如何窮,家中什么都可以典當(dāng)出售,唯獨(dú)藏書一本都不許賣,以留備兒孫之需。何紹基曾言:“架上三萬(wàn)簽,經(jīng)史任所取。”(《憶十九歲》)由此可見(jiàn),他家里的藏書非常豐富。何氏家族在子孫讀書方面管教甚嚴(yán),“尚記誡兒語(yǔ),不許出書屋”(《飛來(lái)寺敬觀先公丁卯年詩(shī)卷次原韻書后》)。在父輩的管教下,何紹基“日或忘餐夜失臥”,讀書非常用功。
古人讀書多以科考入仕為重,何氏家族的人卻有不同,他們勤學(xué)苦讀并不只是為了參加科舉考試,更有涵養(yǎng)人格、經(jīng)世致用、藝術(shù)創(chuàng)新等多方面的追求。何凌漢“服膺許(許慎)鄭(鄭玄)之學(xué)”,而且對(duì)書籍、名帖、金石、字畫等都不惜重金,廣為收藏。他淡泊名利,情系山林,在探花及第后不久,就在《華巖訪故人不值》一詩(shī)中詠嘆“寰中仙子地,物外故人居”的清幽景色,表露出對(duì)田園野趣與隱逸生活的向往。
何紹基雖少負(fù)才名,卻仕途遲緩。他18歲開(kāi)始參加科舉考試,屢試不中,直到38歲方得中進(jìn)士。對(duì)此,何紹基自己似乎并不特別在意。他在“應(yīng)付”科舉考試的同時(shí),還在多方面發(fā)展自己的興趣愛(ài)好。他說(shuō):“余性喜學(xué)書,而亦好為金石考訂之學(xué),又兼及畫理。”(何紹基《金石書畫編年錄》序)他尤其愛(ài)好書法,常四處參師會(huì)友,尋碑訪帖,為成為一代書家奠定了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何紹基生性恬淡,“高門懶去候公卿”,但卻酷愛(ài)游歷,《東洲草堂詩(shī)鈔》錄有山水詩(shī)700多首,幾乎占其現(xiàn)存詩(shī)作的三分之一。他說(shuō):“詩(shī)人愛(ài)山如骨肉,終日推篷看不足。”(《愛(ài)山》)他甚至連做夢(mèng)都在游山玩水:“無(wú)端野性隨春發(fā),萬(wàn)疊奇山入夢(mèng)多。”(《野性》)
何紹基的兄弟及后人的藝術(shù)成就也常為人所稱道。何紹業(yè)詩(shī)書畫均有很高水平,其詩(shī)淡逸,自成門徑;其書風(fēng)貌與何紹基相近,筆力古拙而不失雅逸;其畫意境清遠(yuǎn),富有詩(shī)意。何紹祺精于書法,于顏真卿會(huì)心頗多,他的書作常顏中見(jiàn)歐,峻利精古,變化隨心,別具韻味。何紹京淡泊功名,學(xué)而優(yōu)卻不仕,以詩(shī)詞、書畫及鑒賞聞名于世,所畫花卉蘭竹,隨意揮灑,清逸雅秀。何慶涵能詩(shī),情感真純實(shí)在,風(fēng)格清新曉暢;能書,流暢中見(jiàn)高古,俊逸里蘊(yùn)精神。何維樸精于書法及篆刻、繪畫,他的書法學(xué)習(xí)祖父何紹基而得其形似,清新雋永,文人氣十足;其山水畫清遠(yuǎn)高妙,回味無(wú)窮。何紹祺、何紹京等人在官場(chǎng)上雖然沒(méi)有多少作為,但是他們一生勤奮好學(xué),在自己所喜愛(ài)的書畫、詩(shī)文、金石等領(lǐng)域鉆研甚深,各有所長(zhǎng),各領(lǐng)風(fēng)騷。
從總體上看,何氏子弟不僅學(xué)養(yǎng)豐富,而且往往身兼眾藝,藝道兼?zhèn)洌の陡哐拧_@與良好的何氏家風(fēng)是有密切關(guān)系的。